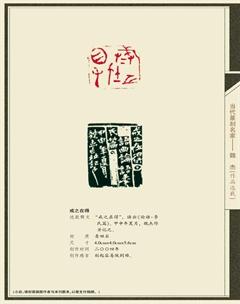瘟疫是檢驗人類文明的重要參數
劉金祥
一直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界眾說紛紜,究竟是何種力量在推動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始終都在尋找背后的某種神秘力量,長于理論分析和理性概括的哲學家們一般說得比較抽象。比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指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尋求承認的斗爭,人類在本質上存在一種被平等對待的精神需求,奴隸希望得到奴隸主的承認,否則就會反抗奴隸主的壓迫,于是,在客觀上就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則把黑格爾的人與人的斗爭概括為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之間的斗爭,認為階級斗爭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并據此提出了“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著名論斷。而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則相對務實和比較具體,在總結人類歷史發展模式方面,美國著名學者賈內德·戴蒙德于《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強調地理環境對于人類文明演進具有決定性影響;另一位美國學者兼探險家埃爾斯沃思·亨廷頓在《文明與氣候》中則強調氣候變化與文明分布之間的內在關系,指出地球上文明的分布與理想氣候的分布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將歷史學和病理學有機結合起來,在《瘟疫與人》(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中,主張應從疫病視角來審視和解讀人類文明發展進程,通過綿綿上推和悠悠下尋,得出了疫病是檢測人類文明的重要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的殊異結論。
瘟疫是人類事務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和不可或缺的維度,在人類歷史變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讀罷影響甚巨的《瘟疫與人》一書,我們也許不難理解人類文明史上的眾多重大事件,其背后大都閃爍著病毒的影子。在人類文明早期,廣闊的歐亞大陸上形成了四個相對獨立的文明圈,從東到西依次為中國、印度、西亞和環地中海的歐洲,即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命名的四大軸心文明。英語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于拉丁文“Civilis”,詞根本意是指“城市化”和“公民化”,衍生為“分工”、“合作”之意,即人們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和睦地從事生產生活。所謂文明圈就是有諸多城市存在和大量人口聚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文化地域。在這一地域的內部,由于人們與病毒經歷了長期的互動伴生,在不斷的患病、死亡與康復的交替循環中,該地域的人們對于特定的病毒就逐漸產生相應的免疫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四大文明圈就是四個獨立的傳染性病毒圈。但隨著軍事戰爭、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等人類活動的擴展,病毒伴隨人類的腳步也不斷地突破原有地域限制。當傳染病越過固有的地域邊界,這對于此前沒有病毒免疫力的異地人口而言,將對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構成致命的威脅。正如《瘟疫與人》指出的那樣:“隨著人類移動范圍的擴大,原來局促于特定區域和人群的某些疫病開始擴散交流,因而造成歷史上數次的大瘟疫。”文明發展史表明,人類歷史上一些影響當時和后世的重大事件,很多與瘟疫的滋生、暴發和傳播有著密切關系,瘟疫成為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的幕后推動力量。《瘟疫與人》一書引述了多個歷史事件,筆者感興趣的古代實例有三個:第一個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興起。公元二世紀前后,地中海地區連續經歷多次瘟疫的襲擊,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65年,由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征戰的羅馬軍隊將瘟疫攜帶到地中海沿岸,嗣后迅速蔓延至整個羅馬帝國,這次殘暴的疫情前后持續了十五年左右,受感染的地區有近三分之一人口死亡。此后五百多年時間里,地中海地區的人口大幅度遞減,經濟文化發展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面對瘟疫的大肆侵犯和無情吞噬,羅馬帝國的普通民眾處于極度恐慌、萬般驚悸的狀態,絕大部分政府組織發揮不了救助作用。恰在此時,基督教承擔起救助被感染者的責任,與同時期其他宗教信仰相比,照顧被傳染者成為基督教確認的一項義務。同時,基督教積極倡導,“即使是突然降臨的死亡也被賦予生命意義”等教義,這對于那些備罹瘟疫摧殘的幸存者來說,永恒的天國世界成了他們內心最大的安慰。正如麥克尼爾在書中所言:“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適應于充斥著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亂世的思想和感情體系。”面對瘟疫的無畏和死亡的從容,基督教于短時間內贏得底層民眾的廣泛認可和極大信任,基督教徒呈幾何級數增長,其社會基礎迅速擴大,最后被羅馬帝國定為國教,由此徹底改變了地中海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走向和文化面貌。以瘟疫所表征的自然力量在塑造和改變歷史關系上,其功能和作用有時是人的因素所難以替代和無法抵消的,比如印度種姓制度的起源。我們知道古代印度有四大種姓制度: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其中前三種屬于遠古南下的雅利安人系統,而第四等級首陀羅則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在雅利安人南下征服印度的過程中,為何沒有像中國那樣,很早就實現完全的民族大融合呢?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導致印度文明缺乏高度的凝聚力,因此,印度容易被外來殖民勢力所征服。印度整個社會結構被一個個內部相互通婚的種姓區塊所間隔,外來殖民者又很難真正深入到印度社會的底層。所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說,印度這個國家容易征服卻難以統治。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居住在中亞干燥草原的雅利安人孕育了吠陀文明,他們逐漸南下印度大陸,不斷征服原來的土著森林民族。而熱帶地區原本就易于衍生各類病毒,印度中南部的濕熱氣候和大量的病菌寄生蟲,延緩了雅利安人的入侵步伐。在這兩個民族不斷的角逐與博弈的拉鋸戰中,熱帶病毒給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大量人口死傷。擁有先進文明的雅利安人一直難以同化土著的達羅毗荼人,這就使得雅利安人發展出跨種姓接觸的種種禁忌,如婆羅門不接受首陀羅用手觸摸過的食物,就暗含著懼怕被當地病毒傳染的歷史文化因素。根據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的說法:“印度文明并沒能像對喜馬拉雅山脈北部居民那樣,將印度南部和東部的原始社群消化掉,而是把森林民族以種姓方式兼并,即把他們作為半獨立的有機體納入印度的文化聯合體當中。”既然二者難以融合、無法統一,他們就采取折中的辦法,劃出領地邊界,各自保持獨立,互不嫁娶通婚,避免相互傳染,熱帶病毒就這樣有力地阻礙了印度各民族在文化和血緣上的完全統一。
一旦作為自然力量的瘟疫以一種變量參與到歷史進程中,其對人類的影響在尺度上將使一些戰爭相形見絀,支撐筆者這一觀點的是六百多名西班牙士兵征服阿茲特克帝國這一事件。公元1520年,西班牙的科爾特斯將軍受命率領六百六十三名士兵、攜帶十六匹馬和十四尊火炮前往新大陸探金尋寶。他們乘船越過大西洋來到中美洲,對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眾多且地域遼闊的阿茲特克帝國進行征戰,結果,科爾特斯將軍憑借微薄力量擊垮了擁有幾十萬兵將的印第安古國。西班牙人何以如此勇猛強悍?以往歷史著作的解釋是歐洲人擁有堅船利炮和技術優勢,加之采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和上帝顯靈助力,但這些理由既不夠充分也不具有說服力,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在那個被后人稱之為“悲傷之夜”的夜晚,勇猛善戰的阿茲特克人大勝西班牙人,將他們逐出了首都特諾奇蒂蘭城(今墨西哥城)。但是,阿茲特克人還沒來得及進行慶祝,一場天花瘟疫從天而降,阿茲特克帝國的將軍和士兵們紛紛暴斃,甚至連皇帝蒙特祖瑪也被天花奪去了性命。而西班牙人在長期與天花病毒抗爭中已經形成了強大免疫力,面對天花病毒不僅毫發無損,而且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整個帝國。作為人類的新大陸,美洲一萬多年前才有人類遷徙居住于此,與歐亞大陸的人曾經多次抵御病毒不同的是,阿茲特克這些美洲土著居民第一次接觸天花病毒便立即大量感染死亡,對于他們來說“病毒就是最可怕的武器”;而對于西班牙人而言,病毒則已進化為穩定的“文明病”,正是這一匪夷所思的因素,最終摧垮了阿茲特克人的抵抗意志,導致龐大的帝國土崩瓦解。或許是受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一書的啟發,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也提到天花病毒對西班牙人征服阿茲特克帝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現代醫學技術雖然取得長足進步并實現大幅躍升,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也漸趨完善,但是面對猝不及防的瘟疫,人類還是非常脆弱甚至不堪一擊。正如麥克尼爾在書中所說,不要陶醉于科技發展的成就,不要過度依賴現代醫學,因為科學技術并非無往而不勝。瘟疫為何會高速率大規模地傳播?很長時間以來瘴氣發作是歐美傳統醫學的主要理論依據,這一說法類似于中醫的解釋。一般而言,瘟疫的爆發是由動物死尸或腐敗物的瘴氣所引發的,體弱多病的人一旦遇到瘴氣就會被傳染,當下有的醫學專家擔心新型冠狀病毒可通過空氣進行傳染,就是瘴氣理論的現代翻版。瘴氣理論曾經流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十六世紀西方醫學界提出接觸傳染的病菌理論后才開始松動,但彼時由于沒有檢測儀器和鑒定藥物,接觸傳染理論也僅僅停留在推測層面,并未得到西方主流醫學界的認可和接受。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獲得1905年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這兩位偉大的微生物學家,借助于顯微鏡發現了炭疽桿菌和結核桿菌,證明了此前提出的接觸傳染理論這一假設是成立的。換言之,傳染病的根源在于病毒,而不是飄移浮動的瘴氣,只有堅決避免人與人或人與動物的接觸傳染,有效防止病毒進入人體內部,才能阻斷瘟疫的大肆傳播與廣泛流行。鑒于大部分有毒細菌是通過食物、飲料進入人體內部的,巴斯德經過研究發明了用飲料殺菌的辦法,這就是迄今為止我們仍在使用的巴氏消毒法。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不難理解人類對生存環境葆有異乎尋常的適應能力,作為一種靈長類或者高級動物,人類無疑是目前地球上繁衍最多、擴展最快的物種。但從生物均衡的角度看,人類這一物種的快速衍生和急劇壯大,意味著與其共同生存于地球上的其他物種的迅速萎縮甚至不斷消亡。也就是說,人類群體的擴張、膨脹是以其他物種的減少和消失為前置條件的,這無疑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導致自然災害的不斷發生,進而給人類自身帶來巨大威脅和嚴重危害。當然,我們也必須以誠實的態度坦言,人類無端屠戮其他物種,大肆毀壞自然生態,無節制地擴充自己的食物欲望等,對于自然界和其他物種來說,人類又何嘗不是一種比瘟疫還兇悍、還暴虐的瘟疫!因此,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人類文明有其自身的界限,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也存在著必要的邊界,每當人類試圖跨過這些邊界時,不可避免地引起自然界的強烈反彈,以病毒感染和瘟疫流行等形式來報復和懲罰人類的貪婪。在歷史發展的漫長旅程中,給人類生命健康造成致命威脅和嚴峻挑戰的,除了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和大規模戰爭等人為禍端以外,便是防不勝防、突如其來的瘟疫。現在人們談及瘟疫,大都“談虎色變”,唯恐“避之不及”。瘟疫對人類的殺傷力有時難以形容和無從表達,即便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醫學已經非常先進和極為成熟,但人類對很多瘟疫仍舊無法加以控制和清除。也許,人類在較短時間內能夠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但下一場瘟疫可能又在向人類奔襲而來。對于瘟疫給人類制造的麻煩、痛苦乃至慘劇,絕大部分當代人已經或正在感同身受。然而,在威廉·麥克尼爾之前,極少有學者將瘟疫與人類相互糾纏的關系作為解釋文明的路徑,“長期以來那些學識淵博的學者在皓首窮經于各種遺存的文獻時,對于人類疾病模式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銳的洞察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瘟疫與人》是一部研究瘟疫歷史及其與人類交錯關系的開山之作,也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經典之作。如前文所述,在三百多頁的篇幅中,博約廣攝的麥克尼爾自由馳騁于世界幾千年文明歷程中,從容出入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諸多領域,對相關資料信手拈來、恰當運用,不僅深度考察了瘟疫與人類的多次交鋒和數度碰撞,而且從一個獨特視角重新詮釋人類文明發展史,拓展了歷史研究的思路和空間,彰顯出一代史學大師的超凡功力和深湛學養,顯示出《瘟疫與人》一書的殊異價值和獨特貢獻。英國著名學者托馬斯曾評論說,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該書不僅激發了世界尤其是我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而且深刻影響了當今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維度。《瘟疫與人》也提醒我們,人類文明發展絕非一種單向度的因果鏈條,而是多種因素共同鋪就了人類文明前行的科學軌跡;告誡我們病毒與瘟疾是一種正在凸顯的巨大現實力量,二者的頻頻發作促使人類必須盡快修正自己的行為規范,完善社會組織結構和公共衛生安全體系,在此基礎上努力重塑今天和未來的文明形態。
最后,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強調,《瘟疫與人》一書的作者威廉·麥克尼爾是國際著名歷史學家之一,是世界歷史科學的“現代開創者”,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卓然有成,與斯賓格勒、湯因比比肩齊名,被譽為“二十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辟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1963年,麥克尼爾以一部《西方的興起》一舉成名,并借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后由其撰寫的《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綱》、《人類社群史》、《權力的追逐》等均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