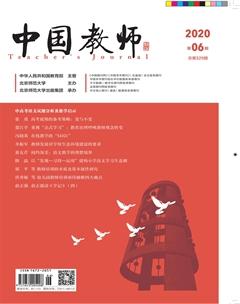十五年寶貴的知青歲月
劉夢婷

劉如英
1945年8月出生,湖南省邵陽市人。從小立志成為一名教師,由于父親政治問題,未能如愿。高二時休學主動選擇上山下鄉,于1964年以個人插隊的方式成為知青,下鄉地點為邵陽市城步苗族自治區白毛坪公社民主大隊,后成為大隊下墦塘小學知青教師。1968年轉點,在西巖公社江南大隊江南小學以民辦教師身份從教,直到1979年返城。1988年,父親洗刷冤屈,落實政策,成為公辦教師,就職于邵陽市前進小學,任教研組長。2001年退休后被返聘,直至2005年正式退休。
一、為了夢想,決然下鄉
1945年,我出生于湖南省邵陽市。我的父親是資江小學的老校長,一輩子兢兢業業,獻身教育事業。受父親的影響,加之身邊有許多善待我的恩師,我從小就立志成為一名人民教師,渴望走上三尺講臺,與可愛的學生們共度朝夕。不幸的是,我的父親讀書時期因被同學冤枉,記下了政治問題;當校長期間因倡導學生學習而非搬磚勞動,以“只專不紅,走白專道路”的罪名受到批判。父親的政治背景讓我數次入團入黨政審不合格、申報師范學校失敗,滿腔熱血無法施展,對人生感到迷茫。恰逢居委會和上山下鄉知青辦在大力號召群眾上山下鄉,我認為農村是廣闊的天地,青年人可以大有作為,加之農村比較單純,不會再考慮我的政治問題,于是我在1964年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下鄉。
我下鄉的公社是城步縣苗族自治區白毛坪公社。公社有37個知青,只有4個女孩。鄉下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最初我與其他三位女知青住在庵堂里,后來公社向大隊秘書借了房子,里面有兩張床,我們兩人擠在一張床上睡覺。后來我當了知青教師,就一個人住在學校里。床上連席子都沒有,就把稻草放在床上,然后人睡在稻草上。除了在課余時幫助鄉親們干農活積工分,我們每月還領5元的民辦教師補助。購置生活必需品要走很遠的路,交通不便、書信不通,與外界基本沒有聯系。
我們也無法適應當地文化。當時苗族地區民風尚未開化,年輕人都講苗語,喜歡對著我們說臟話,而且在男女問題上比漢族開放。下鄉時,干部特意對當地群眾強調,我們是下鄉的知青,需要像保護軍婚一樣保護,誰觸犯這一條就要坐牢。當地學生和青年人就不敢對我們毛手毛腳,但有些人還是油腔滑調。
二、實現夢想,站上講臺
1965年3月,下鄉幾個月后,考慮到我的文化程度,再加上我老實、聽話,大隊選我做知青教師。大隊共有四個老師,我所在的生產隊就只有我一個。
我去的學校在一座半山腰間的庵堂里,只有1到3年級,所有學生都在一起學習,一共21個學生,都來自周邊的農戶。學校沒有教學大綱,也沒人指導,基本是以前我的老師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學生,教學方式非常隨意。所有科目和教學內容都是我自己決定,課程有語文、數學、音樂與體育,語文課就教《毛主席語錄》,數學就教基本的數字和運算,體育課有踢毽子、踏步等活動,音樂課以唱歌為主。沒有固定的課程表,基本是一門課教累了就換一門。教學時長也不確定,一般視當時情況而定,有時60分鐘,有時不到二三十分鐘,但我也會按著我的教學提綱走。當時沒有考試,無法判斷教學質量,也沒人在意。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由生產隊負責發放,總額較少,但仍有黑板和桌椅等基礎教學設施,能夠滿足教師的基本教學需要。
當時學校只有我一個老師,因此我既是老師又是校長,我不但負責教學,還要負責學校的一切事項。公社對教學質量較少過問,但是生產隊的教學還是受公社文教專干的檢查監督,公社偶爾也會在暑假請資深教師為農村年輕教師開展集中培訓,盡可能地提升教師的教學質量。
雖然條件艱苦,事務煩瑣,但幸運的是,當地老鄉對知青十分尊重,照顧我們的起居,不但熱情款待我們,而且還教我們做農活。平日我很少出工,所以同齡的朋友也不多,但我常與周邊年長的老奶奶聊天。正月去給老人家拜年,老人們通常舀一勺甜酒、一勺南瓜,混在一起給我們吃,或者給我們喝油茶,非常客氣熱情。過年如果哪家殺豬了,我們還可以順便分一些。有個比我現在年齡還大的老奶奶,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客氣。我懷著孩子要轉點的時候,她就給我遞了一包自己種的黑豆子,還跟我說:“老劉啊,這個吃了好,能催奶。”鄉親們的悉心照料幫助我度過鄉下的漫長歲月。
學生也成為我快樂生活的源泉。當時學生們較少有“知識改變命運”這樣的想法,但很聽話,對學習比較熱情。他們見到我會輕快地打招呼,我們會一起玩游戲、跳皮筋、踢毽子,師生關系非常好。學生的家庭條件都不好,但思想非常單純,有時候走到我面前咧著嘴問我:“果里有個干紅薯,老師你恰嗎?”①大多數居民、家長和學生對教師非常尊敬,這都是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傳統,所以我在那很少受到別人的刁難。
三、婚后轉點,再次從教
我與老張因同在一個大隊相熟,老張時常接送我去大隊和公社開會,就這樣慢慢在一起了。1968年冬天,老張被調到城步,我只能跟著老張一起走,到他家鄉去了。
到老張家還沒一個月,兒子就出生了。我躺在床上想:“我該怎么辦,做什么呢?”正好他們生產隊開會,沒有會計,有人提議讓我當,于是在兒子滿月后,我參加公社的培訓,做了一名會計,一干就是
十年。
接著老張調到西巖中學教書,恰逢學校公開招聘民辦教師,我就馬上報名了。當時我帶著孩子,也沒什么時間復習,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著后,就點著煤油燈在床邊看看數學公式。當時要考政治、語文、數學三門,去考政治的路上我幸運地瞟見墻上寫著“什么是憲法”的答案,因此也多得了2分;加之我從小在市區接受教育,比當地人的基礎扎實些,就考上了當地民辦教師,只在星期日或者休息時間給大隊決算、統分。
我所在的學校是所完整的大隊小學,一到六年級都有。我教的班有40多個學生,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不是很高,還經常隨性地請假不來上課,但大多數學生畢業后會繼續讀初中和高中,也有學生能一直讀上去,出人頭地。低年級是由一個老師包班教學,固定科目有語文、數學;高年級有單獨的數學老師和語文老師;體育課上得比較少,沒有專職的體育老師,也沒有場地;音樂課一學期一兩次,主要教唱歌、認譜。
當時學校有了成套的教科書,老師們有教學任務,但沒有特定的教學目標,教學非常隨意,只要把書上的內容教完就好,一節課教不完就分兩節課;老師間也不流行互相聽課,都是彼此獨立互不干涉。我剛去的時候,沒有范本,也沒備過課,就按自己構思的教。語文課就學拼音、漢字,數學就學基本的算術,都跟著教材走。開始有基于教材內容的考試,表明教學質量逐漸開始受到重視。
學校一共有7名老師,只有1名公辦教師,其余都是通過考試的村里的民辦教師,后來大多轉正了。當時老師培訓的機會極少,老師如果想提高自己,就去參加中函,有專門的老師教語文、數學、政治等學科內容,寒假集中學習10~15天,暑假集中學習20~25天。那時候我去參加中函,集中學了兩年,后來學習沒有結束我就回城了,也沒有繼續上,所以沒有拿到中函的畢業證。
四、自愿返城,輾轉歸隊
1979年,大規模知青返城,我也自愿返回家鄉。回家后首先就面臨工作問題,下鄉支教時間雖長,但并未給我特別的待遇,我始終是一名民辦教師。我們一家四口回城后先與父親住在一起,過了兩個月,我帶著小孩租了房,房子里橫豎擺著兩張床,手都能直接摸到屋頂。無工作的困苦讓我只得開口問父親討要孩子的學費。
走投無路之際,我找到父親學校的老師,請求他幫忙找工作,隨即被介紹到資江小學當14天代課教師,接著我又在向陽小學代課14天。隨后,我又在沙井頭小學代課一個月。我思忖,代課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我就向教育局領導求助,說我不求工作好壞,只要能解決吃飯問題即可。市政府比較照顧返城知青,第二天就將我安排到水利機廠幼兒園工作,成為廠里的正式員工。在幼兒園,大、中、小班我都帶過,但我還是想回學校教書。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被轉到邵新小學教一年級,區里來聽課覺得我上得不錯,從此校長也就放心下來。在邵新學校的七八年間,我一直是以工代教,雖然被稱為老師,但是享受的是保育員的待遇,后與廠長商討后,給了我幼師的薪資。
我父親通過不斷寫報告說明情況,成功地洗掉了檔案里“歷史反革命”這幾個字,政治問題徹底解決了。1988年,我提供了政審的材料。教育局派人調查情況,替我落實了政策,發布了紅頭文件,說我這是歸隊,承認我自1965年開始的教齡,然后就把我分到了前進小學。學校書記聽說是落實政策來的,認為落實政策的都是不能教書的,并不信任我,甚至一開始跟我說學校不缺人,拒絕在我的調令上簽字。而我認為我應當服從調令,聽從教育局的安排,因此在不斷的求情后,我被安排教一年級。后來三年級一位老師休產假,校長請我代課。全區統考時,我教的兩個班在區里分別名列第三和第五,校長和書記非常滿意。隨后,六年級的老師生病住院,我帶六年級,全區統考時數學考了第一,這也就更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我原有的看法。我曾指導一名學生參加華羅庚數學競賽得了冠軍,我也因此得到“優秀教練員”稱號。后來,我一直擔任學校教研組組長,負責和管理學校的數學教學。
我在當知青教師時并未受過專門的訓練,也不是師范學校畢業的師范生,普通話、板書等方面還存在問題。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源于我堅持不懈的努力。剛從城步回來上課時,我也有點膽怯,擔心別人揭我的短。當時,邵陽九縣三區要選拔一位教師到市區上課,我就去聽課,再忙都不間斷。市里區里有時會請專家上課,我也去聽課,做好筆記,虛心求教。很多上課的形式和教學的內容我就是從聽課中學到的。正是上山下鄉的這段經歷,教會我要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①,從不抱怨,只腳踏實地地干,通過努力和付出得到別人的認可。此外,知青經歷也教會我不要有私心,不要計較,無論在鄉下還是回城我都先等別人選完,我再拿剩下的。
現在國家越來越重視鄉村教育,政策不斷向農村傾斜,農村教育的投入也逐漸上升,但是許多教師還是不愿意去農村,這是整個社會環境的責任。要改善這樣的情況,需要對學校教育、社會風氣、個人精神品質都給予充分的重視。在我看來,“知青教師精神”就能起到很好的帶頭作用,凈化教師的從教信念,促進教師奮勇前行,培養真正關心學生、樂于從教、善于從教的明日之師。對我來說,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仍然愿意去偏遠的山區執教,因為我熱愛這個職業,愿意無怨無悔為之付出!
訪談后記
劉如英老師是一位了不起的知青教師。憑借對教師工作的熱情,她在國家需要她的時候毅然下鄉,忍受貧苦、甘于平淡,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崗位,并始終秉持對教育的初心。返城后,她絲毫沒有享受知青教師頭銜帶來的名利,輾轉奔波后,終于成為一名正式教師。從教近40年,她感恩那段知青歲月,正是那段困難的日子,鍛造了她的教師之魂,教會她作為一名教師要不存私心,對學生有情意,不因家庭富裕與否隨意評判學生,鼓勵和認可困難的學生;不論教書地點如何,都要無怨無悔為教育事業獻身。劉如英老師對每位學生都印象深刻,談起學生來如數家珍。在她收藏的照片和其他資料里,我能看到她作為人民教師的愛與擔當,感受到她無私的奉獻精神。
在此向劉如英老師表達敬意,對她不辭辛勞數次接受訪談表示感謝,并慶幸自己有此機會得以記錄她這段知青歲月!感謝我的妹妹,幫我聯系老師并陪同我一起進行訪談。最后,衷心感謝胡艷老師對我的悉心指導!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口述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