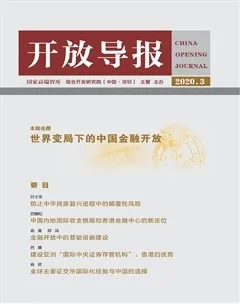空間視閾下經(jīng)濟(jì)失衡問(wèn)題考察


[摘要] 近年來(lái),我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失衡在空間維度上主要表現(xiàn)為東部與中西部發(fā)展差距收窄、南北差距擴(kuò)大、城市群一體化水平及發(fā)展動(dòng)能逐步分化、核心城市的引力和輻射作用不強(qiáng)等特征。要從構(gòu)建系統(tǒng)性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提升城市群協(xié)同創(chuàng)新水平、完善跨區(qū)域利益共享機(jī)制出發(fā),在更大范圍上優(yōu)化對(duì)外開(kāi)放格局、更深層次上提升內(nèi)外開(kāi)放質(zhì)量、更大力度上健全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為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注入新動(dòng)能。
[關(guān)鍵詞] 開(kāi)放? ?區(qū)域經(jīng)濟(jì)? ?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hào)] F061.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4-6623(2020)03-0101-06
西部大開(kāi)發(fā)、東北振興等系列國(guó)家戰(zhàn)略的實(shí)施,有力地推動(dòng)了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跨越式發(fā)展,極大地改善了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面貌,但由于區(qū)域間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不平衡問(wèn)題依舊突出。進(jìn)一步厘清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失衡的原因,更好地促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仍是當(dāng)代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命題。
一、空間視閾下區(qū)域經(jīng)濟(jì)
發(fā)展失衡的主要表現(xiàn)
(一)東部與中西部地區(qū)發(fā)展差距高位收斂,南北方經(jīng)濟(jì)不平衡現(xiàn)擴(kuò)大跡象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始終領(lǐng)先于中西部地區(qū),并呈現(xiàn)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1978—1991年,地區(qū)間絕對(duì)差距由216元/人增至1213元/人,發(fā)展差距呈現(xiàn)緩慢擴(kuò)大的態(tài)勢(shì)。1992—2002年,絕對(duì)差距由1579元/人上升至7699元/人,擴(kuò)大速率為17.74%。相對(duì)差距也由50.39%擴(kuò)大至55.85%,增長(zhǎng)了5.46個(gè)百分點(diǎn),發(fā)展差距迅速擴(kuò)大。2003年至今,地區(qū)間發(fā)展水平相對(duì)收窄,區(qū)域間人均GDP相對(duì)差由56.52%逐步下降至39.69%,發(fā)展差距呈現(xiàn)高位收斂的態(tài)勢(shì)。
然而,南北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距卻于近年呈現(xiàn)出擴(kuò)大跡象。自2012年以來(lái),北方相對(duì)南方地區(qū)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積累的發(fā)展優(yōu)勢(shì)逐漸喪失,并在2015年被南方地區(qū)所超越。2012—2018年,南方相對(duì)北方地區(qū)絕對(duì)差從-2474元/人快速上升至9165元/人,擴(kuò)大速率平均達(dá)到118%。特別是2015年,區(qū)域間絕對(duì)差擴(kuò)大速率更是達(dá)到階段性峰值325.58%。同時(shí),南北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相對(duì)差也自2014年達(dá)到階段性底部(1.44%)后迅速躍升至2018年的13.47%。區(qū)域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快速波動(dòng)加速了南北方經(jīng)濟(jì)總量的分化,北方GDP總量占全國(guó)比重由2012年的29.08%銳減至2018年的24.87%,其相對(duì)南方GDP總量更是從41%萎縮至31.1%,達(dá)到1978年以來(lái)最低水平。
(二)城市群一體化水平與發(fā)展動(dòng)能逐漸分化
由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在空間分布上往往表現(xiàn)出非均衡特征,一國(guó)必然會(huì)存在少數(shù)城市群發(fā)揮著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極”的重要功能(Gottmann J,1957),城市群是區(qū)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群的發(fā)展需要以產(chǎn)業(yè)為依托,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與分工格局是實(shí)現(xiàn)城市群高水平協(xié)同的重要基礎(chǔ)與核心條件。受制度性、結(jié)構(gòu)性、發(fā)展階段等因素影響,京津冀城市群較長(zhǎng)三角、粵港澳大灣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與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仍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近年來(lái),在國(guó)內(nèi)外城市群競(jìng)爭(zhēng)日趨加劇的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二三產(chǎn)業(yè)能級(jí)總體呈現(xiàn)出一定的弱化態(tài)勢(shì)。2008—2017年,京津冀地區(qū)工業(yè)增加值占全國(guó)工業(yè)增加值比重約為8.89%,下降了1.63個(gè)百分點(diǎn);服務(wù)業(yè)增加值占全國(guó)比重由11.78%降至11.33%,下滑了0.45%。同期,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工業(yè)增加值占全國(guó)工業(yè)增加值比重達(dá)到26.2%,僅下降0.1%,服務(wù)業(yè)增加值占全國(guó)比重卻上升了1.1個(gè)百分點(diǎn),達(dá)到24.3%。京津冀產(chǎn)業(yè)能級(jí)的弱化以及長(zhǎng)三角、粵港澳大灣區(qū)的快速崛起,使諸多北京企業(yè)越過(guò)京津冀直接輸出至東部城市群,且遷出企業(yè)多以“科學(xué)研究和技術(shù)服務(wù)業(yè)”“租賃和商務(wù)服務(wù)業(yè)”等高附加值、知識(shí)密集型企業(yè)為主,形成了群體性“蛙跳現(xiàn)象”。
(三)核心城市對(duì)外圍區(qū)域的引力作用和輻射功能存在局限性
核心城市是城市群空間形態(tài)的重要構(gòu)成,具有創(chuàng)新要素與高端產(chǎn)業(yè)高度集聚等諸多特征。中心城市的引領(lǐng)和輻射作用,對(duì)增強(qiáng)城市群內(nèi)部各規(guī)模等級(jí)城市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促進(jìn)城市群整體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意義重大。然而,受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影響,當(dāng)前多數(shù)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引領(lǐng)作用并未充分發(fā)揮,特別是部分省會(huì)城市和副省級(jí)城市問(wèn)題凸顯(張學(xué)良等,2020)。
(其中:Fab表示城市a與城市b之間的空間聯(lián)系強(qiáng)度,Pa和Pb表示兩城市年末總?cè)丝跀?shù),Qa和Qb為兩城市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Ia和Ib表征兩城市專利授權(quán)量,Dab代表兩城市間的空間距離),我們分別對(duì)京津冀、長(zhǎng)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空間聯(lián)系強(qiáng)度進(jìn)行測(cè)算。結(jié)果顯示(表1—表3),各城市群核心城市對(duì)外聯(lián)系強(qiáng)度均以某幾個(gè)鄰近城市為出發(fā)點(diǎn),向外圍逐漸遞減,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具有地理鄰近優(yōu)勢(shì)的北京、天津、廊坊,其經(jīng)濟(jì)與創(chuàng)新的空間聯(lián)系最為緊密;長(zhǎng)三角城市群中以上海、蘇州、無(wú)錫、嘉興、南通、杭州、寧波間聯(lián)系強(qiáng)度最高;珠三角城市群則以廣州—佛山、廣州—東莞、深圳—東莞、深圳—廣州間引力最強(qiáng)。因此,在引力隨距離增大而快速衰減的情況下,如果核心城市的引力作用不夠強(qiáng),就會(huì)導(dǎo)致諸多地處邊緣位置的中小城市與周邊城市空間聯(lián)系出現(xiàn)斷層。可以看到,京津冀、長(zhǎng)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內(nèi)部核心城市的引力作用普遍較弱,大多局限于幾個(gè)地理臨近的核心城市之間,對(duì)外圍及邊緣城市的帶動(dòng)作用有限。另外,一些核心城市的輻射過(guò)程一定程度上還會(huì)屏蔽周邊其他次核心城市輻射功能的發(fā)揮,對(duì)周邊次核心城市發(fā)展產(chǎn)生抑制作用,從而進(jìn)一步擴(kuò)大核心—外圍城市之間的發(fā)展差距。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天津作為雙核心城市對(duì)石家莊等次核心城市對(duì)外輻射就具有屏蔽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輻射影響的范圍(趙正等,2017)。
二、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開(kāi)放政策實(shí)施力度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差異,致使區(qū)域經(jīng)濟(jì)差距加速擴(kuò)大
區(qū)域政策是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優(yōu)化空間布局結(jié)構(gòu)、提高資源空間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孫久文等,2014)。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不平衡發(fā)展受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中國(guó)非均衡、碎片化、分批次的對(duì)外開(kāi)放戰(zhàn)略影響顯著(劉勇等,2017)。沿海地區(qū)憑借生產(chǎn)要素的自由流動(dòng)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自主權(quán)的擴(kuò)大,充分利用市場(chǎng)化方式配置資源,率先融入全球經(jīng)濟(jì),并推動(dòng)地區(qū)要素生產(chǎn)率和利潤(rùn)率不斷提高,由此吸引了中西部及北方地區(qū)勞動(dòng)力、資本等生產(chǎn)要素的集聚。而中西部和北方地區(qū)由于吸引外資能力薄弱,在對(duì)外開(kāi)放進(jìn)程中逐漸淪為能源、資源等要素的提供者,無(wú)法直接參與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體系,從而阻礙了地區(qū)生產(chǎn)效率的提升和技術(shù)進(jìn)步。
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發(fā)展,東部和南方沿海區(qū)域依托良好的區(qū)位條件和制度優(yōu)勢(shì),擺脫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的束縛,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chǎng)化體系,進(jìn)而向全球價(jià)值鏈更高環(huán)節(jié)邁進(jìn)。中西部與北方地區(qū)卻只能繼續(xù)承接?xùn)|部地區(qū)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其產(chǎn)品技術(shù)、品牌含量均較低,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不足,處于價(jià)值鏈底部,致使人才等生產(chǎn)要素進(jìn)一步大量流失,發(fā)展空間嚴(yán)重受限。特別是自2012年經(jīng)濟(jì)進(jìn)入新常態(tài)以來(lái),由于北方經(jīng)濟(jì)長(zhǎng)期高度依賴于交通運(yùn)輸設(shè)備、金屬冶煉和制品等重化工產(chǎn)業(yè),發(fā)展慣性大、轉(zhuǎn)型慢、缺乏韌性,其經(jīng)濟(jì)增速較南方地區(qū)回落速度和幅度更大。2018年,北方地區(qū)GDP增速相比2012年降幅高達(dá)4.16%,同期南方地區(qū)則僅降低2.03個(gè)百分點(diǎn),下滑幅度是北方地區(qū)的一半,進(jìn)一步導(dǎo)致南北發(fā)展差距的擴(kuò)大。可見(jiàn),雖然開(kāi)放政策的實(shí)施有效推動(dòng)了重點(diǎn)區(qū)域短時(shí)間內(nèi)的快速崛起,但實(shí)施力度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上的差異,也加重了地區(qū)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失衡,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東快西慢” “南升北降”的發(fā)展格局日趨強(qiáng)化。
(二)營(yíng)商環(huán)境不完善,加劇三大城市群發(fā)展動(dòng)力的空間極化
企業(yè)是區(qū)域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主體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微觀載體,而營(yíng)商環(huán)境的優(yōu)劣則直接關(guān)系到企業(yè)的選址與布局,對(duì)促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jì)空間平衡意義重大。近年來(lái),在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各地通過(guò)削減行政審批事項(xiàng)、制定負(fù)面清單等方式,有效降低了企業(yè)制度性交易成本,營(yíng)商環(huán)境得到極大改善。然而,隨著我國(guó)以“城市”為主導(dǎo)的競(jìng)爭(zhēng)格局向以“城市群”為主導(dǎo)的競(jìng)爭(zhēng)新格局加速演變,城市群日益成為承載發(fā)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態(tài),而其內(nèi)部地區(qū)間營(yíng)商環(huán)境的整體水平與競(jìng)爭(zhēng)合力,日益成為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指標(biāo)。如京津冀城市群內(nèi)部天津、河北兩地營(yíng)商環(huán)境發(fā)展水平較北京具有較大差距,特別是河北在要素供給能力、產(chǎn)業(yè)配套體系、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水平、行政服務(wù)效率等方面短板十分突出,加之地區(qū)性政策又缺乏基于城市群的一體化設(shè)計(jì),橫向協(xié)調(diào)不暢,諸如創(chuàng)新人才、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資質(zhì)互認(rèn)等基礎(chǔ)性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缺失,放大了跨區(qū)域營(yíng)商環(huán)境方面的缺陷。在北京實(shí)施減量發(fā)展的背景下,一大批受“雙控”(控制人口規(guī)模/建設(shè)規(guī)模)、“三線”(嚴(yán)守人口總量上限/生態(tài)控制線/城市開(kāi)發(fā)邊界)約束而輸出的北京企業(yè)卻在津冀“接不住、落不下”,轉(zhuǎn)而“蛙跳”至長(zhǎng)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并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新創(chuàng)企業(yè),以及技術(shù)、資本等創(chuàng)新要素的隨之外流。
(三)利益共享與補(bǔ)償機(jī)制缺失,致使城市間實(shí)質(zhì)性合作嚴(yán)重不足
利益共享是區(qū)域合作的總體目標(biāo),利益補(bǔ)償是建立合作的基本保障。目前,跨行政區(qū)經(jīng)濟(jì)合作主要以園區(qū)共建、產(chǎn)業(yè)鏈轉(zhuǎn)移等形式展開(kāi),如長(zhǎng)三角城市群以上海為龍頭,浙江、江蘇、安徽共同參與共建的園區(qū)已高達(dá)數(shù)百家,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涉及機(jī)械制造、醫(yī)藥化工、服裝紡織、電子信息等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則以北京中關(guān)村為核心,持續(xù)向津冀等地區(qū)輻射共建園區(qū),包括天津?yàn)I海中關(guān)村科技園、京津中關(guān)村科技新城、保定中關(guān)村創(chuàng)新中心等。然而,雖然各城市群園區(qū)共建項(xiàng)目數(shù)量眾多,但實(shí)際運(yùn)行效果卻并不理想。推進(jìn)過(guò)程往往涉及跨區(qū)域投資、企業(yè)轉(zhuǎn)移、生態(tài)補(bǔ)償?shù)认嚓P(guān)稅收轉(zhuǎn)移與分成、產(chǎn)值計(jì)算、補(bǔ)償機(jī)制等問(wèn)題,實(shí)施難度大,造成多數(shù)合作項(xiàng)目?jī)H停留在高層次戰(zhàn)略協(xié)議階段,缺乏后續(xù)落實(shí)與跟進(jìn)。少數(shù)已啟動(dòng)項(xiàng)目又普遍存在產(chǎn)業(yè)重復(fù)建設(shè)、同質(zhì)化嚴(yán)重、地區(qū)比較優(yōu)勢(shì)無(wú)法充分體現(xiàn)等問(wèn)題。
跨行政區(qū)利益分享不明晰,源于多方面體制機(jī)制障礙。由于國(guó)家層面并未給予相關(guān)的制度安排,使得多數(shù)地方性合作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地方政府為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而缺乏推進(jìn)動(dòng)力。同時(shí),一些已取得國(guó)家授權(quán)的地區(qū),由于政策的玻璃門檻較高導(dǎo)致可操作性不足,政策效果同樣難以達(dá)到預(yù)期。如財(cái)政部和國(guó)家稅務(wù)總局于2015年印發(fā)了《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對(duì)接企業(yè)稅收收入分享辦法》,明確“由遷出地政府主導(dǎo)、符合遷入地區(qū)產(chǎn)業(yè)布局條件、且遷出前三年內(nèi)年均繳納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營(yíng)業(yè)稅‘三稅大于或等于2000萬(wàn)元的企業(yè),納入分享范圍”。此政策對(duì)企業(yè)納稅額要求過(guò)高,鮮有遷移企業(yè)能滿足該標(biāo)準(zhǔn),導(dǎo)致該政策效果無(wú)法有效發(fā)揮(趙莉,2020)。另外,現(xiàn)行總分機(jī)構(gòu)企業(yè)所得稅匯總納稅等制度也缺乏對(duì)不同企業(yè)所在行業(yè)差別、外部效應(yīng),以及總分機(jī)構(gòu)在不同地區(qū)所需生產(chǎn)要素成本的差異化考慮,而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統(tǒng)一按照“五五分成”的方式計(jì)算,難以有效促成跨行政區(qū)的合作形成合力。
三、以更高質(zhì)量開(kāi)放促進(jìn)
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基本邏輯
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是對(duì)地區(qū)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效果、發(fā)展能力與發(fā)展機(jī)會(huì)平衡的綜合建構(gòu)(孫志燕等,2019)。“效果平衡”“能力平衡”“機(jī)會(huì)平衡”三者之間互為依存、相輔相成。其中,機(jī)會(huì)平衡是不同地區(qū)謀求公平發(fā)展的基本保障,能力平衡是實(shí)現(xiàn)空間協(xié)調(diào)的根本路徑,而不同空間尺度下經(jīng)濟(jì)區(qū)、城市群、核心與外圍城市之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效果的空間平衡則是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最終目標(biāo)(賈珅,2019)。
不平衡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下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效果平衡并不意味著各地區(qū)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發(fā)展速度的絕對(duì)均衡,而是要突出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全面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果能夠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個(gè)區(qū)域,保障不同地區(qū)的人民能夠共享發(fā)展紅利。對(duì)外開(kāi)放是形成中國(guó)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塑造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格局的基本力量,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格局的變化與對(duì)外開(kāi)放的空間格局變化緊密相關(guān)。實(shí)現(xiàn)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從根本上推動(dòng)“效果平衡”,就必須改變沿海強(qiáng)內(nèi)陸弱、東快西慢、南升北降的局面,在更大范圍上優(yōu)化開(kāi)放的空間布局,推動(dòng)形成陸海內(nèi)外聯(lián)動(dòng)、東西雙向互濟(jì)的區(qū)域開(kāi)放新格局。
發(fā)展能力的空間平衡是促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的根本路徑。由于地區(qū)間區(qū)位條件、資源稟賦、發(fā)展階段等基礎(chǔ)性差異的存在,不同地區(qū)發(fā)展能力也各不相同,集中表現(xiàn)為創(chuàng)新能力、財(cái)政能力、治理能力等諸多方面。其中,創(chuàng)新作為新時(shí)期引領(lǐng)區(qū)域發(fā)展的第一動(dòng)力,其強(qiáng)弱直接關(guān)系到區(qū)域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進(jìn)程,是影響經(jīng)濟(jì)空間格局最為關(guān)鍵的力量。當(dāng)前,東部及南部部分城市創(chuàng)新引領(lǐng)型經(jīng)濟(jì)已日趨顯現(xiàn),而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在研發(fā)投入、人才要素供給等方面則遠(yuǎn)遠(yuǎn)落后,甚至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孔雀東南飛”現(xiàn)象。因此,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要改變這種創(chuàng)新滯后、要素流失、被動(dòng)追趕的局面,就必須在更深層次上提升內(nèi)外開(kāi)放質(zhì)量,以城市群為單元建設(shè)創(chuàng)新共同體,突出核心城市對(duì)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創(chuàng)新輻射,帶動(dòng)城市群競(jìng)爭(zhēng)力的整體躍升,在區(qū)域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條件下,推動(dòng)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的均衡發(fā)展。
發(fā)展機(jī)會(huì)的空間平衡是促進(jìn)地區(qū)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基本保障。在動(dòng)態(tài)開(kāi)放的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中,發(fā)達(dá)地區(qū)占據(jù)發(fā)展高位,其與戰(zhàn)略疊加所產(chǎn)生的紅利引發(fā)強(qiáng)大的虹吸效應(yīng)。如果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既沒(méi)有優(yōu)越位勢(shì),又缺乏強(qiáng)有力的戰(zhàn)略支持,那么在“循環(huán)累積”效應(yīng)的影響下,其發(fā)展將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發(fā)達(dá)地區(qū)。在此情形下,僅僅依靠市場(chǎng)力量難以有效調(diào)節(jié)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失衡問(wèn)題,甚至在規(guī)模效應(yīng)的作用下會(huì)加劇這種非均衡狀態(tài)(Myrdal G,1957)。因此,要實(shí)現(xiàn)地區(qū)間的機(jī)會(huì)平衡,就必須在更大力度上健全開(kāi)放體系、提高制度質(zhì)量,以加強(qiáng)對(duì)內(nèi)開(kāi)放為重點(diǎn)推動(dòng)政府治理協(xié)同,突破行政區(qū)劃壁壘,建立區(qū)際利益共享與補(bǔ)償機(jī)制,從而為不同地區(qū)經(jīng)濟(jì)協(xié)作與公平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
四、以高水平開(kāi)放推進(jìn)
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基本思路
能否有效遏制經(jīng)濟(jì)落差擴(kuò)大勢(shì)頭,建立起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新格局,是關(guān)系到開(kāi)發(fā)西部、崛起中部、振興東北、加快發(fā)展東部等戰(zhàn)略目標(biāo)能否順利實(shí)現(xiàn)的重大問(wèn)題。因此,要進(jìn)一步從構(gòu)建系統(tǒng)性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提升城市群協(xié)同創(chuàng)新水平、完善跨區(qū)域利益共享機(jī)制出發(fā),在更大范圍上優(yōu)化對(duì)外開(kāi)放格局、更深層次上提升內(nèi)外開(kāi)放質(zhì)量、更大力度上健全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以更高水平內(nèi)外開(kāi)放為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注入新動(dòng)能。
(一)建立系統(tǒng)性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在更大范圍上優(yōu)化內(nèi)外開(kāi)放格局
隨著全球產(chǎn)業(yè)分工的深度調(diào)整以及國(guó)內(nèi)社會(huì)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轉(zhuǎn)變,進(jìn)一步構(gòu)建系統(tǒng)性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優(yōu)化內(nèi)外開(kāi)放格局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由高速增長(zhǎng)邁向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客觀要求。為此,東部沿海地區(qū)應(yīng)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產(chǎn)業(yè)變革窗口期,持續(xù)擴(kuò)大服務(wù)業(yè)對(duì)外開(kāi)放程度,提升服務(wù)貿(mào)易出口競(jìng)爭(zhēng)力,推動(dòng)服務(wù)貿(mào)易與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的高質(zhì)量、融合化發(fā)展。特別是要加強(qiáng)我國(guó)與“一帶一路”沿線相關(guān)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服務(wù)貿(mào)易合作,充分發(fā)揮我國(guó)在信息技術(shù)、金融、建筑等領(lǐng)域,中東歐等國(guó)家和地區(qū)信息產(chǎn)業(yè)研發(fā)能力強(qiáng)、人才資源豐富,東盟運(yùn)輸、文化旅游資源富集等各地區(qū)比較優(yōu)勢(shì),加快形成優(yōu)勢(shì)互補(bǔ)、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在此基礎(chǔ)上,以自由貿(mào)易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為抓手,引導(dǎo)東部沿海城市加工貿(mào)易向中西部、東北等地區(qū)進(jìn)行梯度轉(zhuǎn)移,深化全球價(jià)值鏈的國(guó)內(nèi)環(huán)節(jié),推動(dòng)欠發(fā)達(dá)地區(qū)進(jìn)一步融入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體系。對(duì)接?xùn)|北振興、中部崛起、西部大開(kāi)發(fā)等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及時(shí)補(bǔ)齊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基礎(chǔ)設(shè)施、公共服務(wù)等短板,并優(yōu)先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中心城市推動(dòng)新型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加大對(duì)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領(lǐng)域重大項(xiàng)目和創(chuàng)新平臺(tái)的布局,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集聚人才、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資本創(chuàng)造條件,以國(guó)內(nèi)區(qū)域價(jià)值鏈分工的協(xié)同升級(jí)促進(jìn)區(qū)域均衡發(fā)展。
(二)提升城市群協(xié)同創(chuàng)新水平,在更深層次上提升內(nèi)外開(kāi)放質(zhì)量
隨著新科技革命和產(chǎn)業(yè)變革的孕育興起,世界競(jìng)爭(zhēng)格局的深刻變革對(duì)系統(tǒng)的創(chuàng)新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更加注重增強(qiáng)內(nèi)外開(kāi)放質(zhì)量,以創(chuàng)新為引領(lǐng)、以城市群為單元,促進(jìn)區(qū)域的平衡發(fā)展。進(jìn)一步擴(kuò)大科技全球化合作,在世界范圍內(nèi)整合創(chuàng)新資源。以我國(guó)頭部企業(yè)為牽引,推動(dòng)科技企業(yè)“走出去”,在全球布局研發(fā)合作網(wǎng)絡(luò),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在新一輪科技全球化浪潮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以國(guó)內(nèi)城市群為主體,推動(dòng)全面創(chuàng)新改革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將傳統(tǒng)行政區(qū)劃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城市群經(jīng)濟(jì)。建立區(qū)際聯(lián)席會(huì)議制度,在技術(shù)研發(fā)、企業(yè)引進(jìn)、土地批租等方面實(shí)施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一政策、統(tǒng)一服務(wù),形成基于城市群一體化的頂層設(shè)計(jì),提高供給體系的質(zhì)量和效益。突出完善城市群內(nèi)部資源要素跨區(qū)域配置的保障機(jī)制,特別是圍繞重點(diǎn)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加快建立區(qū)域內(nèi)人才、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資質(zhì)互認(rèn)機(jī)制,在要素指標(biāo)轉(zhuǎn)移、企業(yè)異地監(jiān)管、人員待遇保障等方面構(gòu)建要素流動(dòng)大通道,推動(dòng)城市群內(nèi)部營(yíng)商環(huán)境的梯度銜接與整體躍升。
(三)完善跨區(qū)域利益共享機(jī)制,在更大力度上健全內(nèi)外開(kāi)放體系
為推動(dòng)核心城市與周邊區(qū)域加強(qiáng)實(shí)質(zhì)性合作、促進(jìn)多中心都市圈化發(fā)展,要重點(diǎn)解決好跨行政區(qū)利益分享與補(bǔ)償問(wèn)題,平衡城市間財(cái)政收入能力,避免城市群內(nèi)部的非理性博弈和稅源爭(zhēng)搶。推動(dòng)設(shè)立跨行政區(qū)稅收協(xié)調(diào)機(jī)構(gòu),由各城市稅務(wù)部門共同派駐人員,負(fù)責(zé)區(qū)域間稅收事務(wù)的協(xié)調(diào)和調(diào)度工作。借鑒深汕特別合作區(qū)、北京·河北滄州渤海新區(qū)生物醫(yī)藥產(chǎn)業(yè)園等模式,建立以飛地和共建園區(qū)為載體的跨區(qū)域稅收利益分享機(jī)制。建議可按照各地區(qū)出資比例,將跨行政區(qū)項(xiàng)目產(chǎn)生的企業(yè)所得稅、營(yíng)業(yè)稅、增值稅等稅種地方留成部分進(jìn)行區(qū)域間分成;將房產(chǎn)稅、契稅、印花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地方稅種全部留存給所在地政府。圍繞不同城市因定位差異所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jì)利益不平衡問(wèn)題,要建立起地區(qū)間的利益補(bǔ)償機(jī)制。如針對(duì)跨區(qū)域經(jīng)營(yíng)匯總納稅企業(yè),結(jié)合企業(yè)分支機(jī)構(gòu)的實(shí)際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程度以及生態(tài)成本等因素,給予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或承擔(dān)環(huán)境治理責(zé)任地區(qū)一定利益補(bǔ)償,確保區(qū)域間合作收益能夠在各利益主體間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參考文獻(xiàn)]
[1] 孫志燕, 侯永志. 對(duì)我國(guó)區(qū)域不平衡發(fā)展發(fā)展的多視角觀察和政策應(yīng)對(duì)[J]. 管理世界, 2019, 35(8): 1-8.
[2] Gottmann J.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1957(33): 189-200.
[3] 張學(xué)良, 楊朝遠(yuǎn). 發(fā)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中的帶動(dòng)引領(lǐng)作用[N].光明日?qǐng)?bào)·理論周刊, 2020-01-14.
[4] 趙正, 王佳昊, 馮驥. 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空間聯(lián)系及影響測(cè)度[J]. 經(jīng)濟(jì)地理, 2017, 37(6): 60-66+75.
[5] 孫久文, 原倩. 我國(guó)區(qū)域政策的“泛化”、困境擺脫及其新方位找尋[J]. 改革, 2014(4): 80-87.
[6] 劉勇, 宋逸群. 協(xié)同:促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新路徑[M]. 中國(guó)發(fā)展出版社, 2017.
[7] 趙莉. 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背景下北京市屬企業(yè)遷移的政策需求分析[J]. 新視野, 2020(1):73-80.
[8] 賈珅. 新時(shí)代關(guān)于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再思考[M]. 中國(guó)發(fā)展出版社, 2019.
[9] 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