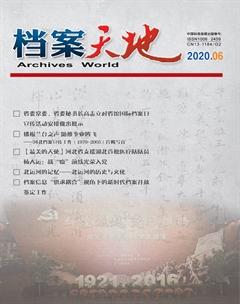晉代繁華地 如今有此樓

古代滄州,歷朝歷代曾經(jīng)所建樓閣臺宇不計其數(shù),伴隨滄桑巨變,綽約風姿幾乎湮沒殆盡,惟余足讓后來懷古尋蹤者徒增唏噓、平添寂寥的一地閑愁罷了,如明清時期,盛名在外,紅極一時的朗吟樓、南川樓等皆已片瓦無存,消逝于時光長河之中。當然,無論古今,在當?shù)乇姸嗝麡侵校蜌v史悠久,名氣長盛不衰者而言,當首推清風樓,尤其元代薩天錫駐節(jié)錄囚鞫讞并題壁留詩的故事令其聲譽日增月盛,文物華輝。其實,今人對于清風樓的過往知之甚少,單是具體位置就因忽略古代滄州行政駐地變遷和受當今清風樓矗立基址地點之誤導而混淆不清。此外,一些以清風樓為題詠對象的古詩在表達記述時所出現(xiàn)的“同名化”現(xiàn)象亦使研辛者細辨不及造成引論時謬誤,后又被以訛傳訛,乃至出現(xiàn)以假亂真之相。因此,有關(guān)于清風樓的種種錯誤解讀,莫不使人引以為憾。
說到清風樓,本地人腦海中呼之欲出的就是位于市區(qū)運河西岸解放橋旁的那座五層重檐結(jié)構(gòu)的樓閣。其實這座樓閣是建于1992年的仿古建筑,原是有關(guān)部門為解決離退休老干部的活動場地而為,可以說和古代清風樓沒有直接的歷史淵源,唯一關(guān)聯(lián)就是“清風”樓名的繼承及“清風”二字背后所寄托的對古今干部清廉為政之勉勵厚望。若從地理的就近原則上看,倒是新清風樓的運河對岸往南不遠處則真正有一處古樓遺址,民國《滄縣志》古跡篇中云:“度帆樓,今在菜市口以南,張棻之樓也。”此樓即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里提到的他外祖父張棻家的度帆樓。從某種意義來說,度帆樓和新清風樓在歷史位置對接與傳承上更恰如其分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新清風樓為偷梁換柱之產(chǎn)物,但這絲毫不影響人們對新建樓宇的喜愛和贊美,并迅速將之視作滄州市區(qū)的文化地標,想來這是當初建設(shè)者們所始料未及的。
與新清風樓不同,古代清風樓相傳建于太康年間,名字由來取自滄州鄉(xiāng)賢尹吉甫贈樊侯詩句中的“穆如清風”,舊有位置應(yīng)在舊滄州,也就是現(xiàn)在的舊州鎮(zhèn)。萬歷《滄州志》記載:“元元統(tǒng)乙亥節(jié)度使薩天錫錄囚駐節(jié)此樓,留題錄詩于后,故老相傳舊州城內(nèi)西南寺即故址。”西南寺即今舊州密云寺遺址,位于舊州城西南處,此寺建于明正德三年,寺旁原有古建舊址,即清風樓之遺存。乾隆《滄州志》引用《畿輔通志》所記亦幾乎無二。清代名儒河間左方燾的《清風樓記》不但詳述了“清風”之寓意,在位置上和時間上也進行了記載:“渤海有清風樓,創(chuàng)建自晉,其來舊矣。”這里的渤海,特指渤海郡曾經(jīng)的行政駐地也就是如今的舊州。清雍正丙午科舉人賈繼曾又有《清風樓懷古》一篇,詩云:“清風尚未休,五壘荒城夜。”《方輿紀要》記載:“五壘故城,在清池舊縣西南二里,漢宣帝封河間獻王子雍為景成候,營別邑于此,使五子分居城中。各筑一壘,因名。”其中清池舊縣駐地舊州城。此處亦從側(cè)面點明了清風樓的位置在舊州城之西南處。遺址距城墻不遠,城外即護城河及成片的泊淀,蓮葉田田,所以薩天錫在《元統(tǒng)乙亥錄囚至滄州清風樓題詩》中才有“城南秋欲盡,寂寞采蓮舟”場景的描述。
至于明嘉靖《河間府志》中云:“清風樓在滄州公館內(nèi),相傳建于晉永康中,元薩天錫元統(tǒng)錄囚至滄州,題詩《清風樓》。”此滄州意為舊滄州,只是所指同一對象的參照物不同罷了。對于有人據(jù)此持長蘆一說,如細加考釋便知不足為憑。首先,根據(jù)萬歷《滄州志》“州城之圖”記載,新滄州駐地(長蘆)標記公館性質(zhì)的署所有兩處,分別為“新公館”和“府館”,由此可知,長蘆處的公館為“新公館”,全稱應(yīng)為“滄州新公館”, 此處刻意標注“新”并不是指建筑剛建未久,而是為區(qū)分舊滄州原有的公館“滄州公館”。其次,舊時雖州治所在搬至長蘆,但人們?yōu)閰^(qū)分新舊地點之別,仍延續(xù)傳統(tǒng),凡涉舊滄州則多以舊滄州或舊州或滄州代指,而新處則以新滄州或長蘆代指,尤以長蘆為多。而且此稱呼甚有歷史傳統(tǒng),薩天錫造訪時就已如此,有詩為證,他曾作《宿長蘆》一首。再者,長蘆在元代“時未有城,故仍以鎮(zhèn)為名”,所以如若在長蘆,則薩天錫詩中的“城南秋欲盡”之句就脫離了據(jù)實記述之真境,變得詞不達意。還有,長蘆在漢代為參戶縣地,人員稀疏,發(fā)展落后,直到北周大象年間基于戰(zhàn)略位置的重要性才被設(shè)置為長蘆縣,其后方有所興。因此在晉代,長蘆此地不足以支撐清風樓興修和延續(xù)的基礎(chǔ)條件,況且此地歷史上經(jīng)常面臨洪水泛濫的威脅,唐開元十六年處于運河之西的長蘆就曾遭遇滅頂之災(zāi),被迫在洪水過后遷至東岸重建。與此相反,舊滄州自西漢初年設(shè)為浮陽縣并作為渤海郡郡治所在地向有興盛的資本,晉代更是蓬勃發(fā)展。清代乾隆年間鹽山名士劉靜年在《過舊滄州吊古》的詩中曾慨嘆道:“城郭猶存唐制度,衣冠不是晉風流”,同時,修于漢代,唐代增筑,宋代重修的舊州城墻至今仍高大煌煌屹立于野便是旁證。因此,總的來看,清風樓故址在舊州當可確定。
清風樓在元代晚期仍繁華壯麗,到明代卻境況直下,最終化為丘墟,萬歷一朝的滄州知府李夢熊在《憶清風樓詩》有“何事年來清風邈,等閑平地一荒丘”之句,足見景象荒涼破敗。究其淪落原由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還是政治因素使然。經(jīng)過元末農(nóng)民起義、靖難之役等戰(zhàn)火的摧殘,隨后州治中心轉(zhuǎn)移,尤其“天順六年,知州賈忠取磚石,城廢”等緣故,使之在連串致命打擊的遭遇下而塌陷,舊有宏麗氣象不復存在。
盡管古清風樓在歷史的滄桑中湮滅于瓦礫黃壤里,但這絲毫并未影響后來者對它的文學追憶和傳頌。在眾多的關(guān)于清風樓的詩歌文學中,有一類作品雖字里行間充斥著清風樓的字眼,但卻是張冠李戴,同名不同樓,如不細加研讀,很容易讓人陷入歷史史實的迷亂中。例如清代傅華冕于《滄酒歌》中敘述滄酒具體位置時稱:“直沽地接清風樓,鯉魚灣水綠似油。紅砂大甕家家篘,昨朝雙鴟遠自五壘城迅寄。”眾所周知,滄酒又叫麻姑酒,產(chǎn)于長蘆運河水畔,而不是舊滄州,所以此“清風樓”非舊滄州清風樓,而句中所提的“五壘城”亦非舊滄州之五壘城。那么,二者又是真正指向何處呢?通過史料記載和實地考察可知,此處清風樓當指朗吟樓,而五壘城則是長蘆璞頭城。明代所修的滄州長蘆新城有城門五座,“北曰拱極,南曰阜民,西曰望瀛,東曰鎮(zhèn)海,小南門曰迎薰”,城池布局狀如古代的璞頭官帽,所以俗稱璞頭城,又因有五個城門樓,亦被人以五壘城代稱(按,非指舊州五壘故城)。再說朗吟樓。朗吟樓,乾隆《滄州志》記載:“在南關(guān)衛(wèi)河之滸,夏月郡人多游息于此。”關(guān)于朗吟樓的歷史淵源,康熙《滄州新志》亦有記述:“呂洞賓,開元中一道士,自號彭蠡主人,索滄酒千余斗,飲竟,乘鶴而去。后人構(gòu)樓肖像以奉之。樓在衛(wèi)河之滸,名朗吟。”于是,明清文人在吟唱朗吟樓時常以“列子乘風”之典應(yīng)和呂洞賓醉酒后仙風道骨飄逸而去的場景。清代諸生樊世翼在《登朗吟樓》一詩中贊曰:“吟殘皓月和清風,數(shù)聲清籟九霄徹”,而明代方俊銑的《中秋高司寇魯司馬熊州伯雅集朗吟樓》更是直接將二者的關(guān)聯(lián)通俗化,詩云:“把酒臨風須起去,碧欄桿外五城頭。”因此,詩人化用清風樓與五壘城于長蘆處也就無可厚非了。
此外,關(guān)于滄酒的具體產(chǎn)地,世人皆知在南川樓旁,而清風樓鯉魚灣又作何解?其實二者毫不矛盾。南川樓,“在南關(guān),昊天觀后”,是一處南北過客及本地百姓頗受歡迎的登臨處。嘉靖乙丑科進士馮惠曾留下《登滄州南川樓》的詩篇:“危樓新建枕蘆洲,過客登臨即勝游。倚醉北瞻天柱近,憑高東望海門悠。鯨波晚帶霞千道,鶴夢秋銜月一鉤。謾道岳陽多壯麗,古今同樂亦同憂。”從詩人的吟唱中可知,南川樓新建未久,且壯觀高大,乃是觀賞與休憩的好去處。當然說到南川樓,與之關(guān)聯(lián)以及使之名聲鵲起的則是滄酒的產(chǎn)地之所。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便曾有關(guān)于滄酒最佳取水之地與南川樓關(guān)系的記載:“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舊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jié)候。水雖取于衛(wèi)河,而黃流不可以為酒,必于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錫罌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沖虛之致。”人們都知南川樓下出美酒,南川樓隨之揚名海內(nèi)。與南川樓相比,朗吟樓名氣更大,建造年代更早,且文化內(nèi)涵更為豐富,尤其朗吟樓與滄酒的關(guān)聯(lián)充滿玄幻色彩,引人遐想,乾隆《滄州志》卷之十三遺聞一目中有:“滄酒得名久矣,相傳呂祖來飲于滄,后人即其地建樓,以岳陽名之,有聯(lián)云:‘黃鶴偶乘滄海月,白云遙帶楚江秋。惜未得題聯(lián)者姓名。劉孝廉香畹為予言之。”朗吟樓周遭景色宜人,酒食不錯,交通又方便,加之明代特別是嘉靖皇帝對道教的推崇,在社會上形成了深遠影響,人們對呂洞賓神仙附會之傳奇信奉有加,在文人雅士的推波助瀾下,朗吟樓的名聲大噪,就連乾隆皇帝都曾留下御詩。如此,在朗吟樓里品飲滄酒成為當時一種風靡時尚。朗吟樓處的滄酒水源實際上就是來自南川樓旁運河地下之暗泉,此泉也被人因酒名而稱作“麻姑泉”。同時,共在運河旁的朗吟樓和南川樓兩樓實際距離不是太遠,兩地附近區(qū)域所在有一運河灣名曰“鯉魚灣”,麻姑泉就在鯉魚灣內(nèi)。乾隆時的汪沆在《飲滄酒懷津門舊游和郭鷗汀韻》詩中自注云:“鯉魚灣在滄州城南,釀酒俱汲此水。”因朗吟樓與滄酒的關(guān)聯(lián)不但時間早,而且朗吟樓的名氣比南川樓更有過之,且酒沾神仙氣易于標榜,因此提及滄酒的所在地言之“清風樓,鯉魚灣”亦為正解。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清風樓作為滄州當?shù)氐囊蛔Ч琶麡窃诓煌瑲v史時期存在著地點不清,名字混亂借用之象。這些隨之連帶衍生出一些歷史謎題讓不明就里之人困惑不已,大大影響了人們對滄州鄉(xiāng)邦區(qū)域文化的記述和解讀。因此,正本清源,對此訛誤進行撥亂反正是大有必要的。如今,作為滄州歷史文化的標志性建筑,無論是即將重建的朗吟樓、南川樓,還是早已移建完成的清風樓,它們以新的面貌重現(xiàn)于新時代并矗立于運河水畔,對于滄州的文化建設(shè)和大運河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不僅有助于人們感受文化魅力,增強歷史自豪感,還能以旅游為抓手,促進本地的經(jīng)濟文化大發(fā)展。
作者簡介:王立成 (滄州市第三中學)教書為業(yè),業(yè)余訪古讀書,最喜天心月圓、芳華滿枝。作品散見于《中華讀書報》《中華文化畫報》《南方周末》《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文物報》《世界知識畫報》等國家級、省級、市級報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