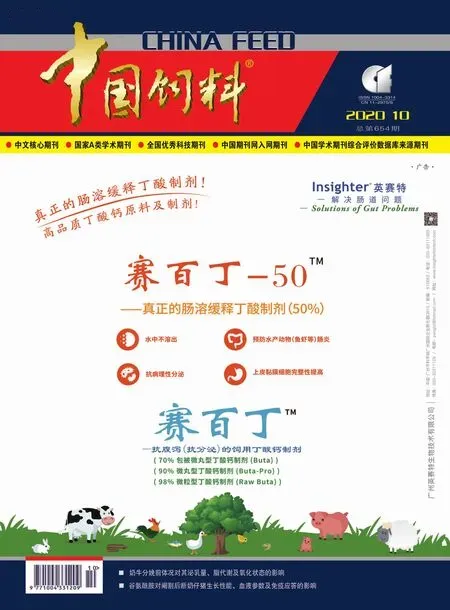纖維分解酶對大麥秸稈體外發酵和消化的影響
王先桂,許華杰,曾 丹
(1.茅臺學院,貴州仁懷 564501;2.貴州珍酒釀酒有限公司,貴州遵義 563000)
反芻動物瘤胃中纖維素分解微生物負責消化植物纖維,這些微生物對纖維降解至關重要。Gado等(2009)研究表明,外源性纖維分解酶的添加可以促進微生物生長和微生物蛋白的合成。Morgavi等(2004)報道,木霉中纖維分解酶促進絲孢桿菌S85對玉米青貯和紫花苜蓿干草的粘附和降解,但未促進純纖維素的降解。將纖維分解酶應用于青貯飼料時,它促進了需氧微生物的活性,并對瘤胃微生物氮摻入產生不利影響(Wang等,2002)。這些結果表明,纖維分解酶在使用前的預處理(水解)可能在調節纖維分解酶的功效方面發揮作用。反芻動物纖維分解酶產品比較廣泛,但它們對養分利用的影響并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旨在檢驗體外培養條件下外源纖維素酶對瘤胃纖維素分解菌生長的影響,并評估纖維酶預處理對其整體效果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1 以大麥秸稈和苜蓿干草為試驗原料,采用產琥鉑酸絲狀桿菌和黃色瘤胃球菌對其進行體外消化試驗。將20捆大麥秸稈和紫花苜蓿干草(每個5 kg)粉碎后過2.0 mm篩網,然后用1.5 mm的篩網收集1.5~2.0 mm的顆粒。試驗用的酶主要以木聚糖酶和β-葡聚糖酶為主,濃度分別為0、30和300 μg/mL,之后參考Wang等(2003)的方法對樣品進行處理,并評估原料中性洗滌纖維降解情況。
1.2 試驗2 大麥秸稈樣品的處理方法同試驗1,試驗共分為6個處理,對照組不經纖維素酶處理,T1組經過纖維素酶處理(150 mg/mL,7.5 mg),T2組纖維素酶處理,體外孵化前預先水解24 h,T3組T2組預處理后用水去除可溶性水解產物,T4組、T3組處理后再經過高壓蒸汽處理,T5組在T3組的基礎上加入與T2組同水平的還原糖。除T2和T3組外,其余12種底物均在批量培養前處理。選擇2頭帶有瘤胃插管的公牛作瘤胃液體供體。在飼喂后2 h收集瘤胃液,通過4層紗布過濾。瘤胃液與緩沖液按1∶2的比例混合,將(15NH4)2SO4(0.75 g/L)作為微生物氮標記物加入緩沖瘤胃液中。孵育和測定干物質降解和揮發性脂肪酸含量的方法參考Wang等(2002)的研究。
1.3 統計分析 試驗數據采用SAS軟件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在試驗1中采用多項式檢驗酶濃度對指標的線性效應,組間差異用Tukey法進行多重比較,P<0.05表示差異顯著。
2 結果與分析
2.1 外源酶及不同微生物孵育對苜蓿草和大麥秸稈中性洗滌纖維降解的影響 由表1顯示,隨著酶濃度的增加,中性洗滌纖維的降解率表現為顯著線性升高(P<0.05)。微生物種類對大麥秸稈中性洗滌纖維降解率的影響無顯著差異(P>0.05),但黃色瘤胃球菌對苜蓿草的消化能力顯著高于產琥鉑酸絲狀桿菌(P<0.05)。產琥鉑酸絲狀桿菌和酶濃度在300 μg/mL時對中性洗滌纖維的降解率具有顯著協同效應(P<0.05)。300 μg/mL酶濃度時,黃色瘤胃球菌對苜蓿草的消化表現最高(P<0.05)。

表1 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及微生物孵育對苜蓿草和大麥秸稈中性洗滌纖維降解的影響
2.2 纖維酶的預處理對大麥秸稈體外發酵氣體產生和干物質降解的影響 由表2可知,與對照組相比,應用外源纖維素酶處理天然大麥秸稈可顯著提高4 h氣體產量及4、12和48 h干物質降解(P<0.05),而外源纖維素酶應用于氨化大麥秸稈顯著提高了4和12 h氣體產量和干物質降解(P<0.05)。與對照組相比,纖維素酶預先水解后顯著提高了天然和氨化大麥秸稈4和12 h氣體產生及4、12和48 h干物質降解(P<0.05)。與T3組相比,T5組顯著提高了4和12 h大麥秸稈氣體產生(P<0.05),同時提高了各孵育時間干物質降解(P<0.05)。無論大麥秸稈類型是什么,T3、T4和T5組在各孵育時間的干物質降解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表2 纖維素酶的預處理對大麥秸稈(天然或氨化)體外發酵氣體產生和干物質降解的影響
2.3 纖維酶的預處理對大麥秸稈體外標記物殘留量的影響 由表3可知,T1組較對照組顯著提高天然秸稈中15N殘留量(P<0.05),而T3和T4組較對照組顯著降低了15N殘留量(P<0.05)。T2、T3和T5組氨化大麥秸稈在孵育4 h后15N殘留量顯著提高(P<0.05),而T1和T5組在孵育12 h后15N殘留量顯著提高(P<0.05),所有處理組較對照組在孵育48 h后15N殘留量均顯著提高(P < 0.05)。
2.4 纖維酶的預處理對大麥秸稈體外發酵揮發性脂肪酸含量的影響 由表4可知,與對照組相比,T3、T4和T5組天然大麥秸稈在孵育12和48 h后乙酸濃度顯著降低(P<0.05),而孵育48 h后的丙酸及4和12 h后的丁酸含量顯著升高(P<0.05)。氨化秸稈在孵育12和48 h后,處理組乙酸濃度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但丙酸濃度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

表3 外源纖維素酶的不同預處理方法對大麥秸稈(天然或氨化)15N殘留量的影響

表4 纖維素酶的預處理對大麥秸稈(天然或氨化)體外發酵揮發性脂肪酸含量的影響
3 討論
有研究表明,黃色瘤胃球菌菌株具有降解植物細胞壁非纖維素多糖成分的能力,因為它們產生多種多糖酶,包括木聚糖酶和果膠酶(Erfle和Teather,1991)。這種能力可以解釋本研究結果中黃色瘤胃球菌較產琥鉑酸絲狀桿菌能降解更多的苜蓿草,此外作者認為,這兩種細菌降解中性洗滌纖維的能力取決于底物類型和外源纖維素酶水平。本研究表明,高壓蒸汽滅活的外源纖維素酶對大麥秸稈的干物質降解無顯著影響。外源纖維素酶對纖維素分解菌消化能力影響程度的差異可能是由于底物物理和化學特性、菌株固有酶譜和外源纖維素酶產物的酶譜有關(Morgavi等,2004)。
與紫花苜蓿干草相比,大麥秸稈含有較多的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Bhat等(1990)研究發現,黃色瘤胃球菌和產琥鉑酸絲狀桿菌在大麥秸稈上具有不同的粘附位點。本研究中使用外源纖維酶使產琥鉑酸絲狀桿菌較黃色瘤胃球菌增強了對大麥秸稈的降解能量,這表明外源纖維素酶譜與產琥珀酸絲狀桿菌基因酶譜在大麥秸稈消化過程中具有更強的互補性。Jalilvand等(2008)通過混合瘤胃細菌研究發現,與苜蓿干草和青貯玉米相比,外源纖維素酶更能促進小麥秸稈等高纖維粗飼料的消化。但Gallardo等(2010)研究發現,外源纖維素酶對苜蓿干草消化的影響大于水稻秸稈。這些研究之間的差異可能是由于外源纖維素酶產物中酶種類和活性不同。
外源纖維素酶預處理(T2組)在孵育4 h后較T1組降低了15N殘留量,這表明外源纖維素酶在瘤胃發酵前水解降低了初始細菌定殖。Wang等(2004)發現,經外源纖維素酶處理的大麥秸稈中酚類化合物較為集中。與對照組和T1組相比,外源纖維素酶水解后去除可溶性產物和纖維素酶底物的T3組15N殘留量較低,這也說明外源纖維酶使大麥秸稈表面提高,進而減慢了細菌附著速度。本研究發現,盡管外源纖維素酶處理對大麥秸稈發酵產生的揮發性脂肪酸無顯著影響,但經過水解預處理的外源纖維素酶組乙酸和丙酸比值較對照組降低,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4 結論
外源纖維分解酶可改善瘤胃細菌對纖維的消化能力,但其有效性取決于底物、細菌種類和孵育時間。在瘤胃孵育前將纖維素酶進行預水解可以通過增加還原性糖的有效性來促進微生物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