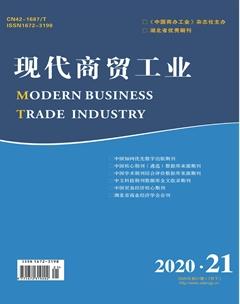應用型高校來華留學生漢語能力量表制定探討
金蒙
摘 要: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之下,中國高職教育國際交流合作水平日益提升,來華留學生日益增加,如何提升應用型高校來華留學生的漢語能力水平,為專業技能學習奠定堅實的語言基礎,成為我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而適用于普通高校留學生的漢語語言能力量表是否適應于應用型高校留學生呢?本文在分析已有的語言能力量表的基礎之上,結合應用型高校來華留學生培養特點,嘗試著對應用型高校來華留學生語言能力量表提出一些認識和思考,主要從應用型高校漢語語言能力量表亟需建構的緣由、語言能力的界定、量表制定的原則、方法和步驟幾個方面發表個人觀點,以期對量表的建構有所裨益。
關鍵詞:應用型高校;留學生;語言能力;語言能力量表
0 引言
2019年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中指出中國高職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發展水平在不斷提升,來華留學生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高職院校通過擴大招收東南亞、非洲等地留學生,探索海外辦學,建設魯班工坊,為“一帶一路”建設輸出本土化技能型人才。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如何健全和優化來華留學生的培養模式,達到育人標準成為擺在我們面前并且亟需探索的一個問題。其中漢語語言能力是衡量來華留學生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指標。目前應用型職業院校在留學生漢語課程的設置上大多沿用普通高校的漢語課程設置,漢語課堂上所學的內容基本由于日常生活方面,專業課堂上教授專業知識和相關技能,兩者無法交融,相互補益,語言基礎的薄弱影響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從語言能力標準的量化說起,只有界定好應用型職業院校留學生語言水平在學業年限中所能達到標準,在系統性的漢語能力量表的指導下我們才能更好地進行專業建設,制定人才培養方案、課程大綱和課程標準,開設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漢語課程,健全和優化來華留學生的培養模式,從而達到精準施教的目的。
目前國內圍繞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研究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語言能力內涵的界定;二是對已有的語言能力標準體系進行探討;三是關于制定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的思考;四是語言能力量表與語言測試的對接研究。
徐海冰、程燕(2011)提出《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存在結構不合理,內容缺失,缺乏關于目的語國家文化、風俗等知識和相關社會語言能力量表;李莉(2018)對已有的漢語能力標準體系進行優缺點分析,認為《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強調語言要素和語言技能,而非語言交際能力;《國際漢語能力標準》)雖然強調了語言知識的交際運用能力,彌補了《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的不足,但是忽視了社會文化在語言交際中的影響,且分級描述不夠細致。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已有的漢語能力標準體系,仍存在著不足和需要商榷的地方,未能與國外業已成熟標準體系接軌和兼容;二是已有的漢語能力標準體系主要面向普通高校的留學生對通用漢語能力的考核,而未能涉及到職業院校留學生職業漢語能力考核。漢語交際由于日常生活范圍,與專業領域脫節,語言能力內涵界定存在缺失,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目的所在,嘗試著對應用型高校來華留學生漢語能力量表制定方面提出自己的幾點思考。
1 應用型高校留學生漢語語言能力的界定
我們在界定“語言能力”時,既應參考已有的代表性能力標準體系,如《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國際漢語能力標準》《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等和相關學者對語言能力的研究,同時也應該結合應用型高校留學生專業人才培養定位和留學生的實際學情來界定應用型高校語言能力框架構成。
語言活動總是在一定領域內進行的,當然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交際環境悉數列舉出來,但是主要的與漢語學習相關聯的應該主要有四個領域:教育領域、公共領域、專業業務領域和個人領域。
教育領域:能傳授知識和具體本領的地方,這里主要指的學校課堂教學,對于應用型高校的留學生而言,主要包括理論課程和實訓課程的課堂教學。
公共領域:所有的日常社會交往,在公共場所進行的交際活動,包括互聯網領域,諸如交通、旅行、購物、簽證辦理等。
專業業務領域:與專業業務相關的領域,如公司業務實習。
個人領域:交際者的家庭關系和其他個人社會活動領域。
語言能力的界定無法脫離實際的交際領域,故而結合上述領域,語言能力應當包含語言知識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和社會語言能力三個方面。其中語言知識能力包含語音、詞匯、語法和書寫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具體到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社會語言能力是跟社會文化相關的語言知識能力,語言在社會中使用的,受一定社會規約的制約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包括人的言談舉止、禮儀、輩分、性別、身份、社會團體因素等,社會語言能力主要涉及對語言變體的敏感性;對語域差異的敏感性;對語言自然地道的敏感性以及理解和使用文化典故、修辭的能力。語言能力各方面的描述一定要切實結合應用型高校育人特點——強調實踐教學,注重實習實驗實訓,將產教研融為一體。所以語言能力各方面除了涵蓋通用漢語能力層面,也要囊括到專業漢語能力,如語言知識能力層面需要包含對專業詞匯的要求;語言交際能力涉及專業領域、實訓操作流程的表達;社會語言能力又會關聯到師徒制育人理念和文化背景等。
2 應用型高校留學生漢語語言能力量表制定的原則
王佶旻(2012)在《制定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的初步構想》一文中提出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制定的四個原則:科學、全面、實用和兼容。這四點原則也是我們在制定應用型高校留學生漢語語言能力量表所應遵循的。
語言能力的界定、語言能力的描述語、語言能力的等級劃分都必須切實地反映出學習者的實際情況,將語言能力量表作為一個衡量指標或者視為一個常模,必須具備客觀性和科學性。
全面性意味著量表能夠涉及到語言應用的各個方面,目前現有的能力標準體系可以為我們制定應用型高校留學生語言能力量表提供一個參考標準,但是一味地照搬照抄,倡導拿來主義,卻是不可行的,應用型高校不同于普通高校,尤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在,前者更加強調實踐能力,而在專業實踐中所運用的漢語的能力便是我們考核的一個方面,例如是否在實訓課程中理解相關的實操指令;是否能夠描述運行流程等,而這些無法在目前的標準體系內容中體現出來,但是確實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
實用性也很重要,這也是量表制定的意義所在,所以量表中具體內容表述不僅應該將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切實地為留學生語言能力評估提供一個評價標準,同時也為授課教師校本教材開發、人才方案撰寫、課程大綱編寫、教學目標設定以及測試考試內容確定等提供參考。
兼容性除了王佶旻文中(2012)提及到要與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CEF)兼容外,也應該與漢語水平考試(HSK)大綱進行兼容,這是因為漢語水平考試(HSK)是目前國內一項國際化標準考試,也是許多應用型高校對來華留學生結業要求,將HSK考核內容量化到量表中,也能保證所學與所考沒有分離。
3 應用型高校留學生漢語語言能力量表制定的方法和步驟
目前最常見的方法有直觀法、定量法和定性法。大多現有的語言能力量表都是采用直覺法。這里最好綜合使用這三種方法,實現優勢互補。
(1)借助調查問卷、訪談等方式進行調研,調研內容涉及到:留學生語言應用的領域、面臨的交際主題,需要完成的交際任務、不同級別學習者語言能力的自我評估情況。
(2)利用以上信息明確學習者的各種需求,并找出他們關注的主要方面,擬定出學習者在這些方面上能力自我評估量表,這里擬定學習者自我評估情況,可以通過直接問答和分級測試方式擬定不同級別的語言能力情況,測試項目必須精心設計,目的是顯示出測試指標的相對難度。
(3)綜合使用公認的語言評估詳細量表和等級標準,制定最初的詳細量表。
(4)通過評估它與學習者自我評估量表之間的相關性來對量表進行調整。
(5)在學生和教師中進行實驗,以評估其適應性和透明度,對詳細量表的表述進一步更正,修訂或者簡化。
上述方法和步驟只是粗線條勾勒,每一個環節仍存有許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從單個學校層面而言,制定本校的語言能力量表,首先需要借助專家和組建教師委員會,專家可以對量表進行直觀審議,提出不足之處,也可以參與設計量表;組建教師委員會,這樣的委員會可以根據訪談對象或者應試者的實際表現或者測試結果來討論界定能力標準,通過收集其反饋意見,讓能力標準制定更加完善;其次語言等級的劃分,大多能力量表都是沿用三等六級,每個級別都有相應的界定,等級描述時應采用肯定式定性描述,同時盡可能地以量化指標加以定量描述。以《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為例,該量表的測評總表將語言能力劃分為三個階段:初學階段、獨立階段和精通階段。而具體到一個教學單位,是否也能在規定年限內達到精通階段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每個教學單位的學情都是不同的,自然需要因地制宜,根據被測評的具體人群進行語言能力等級劃分。
4 結語
隨著職業院校留學生招生人數日益攀升,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策略顯然應該根據學習者的特點和學習需求進行相關轉變,普通高校中的通用漢語無論是在語言能力評估方面還是課程標準制定還是課時設置方面都已然頗有成果和經驗的積淀,而應用型職業院校卻經驗缺乏,這并非是通過簡單地照葫蘆畫瓢就能解決的,應用型職業院校的留學生培養定位顯然不同于普通高校,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能力方面評估指標也顯然不同,語言能力量表作為一個標準體系亟需構建出來,只有在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的標準體系的指導下,對外漢語課程還是專業漢語課程制定、課程目標、授課要求、教學重難點等諸多方面才能有章可循。漢語技能型國際化人才才能得以鑄造,這樣才能服務于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參考文獻
[1]徐海冰,程燕.《國際漢語能力標準》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兼與《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比較[J].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1,31(05):91-95.
[2]李莉.漢語測試語言能力標準研究述評[J].考試研究,2018,(03):45-49.
[3]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語國際能力標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4]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水平考試部.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的等級大綱[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5]中國對外漢語賈傲雪學會漢語水平等級標準研究小組.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2007.
[6]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2008《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劉駿,傅榮主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
[7]孫斐斐.語言能力的三大模塊與對外漢語教學的策略[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1.
[8]王佶旻.制定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的初步構想[J].語言文字應用,2012,(01):109-116.
[9]盛炎.《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與國外一些標準和大綱的比較[J].世界漢語教學,1988,(04):241-243.
[10]于亮.漢語語言能力量表制定的相關思考[J].語言科學,2013,12(06):585-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