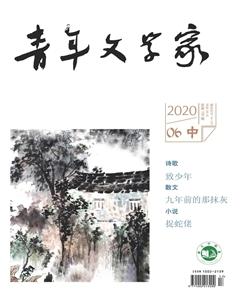從中古釋《詩》看中國古代文學功用觀
王廣鵬
摘? 要:中古時期對于《詩》的解釋,有了自身新的變化,然而整體上仍延續了上古時期對文學的功能定位,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民族的思維模式與文化特征。本文以《關雎》之闡釋為例,管窺中古時期釋《詩》背后古代文學的功能定位。
關鍵詞:詩經;關雎;闡釋;文學觀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釋《詩》的艱難演進
魏晉時期,我國文學進入到自覺時代。在社會分裂、動蕩的背景下,儒學失去了其壟斷性統治地位,玄學、佛學等流派興起,文學本身的獨立地位也在這一時期得到突出顯現。宋文帝設立文學、儒學、史學、玄學四科,將文學作為與儒學等學科并舉的地位存在。這一時期,《詩》的博物學開始發端,代表作品是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除專門詮注《詩》的文本以外,伴隨文學理論的繁盛,文學理論作品也開始對《詩》進行大量的詮釋論述,將《詩》本身的文學性提到了前代所未有的高度。下文即選取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兩部文學理論作品——《文心雕龍》與《詩品》,考察其對于《詩》的闡釋:
首先,《文心雕龍》與《詩品》都關注到了《詩》審美性的特點。劉勰在認為:“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1]“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2]鐘嶸在《詩品序》寫道:“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3]這顯然與《毛詩序》“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等理論一脈相承,都強調了詩本身的情感性。但《文心雕龍》與《詩品》相較毛詩而言,在對《詩》的審美性闡釋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即強調文學作品形式要素的重要性,例如劉勰對于《詩》“摛鳳裁興”的強調[4],甚至于單列《比興》一章,專論這兩種藝術手法;再如鐘嶸在《詩品序》對“賦比興”的定義,與《毛詩序》相比,是完全從文學修辭手法,而非政治內容承載的角度進行定義,這也影響到后代朱熹等人對《詩》表達手法的認識。鐘嶸在“宏斯三義,酌而用之”的基礎上還進而將“風力”與“丹彩”相結合,強調了文學作品應當文質統一的觀點。這些都表明在文學作為一個日漸獨立的門類的背景下,文學本身的審美特性不斷得到挖掘,情感、想象等內容要素與修辭、聲韻等形式要素不斷被深化認識。雖然《文心雕龍》與《詩品》并沒有諸篇解釋《詩》具體篇章,但這并不妨礙其作為具有釋詩代表性的作品,可以從中集中看出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釋詩思想與理論的變化。
其次,《文心雕龍》與《詩品》雖然開始關注到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這一獨立門類的原因,強調了《詩》本身審美特性的因素,但對于《詩》仍將其定位于儒家經典之列,仍強調了其政教性功用。《文心雕龍.宗經》篇寫道:“經也者……不刊之鴻教也。”劉勰認為,包括《詩》在內的五經是永遠不可變更的教條,在教化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以此為出發點,《文心雕龍》貫穿了宗經思想的色彩。進而劉勰寫道:“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義取其貞,無于夷禽”[5]劉勰認為之所以《關雎》選取雎鳩這種鳥作為比興對象,落腳點在于“德”。雎鳩的雌鳥與雄鳥各自成對,寓意著后妃貞潔的美德。不必糾結雎鳩這種鳥是否為猛禽,因為《關雎》選擇這種鳥,出發點是這種鳥的德行,用意是取其專一的寓意。劉勰在《明詩》篇也寫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強調了《詩》對于匡持人的性情的重要意義,這與孔子“樂而不淫”、毛詩“止乎禮義”等思想一脈相承,強調了《詩》思想對于教化訓誡可以起到典范意義。鐘嶸在《詩品序》中也提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強調了詩歌重要的社會功用。在鐘嶸的《詩品》體系里,或源于風雅,或源于楚辭,對于風雅的強調即可以看出鐘嶸對《詩》雅正體系下風化、諷化精神的重視。
總而言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于《詩》的詮釋一方面延續了兩漢以來的經學化釋詩,一方面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詩》產生了文學、博物學等詮釋方法;盡管整體上并未擺脫漢儒建立的政治性詮釋框架,但是在《詩》解釋的審美性上有了相當可觀的突破,尤其是對于《詩》形式因素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分裂動蕩的一段歷史時期,文學藝術在這段時期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發展,但即使是在這種背景下,對于《詩》的闡釋仍然是在漢儒規定的框架內行進,等到隋唐時期,漢儒的框架發揮了更加明顯地作用。為了適應統一國家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統治者組織人員校勘五經,由唐朝孔穎達主編的《毛詩正義》成為這一時期《詩》詮釋的集大成的著作,這部書接過鄭箋的大旗,成為漢學體系下集大成的第二座豐碑。孔穎達主編的《毛詩正義》采用《毛詩傳箋》為本,采用“疏不破注”的原則,對鄭箋的注疏都符合鄭玄的注釋,不符合鄭玄箋注的都予以剔除,統一了過去各派紛繁復雜的爭論,因此孔疏屬于嚴密的漢學體系。孔疏認為《關雎》:“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從中可以看到,孔穎達對于《關雎》的解釋完全符合毛詩與鄭箋的闡述,認為《關雎》是言后妃之德的作品,目的在于起人倫之典范的作用。由于孔疏完全是按毛詩與鄭箋的思想注解《關雎》,此處不再贅述。總而言之,隋唐時期的釋詩是在漢學體系下進行的,屬于漢學體系在隋唐時期的順向演進,這種情況等到兩宋時期才得到新的發展。
二、兩宋時期:釋詩的宋學體系
經過五代時期的分裂割據,原有的禮制綱常受到了極大破壞。北宋學者需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經學進行新的闡發,進而服務于新的社會政治。北宋時期對于《詩》的闡釋始終貫穿著宋學與漢學之爭,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
首先對漢學體系進行質疑與動搖的是歐陽修。歐陽修在《毛詩本義》中常常指出《毛詩序》、《毛詩傳》、《毛詩傳箋》的相互矛盾之處,從漢學體系內部瓦解了其權威地位。在《毛詩正義》中歐陽修認為:“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于人情?”[6]歐陽修認為《關雎》雖是表現后妃之德,表現的內容主要是太姒與文王琴瑟相調,堪為婚姻典范,而不是太姒并不嫉妒后宮嬪妃,擁有謙虛忍讓之德。如果是表現太姒包容大度之德的話,以淑女比喻后宮嬪妃,則《關雎》并未有詞句談到太姒,這是不符合情理的。歐陽修還寫道:“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可以看出,歐陽修進一步繼承了漢朝“刺詩說”的理論,對于“思古以刺今”的理論予以肯定。歐陽修盡管動搖了漢學體系,但是并沒有勇氣全盤予以否定,其對于《關雎》的解釋仍然只局限于政治性闡釋,只是對漢儒可能牽強附會的地方予以批駁。但歐陽修畢竟開啟了對漢學體系瓦解的先河,到朱熹手里,就已經建構起屬于自身的宋學體系。
首先,相對于魏晉隋唐時期的艱難突破而言,朱熹已經在構建自身新的體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建構起理學基礎上的宋學體系。他綜合篩選前代和自己的注疏、很多注疏超過了前人;以求實的精神注重訓詁文字的考察,注重文字韻讀;此外,他的《詩集傳》是我國第一本系統地闡釋《詩》本身文學性要素的作品。相較于魏晉隋唐時期的針對《詩》來源、功能、手法等文學要素闡釋的零散敘述,《詩集傳》不僅對于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而且貫徹到針對《詩》每首具體詩歌的解讀中去,進而形成了釋詩史上的重大突破。朱熹的釋詩是其理學體系建構的一部分,其釋詩活動是在理學整體框架內行進的。朱熹繼承了孔子“樂而不淫”“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傳統,反對“刺詩說”的理論。他在《朱子語錄.卷八十.詩一》中提到:“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在《詩集傳》中,朱熹對于《關雎》的刺詩理論進行了更為充分的批駁,認為若是刺詩,此乃君王內事,如此丑事為何還要大宣于天下?為何還要放在三百篇之首這么明顯的位置?這與孔子以來的“樂而不淫”“溫柔敦厚”等思想是否相悖?若為君王荒淫無道、周道分崩離析之作,又怎么能起到對于綱常禮教的典范意義?又怎么能發揮《詩》對于風化的正面作用?針對《關雎》的主旨,朱熹也認為是后妃之德,并將后妃具體化到太姒,將君子具體化到文王。從《詩》的次序編排來看,“四始”之編排應該考慮到文本本身反映對象的先后性,即《關雎》所反映的應是西周初期的作品,的確更加貼合文王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朱熹認為君王應當以文王為典范,后妃應當以太姒為標桿,夫婦和諧,家庭和睦,后宮安寧,然后才能國家繁榮,天下大治。他在《朱子語類》中談到“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八。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7]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朱熹所批判的,往往是那些有害于綱常禮教的闡釋,無論是對于“溫柔敦厚”、“性情之正”的強調,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闡釋,朱熹的釋詩都是服務于其理學意識形態的建構,進而維護統治階級加強統治的需要,與漢學體系從本質上看并無區別,只是闡述體系與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關雎》中的男女情欲都被朱熹自動篩除掉了,轉之以天理綱常的闡釋方式。《詩》中多篇詩歌,朱熹承認其描寫了男女之情,但又將其斥責為“淫詩”,進而服務于其“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體系建構。朱熹即使可以稱為《詩》闡釋的重大突破,但是在整個中古時期,都只能算作《詩》闡釋的發展期,即這一時期是按先秦兩漢奠定的基礎與框架行進,就《詩》的內容闡釋方面,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注釋:
[1]見《文心雕龍.明詩》篇,劉勰編,周振甫譯,中華書局,2017年,55頁.
[2]見《文心雕龍.情采》篇,劉勰編,周振甫譯,中華書局,2017年,289頁.
[3]見《詩品譯著》,鐘嶸編,周振甫譯注,中華書局,2017年,15頁.
[4]見《文心雕龍.宗經》篇,劉勰編,周振甫譯,中華書局,2017年,28頁.
[5]見《文心雕龍.比興》篇,劉勰編,周振甫譯,中華書局,2017年,326頁.
[6]《詩本義》卷一,影印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23冊,詩類,世界書局1988年版,第17頁.
[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