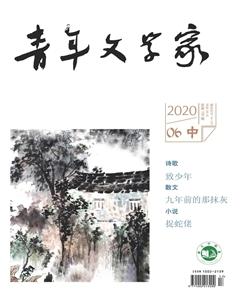論“鄭聲”非《詩經?鄭風》
李勝楠
摘? 要:“鄭聲”的概念從首見于文獻記載以來到東漢許慎將其與《詩經·鄭風》相聯系,最后到宋代朱熹將其完全等同于《詩經·鄭風》,歷代學者對兩者的關系爭論不休。但是在最初“鄭聲”概念形成的時候并沒有證據將其指向《詩經·鄭風》,所以在相關論據證明下,“鄭聲”應當是鄭國新興起的音樂,有別于《鄭風》;“淫”之概念亦有過分、過度、不中正和好色淫欲等多層含義;《詩三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已經是正統音樂典范,所以《詩三百》中并無淫詩,且沒有證據可證明當時有人認為其中有淫邪之詩。
關鍵詞:鄭聲;淫;詩經;鄭風
“鄭聲”的概念第一次見于《論語》,但并未將“鄭聲”與《鄭風》之詩相聯系。東漢許慎《五經異義》引《魯論》:“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合,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后來班固也提到:“孔子曰‘鄭聲淫者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誘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最終將“鄭聲”等同于《鄭風》的是朱熹《詩集傳》。
一.“鄭聲淫”之“淫”
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及“鄭聲”的是《論語》中兩則孔子語錄。第一則是《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1]朱熹在其《四書章句集注》中注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歲首也。……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于此又以告顏子也。殷之輅:輅者,大車之名也。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奢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謂禁絕之。”[2]這里大致是說鄭聲有過度、繁蕪、奢靡的特點,所以孔子要禁絕鄭聲,以合于盡善盡美與中庸之道。
《說文·水部》:“淫,浸淫隨理也。一曰久雨為淫。”《爾雅·釋天》:“久雨謂之淫。”“久雨”是降雨過多,所以可引申為“過度”之義。除了“過度”之外,還有“好色淫欲”之義,這個意義放在“鄭聲淫”中也較為合理。[3] “淫”字本為“久雨”,而遠古人類觀念中,自然界的萬物是天父地母結合的產物,降雨則是天地合的象征,所以“淫”又引申為“好色淫欲”,“鄭聲”之“淫”此二者當皆有之。
二.“鄭聲淫”之“鄭聲”
《論語》中提到“鄭聲”的第二則是:“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篇》)朱熹注曰:“朱:正色;雅:正也。”[4]我們現在也說“紅得發紫”,紫是紅色過度的狀態。從朱熹的注解來看,說“鄭聲淫”就是說鄭聲過分、不中正。這一則與前文所提《論語·衛靈公篇》論及“鄭聲”的一則都未說明“鄭聲”到底為何。
何為聲?《禮記·樂記》卷首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據《說文解字》對“樂”“音”“聲”的解釋可知,“音”是絲竹金石匏土革木;“聲”是宮商角徵羽;“樂”則是這五聲八音的總稱。我們可以由此知曉,“鄭聲”應為一種音樂曲調。
當然,有人指出“鄭聲”或許并非《鄭風》,但它可以是與《鄭風》相配合的曲調。但是嚴謹來講,并非只有同《詩經·鄭風》相配的樂調才能稱為“鄭聲”;而且,音樂曲調會與所歌之詞風格一致,沒有歌詞正統曲調淫靡的道理。所以“鄭聲”并不是特指已經周王朝太師整理審定的詩樂,而是指當時在鄭國等地興起的新生音樂。如《禮記·樂記》中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我們知道子夏是孔子的學生,而“孔子刪詩說”不可信的觀點已大致為現在的學者們認可,也就是說魏文侯聽鄭衛之音時《詩》已成書,若“鄭衛之音”是《詩經》中的《鄭風》和《衛風》的話,則不可能把“鄭衛之音”稱作“新樂”。
《禮記·樂記》中載: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選俯,奸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忐,宋音燕如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鳶辟驕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5]
這里子夏與孔子相同,把古樂與鄭衛之聲并提,所以鄭聲為新樂代表;其次,子夏將鄭、宋、齊、衛四國之音相提并論,并稱其為溺音。如果“鄭”即《鄭風》的話,那么“宋”就應該是《宋風》,但《詩》中并無《宋風》。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道:“孔子與晉平公同時。《晉語》里的‘新聲是否即《論語》里的‘鄭聲,或‘鄭聲還是另外一種樂調,這種問題現在雖未能解決,總之,新聲與鄭聲都不是為了歌奏三百篇而作的音樂是可以斷言的。”[6]此言得之。
三.“鄭聲淫”與《詩》無“淫詩”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篇》)
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先進篇》)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論語·季氏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鄉黨篇》)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鄉黨篇》)[7]
由上觀之,《論語》中提到孔子對《詩》的評價無一例外都是正面的、褒揚的。如果其中有孔子認為不合適的詩,一定會將其強調出來讓弟子和兒子不要去學。
第二,除孔子從未對《詩》表現出要有所取舍之外,在周代的大環境中,也沒有誰認為《詩》中有不好的內容。周代王官很早就以《詩》、《樂》為教。《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教六師、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六律為之音。”《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玄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要把《詩》教給王室國子,其內容必定不能避開《鄭風》,且沒有相關記載提到在《詩》中“放”《鄭風》,如果《鄭風》就是淫邪的“鄭聲”,那么很難想象太師如何在“國子”們面前“誨淫”。
第三,春秋時期人們在比較正式的談話中會引用《詩》。《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左傳·昭公十六年》也記載了鄭國子產等六位大臣在接待晉使趙宣子的宴會上賦詩的情形: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知鄭志”。子蕃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兩”,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呢燕好也。”[8]
其中所賦之詩皆為《鄭風》之詩,且有五首是愛情詩。如果《鄭風》之詩是需要“放”的淫邪之詩,子產就絕不會在宴會上領眾卿吟誦《鄭風》,而宣子聽完更不會如此感激和高興。
第四,春秋時代,男女自由戀愛現象十分普遍。《周禮·媒氏》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相反,如果大齡男女不適時結婚其與家人都會被當權者懲罰。越王勾踐曾規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勾踐滅吳》)當時社會對男女戀愛還是持鼓勵態度的。所以,如果因為《鄭風》中多為愛情詩就將其斥之為“淫詩”并等同于“鄭聲”的話,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合情理的。[9]
第五,《鄭風》雖多情詩,但縱覽“詩三百”,其它各部分情詩也不在少數。“二南”中愛情詩比例僅次于《鄭風》。有人說“二南”之所以“思無邪”是因為它比《鄭風》更加含蓄委婉,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但仔細分析“二南”詩篇會發現,其中諸如《汝墳》、《摽有梅》、《野有死麕》等詩熱烈大膽的程度毫不遜色于《鄭風》之詩。此外,如果說《鄭風》之詩過于直露而被斥為“鄭聲淫”,那么《齊風》中的詩也足夠直露大膽,且其中有多篇是記載齊襄公與其同父異母妹妹文姜通奸之事的,但孔子和當時的人都未曾講過要“放齊風”,所以其實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論孔子還是其他人,都沒有“淫詩”的概念,都沒有對《詩》中任何一篇有過反面的、貶斥的評價,所以應該禁絕的亡國淫靡之“鄭聲”不可能是《詩經》之《鄭風》。
注釋:
[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同上
[3]黨萬生.“鄭聲淫”新論[D].西北師范大學,2003(06),第10頁。
[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5]孔穎達.禮記正義——卷三十八、三十九(影印)[M].北京:中華書局,1980(10).第1538-1540頁。
[6]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08).第350頁。
[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03).第1380-1381頁。
[9]黨萬生.“鄭聲淫”新論[D].西北師范大學,2003(06).
參考文獻:
[1]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清]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5][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5.
[6]黨萬生.“鄭聲淫”新論[D].西北師范大學,2003(06).
[7]白凱.新時期《鄭風》研究綜述[J].山西大學,2017-05-28.
[8]方延明.“鄭聲”非《詩經》鄭風辨[J].文獻,198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