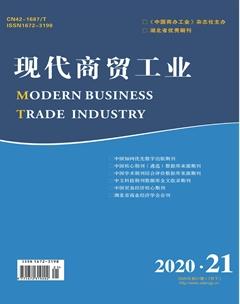論新時期桂劇與廣西本土文化
鹿義霞
摘 要:桂劇是廣西主要地方劇種之一,它根植于八桂大地的沃土,飽蘸著廣西特有的風土民情。新時期桂劇在拓寬題材空間和豐富舞臺表達方面做了很多創新,仍保持著其鮮明的民族個性。它有機融匯了壯鄉的山水文化、歷史文化、民族與民俗文化等元素,生動地展現了廣西的地域人文景觀。
關鍵詞:新時期桂劇;山水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
在新時期,面對戲曲生存生態環境的眾多危機,桂劇依然推出了系列精品,體現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重魅力與藝術價值。《大儒還鄉》成功入選2005-2006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七步吟》成為2010-2011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年度資助劇目,《瑤妃傳奇》獲得中國戲劇最高獎“文華獎”,《打棍出箱》斬獲第三屆中國戲曲“紅梅薈萃”大賽金獎,《風采壯妹》獲中宣部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漓江燕》獲得第七屆中國戲劇節劇目獎,《商海搭錯船》獲取文化部第八屆文華新劇目獎。新時期桂劇在戲曲傳統方面既有恪守也有超越,其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向壯鄉獨特地理人文環境及其豐富精神源流的深處掘進”。
1 八桂山水,自然人文
山水可以是背景,可以是人文,可以是情懷,也可以是故事情節的一部分。嶺南的自然環境與人文山水給予新時期桂劇豐富的創作資源與藝術滋養。《大儒還鄉》《劉三姐》《破陣曲》等作品中,均有八桂山水的身影。
山水劇場,故事舞臺。劉三姐的故事孕育、生發于嶺南秀麗山水與多維交融的民族審美。廣西以喀斯特熔巖地貌為主,多山多水。山水既充滿詩意與浪漫,也制造著聯通與阻隔,催生著山歌藝術與歌圩風俗。《劉三姐》一劇中,劉三姐的歌聲飄蕩于山水之間,滲透著嶺南地區特有的景觀要素,多見山、水、嶺、灣、古榕、木棉等自然意象,釀造出耐人尋味的南國意境。廣西的山水景觀為《劉三姐》營造了大寫意,為人物打造了豐富的生活空間,也為故事鋪展了偌大的舞臺。大型桂劇《破陣曲》圍繞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文化名人田漢、歐陽予倩等人的故事,將抗戰的烽火與廣西的風情結合在一起,融入了桂林的山水、巖洞、棧橋、漁船、石刻等景觀元素。桂劇電視劇《風采壯妹》講述壯族姑娘駱妹帶領山寨姐妹織錦,推動民族工藝品走出國門的故事,呈現出濃郁的民族風情。劇作以龍勝縣金平寨作為故事背景,將壯寨如畫的青山、清澈的綠水、錯落的梯田、風情的木樓搬上熒屏,充滿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情的金平寨成為浩大的視覺盛宴,使故事更加真實生動。不止桂劇,1997年,張藝謀執導的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亦是聚焦桂林的陽朔地段,將漓江水域與書童山等十二座山峰打造為天然的山水劇場。夜幕之中,燈光之下,山歌縈繞,舞蹈翩然,山水如詩。
山水既是寫意畫,也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義。這在《大儒還鄉》中有生動體現。該劇講述清朝名臣陳宏謀的故事,陳年事已高,向朝廷請示告老還鄉于桂林。他曾位居清朝重臣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一生政績無數,特別知名的是“秦絹”工程。返鄉前,陳宏謀不顧勸阻執意去曾任職的陜西考察秦絹之南引北種。這是他的驕傲、他的情懷,其間凝聚著太多的情愫。豈知,這竟是形象工程,造假工程,不但導致自己的學生佟三秦無辜冤死,也造成大量的經濟浪費,帶來系列惡性循環。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是親手推倒自己的豐碑?是明哲保身捂住真相,還是揭開蓋子承認錯誤?陳宏謀陷入了內心的撕扯。最終,崇高的人格讓他戰勝了自我。“家鄉萬里歸不得,只緣漓江太清純”,《大儒還鄉》中的這兩句臺詞既渲染著陳宏謀的悲情,也揭示了其品格的高潔。八桂風土哺育了他,漓江的水滋養著他。漓江之清澈與主人公之追求清白自然融合一體,都是人物心中的情結。
2 歷史文化——歷史意識與現代觀念的雙向觀照
新時期,桂劇推出了不少演繹本土歷史、體現廣西本土文化內涵的作品。此類作品多取材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并以之傳揚當代理念,如《金田起義》《瑤妃傳奇》《風雨南關》《大儒還鄉》《柳宗元》等。
歷史文化名人題材,是新時期桂劇的重頭戲。桂劇以之為媒介,傳承文化的積淀,發掘歷史的智慧,啟迪當代的思考。前文提及的《大儒還鄉》就頗富歷史意味和當代價值。主人公陳宏謀是清朝官員、桂林歷史文化名人,曾被乾隆稱之為“大儒之效,百官楷模”。作者舍棄傳統戲曲對歷史文化名人的書寫套式,以“秦絹桑政”作為選材重點,透過造假工程思考何為真正的政績,并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故事既有歷史的內涵,又回復了當前人民的關注焦點,凸顯了執政愛民的實質,“對當前追求虛假政績的官員無非是一劑良藥。”以歷史鏡鑒過往,以歷史警示當下,這樣的作品自然容易獲得共鳴,贏得更多受眾的認同感。新編歷史傳奇桂劇《瑤妃傳奇》的部分故事,有真實史料可考。明史曾有記載,廣西一位瑤族少女被選入宮,生下太子,后來太子繼承王位。現在,桂林附近的賀縣有“圣母墓”和“墓碑記”,桂林市也有“圣母池”遺址。劇作者既借鑒真實史料,又融入民間傳說,并灌注當代思考。瑤妃背著大鼓走入皇宮,對民族有擔當,對愛情不盲從,對皇權不折腰,其清新自然之風體現了八桂兒女的風骨,也濡染著廣西文化的風情。桂劇《何香凝——桂林記憶》通過何香凝的故事,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致敬革命者。《柳宗元》成功塑造被貶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通過鮮活事例展示了其可貴的品格,獲廣西第六屆劇展廣西戲劇“桂花金獎”。柳宗元面對逆境時的豁達樂觀,為官一方時的親民愛民,既回蕩著歷史的聲音,也寄托著當代觀眾的美好愿望。
民族英雄題材與戰爭題材,也是新時期桂劇的重要關注點。《浩氣千秋》塑造了瞿式耜、張同敞兩位民族英雄人物,他們抗擊清軍、不懼生死,心系桂林、無私無畏,體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桂劇《金田起義》以太平天國起義為背景,講述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壯大之路。太平天國起義發端于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其浩大規模有成功之道,其走向失敗也有主客觀原因。九場桂劇《金田起義》講述天國初期洪秀全團結天地會共同抗擊清軍的故事。劇作中,無論是洪秀全、羅大綱,還是馮云山、韋昌輝、楊秀清都刻畫得比較成功。特別是羅大綱的草莽氣息、韋昌輝的剛愎自用,描述得尤為形象。桂劇《漓江燕》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故事亦是驚心動魄。
新時期桂劇還熱衷于闡釋廣西少數民族本土文化與漢族文化的沖突與共融,書寫民族史詩。《靈渠長歌》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而編寫,場景波瀾壯闊、情節扣人心弦。該劇敘寫秦始皇在統一中國歷程中,為解決糧草運送難題而命史祿修建靈渠的故事。靈渠這一偉大工程是集體的心血之作,凝結著史祿、10萬開渠士兵以及駱越百姓共同的汗水與智慧。故事將嶺南文化作為重要背景,滲透著濃郁的人文氣息和歷史感。《瑤妃傳奇》書寫“蠻女”成為帝王妃的故事,其山野氣息、潑辣性格、大腳風采、平等觀念,都是生動的價值符號,彰顯著古樸的瑤族文化。而劇中的矛盾,也不僅僅意味著少女與皇宮的矛盾,其間滲透著漢瑤民族文化的沖突與共融,古樸瑤族文化與傳統儒家文化的對立與融合。
3 民族風味與民俗文化
廣西是多民族聚居區,在此生活的少數民族有十數個:壯族、瑤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各少數民族在語言、服飾、建筑、飲食、娛樂、宗教、風土人情、婚慶節日、民間藝術等方面有著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比如壯族的三月三歌節,瑤族的盤王節,苗族的蘆笙節,侗族的花炮節……在這里,有音樂的、工藝的、語言的、風俗的文化富礦。燦爛的民族與民俗文化自然流溢在新時期桂劇中,豐富著劇作的審美內涵。
廣西山歌歷史久遠,積淀著民族集體心理。對歌不只是傳說中的場景、演出中的片段,在現實中依然隆重上演,比如當下仍然火熱的壯族“三月三”盛會。對歌比賽至今在桂林、柳州各地仍有傳統。《山歌好比春江水》《只有山歌敬親人》《壯族大歌》《大地飛歌》等,都是廣西知名的山歌。每逢年節假日,山谷中、溪水畔、田埂邊、廣場上都有歌者自發結伴對唱山歌。歌者投入,聽者動情,場面十分壯觀熱烈。《劉三姐》一劇充分體現了廣西的山歌文化。無論是俏皮對歌還是智斗敵人,山歌中融入大量生產生活常識。劉三姐憑借敏捷的思維、出眾的歌喉在對歌中戰勝了莫老爺請來的三個秀才,其間的對歌不但形象動聽、妙趣橫生,而且故事性強,對于塑造人物、豐富情節也頗有推動作用。有評論者認為,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瑤妃傳奇》也體現了廣西的山歌習俗。生長在廣西邊遠瑤寨的瑤族姑娘紀山蓮被選為“秀女”。與其他秀女不同,她以最淳樸的姿態走進皇宮——背著一支長鼓,邁著一雙大腳。后來,她與明憲宗滋生了愛慕之情,他們的示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信物和誓詞,而是唱山歌、咬手臂定親,充分彰顯了民間性、民俗性和民族性的風格。此劇中飄蕩的嶺南瑤鄉無歌詞的“香哩歌”和瑤家兒歌,亦氤氳著濃濃的地域風味與民族特色。
新時期桂劇也涉筆廣西民間藝術、民族工藝,體現出濃郁的壯鄉風情。《風采壯妹》刻畫壯族姑娘駱妹帶領家鄉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故事。該劇的地域景觀和地方風情,既體現在美麗的壯寨、不服輸的壯家性格,也體現在劇中傳說性的五彩壯錦上。壯錦是壯族著名的手工業品,經以素色棉紗,緯以五彩絲絨。絢麗的壯錦,不但是該劇的重要物像,也是該劇的重要意象,既服務于塑造人物、推動情節發展的需要,也營造了新穎奇特的審美效果。《商海搭錯船》圍繞著名化學家洪川和桂劇名演員青夢下海經商的故事,折射出時代浪潮下劇團演員的生存困境。地方曲藝漁鼓的融入,更是體現出民族文化與八桂風情。桂劇《瑤妃傳奇》展示有瑤族的“長鼓舞”,隨著背、肩、手強烈扭動跪地躺腰等大幅度動作,人物的心理世界也鋪展在觀眾面前。那些動作看似夸張,卻極富寫實意義與象征意義,它們是詩化的舞蹈。《打棍出箱》除了軟氈功、甩發功、水袖功之外,還有技驚四座的“跌箱”和“箱內換衣”,其高難度動作讓人嘆為觀止,速度之疾簡直要以秒算。此外,一些劇作還融入銅鼓文化。節日慶典或喜喪祭祀之時出現的銅鼓,是壯族人民心中的神物,是壯族文化的重要組織部分,是活著的文化遺存。2006年,壯族銅鼓習俗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對于文藝創作者而言,如果能獲得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也是一種殊榮。
服飾建筑等作為物態形式,承載著豐富的時空信息,傳達著民族的生活意趣,寄托著民族的審美意念。在新時期桂劇的舞臺上,那些華麗紛繁或特色鮮明的服飾,其刺、繡、鑲、染,都有著特別的工序,也滿含著文化的符號。如,壯族男子多穿青布對襟上衣,苗族女子衣襟、領邊、袖口都鑲苗錦花邊,侗族男子頭上包長頭帕;壯族習慣在底架上建住宅,瑤族的民居有全樓、半邊樓之分;苗寨民居常選用飛檐翹角的吊腳木樓,侗族建筑的鼓樓和風雨橋各有風韻……另外,廣西飲食風俗在新時期桂劇中也有展現,比如爽滑、柔韌的米粉,咸香、味濃的油茶。
參考文獻
[1]林毓熙.精品催生與精品積累[J].劇本,2003,(1).
[2]楊戈平.文化精神彰顯人格魅力——參與桂劇大儒還鄉創作心得[J].中國戲劇,2007,(5).
[3]鐘敬文.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