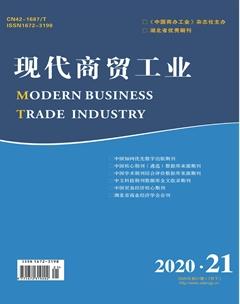“不配合親子鑒定”司法解釋的解讀與適用
舒春光
摘 要:隨著社會對兩性關系容忍度的開放,我國婚姻家庭倫理道德也處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民事訴訟實務中,不少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中,當事人一方因與子女的血緣關系產生爭議而申請親子鑒定時,發生另一方拒絕予以配合的情形。實踐中,多地法院就此類案件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亦出現差異。本文就這一法律理解適用方面略表拙見。
關鍵詞:不配合親子鑒定;司法解釋;解讀
1 “不配合親子鑒定”司法解釋規范分析
司法實際中,針對“不配合親子鑒定”情形,最高法院就案件事實認定適用依據方面作了相應規定,《婚姻法解釋(三)》第二條規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張成立。當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以下簡稱“該解釋條款”) 筆者認為,最高法制定該解釋條款的本意顯然旨在彌補民訴法適用依據的不足、指導人民法院對于當事人拒不配合親子鑒定的情形,運用了結合常理進行事實推理方式以維護當事人正當權益,同時以此起到引導、教育功能。
該解釋條款中“并已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內容在實務中通常被理解為申請鑒定當事人一方的舉證責任。若此內容作為一方提出申請前提條件,那么另一方為某種目的拒絕配合鑒定將是輕而易舉的選擇,那么產生的后果將是,法院以申請一方未能提供“必要證據”另一方不配合鑒定為由否定申請一方的非親子主張似乎符合本條規定的推理邏輯。按照如此理解,法院很可能會以一方不能“提供必要證據”為由輕易地認定其“與張小甲不存在親子關系”主張不能成立,導致不能維護鑒定申請方的合法權益,顯然違背了該解釋條款的立法本意,其也將失去大部分實際裁判價值,故筆者并不認同上述對該解釋條款適用方面的通常理解及適用。
2 “不配合親子鑒定”司法解釋案例分析
張甲王乙自由戀愛,2013年結婚后因工作需要聚少離多,2015年王乙生育一子張小甲,兩人因故感情不和,王乙將張小甲抱回娘家生活拒絕張甲探望,期間王乙多次要求與張甲離婚并撫養張小甲撫養費自理。期間,一自稱王乙男友的男性電話威脅張甲。為此張甲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的同時認為,王乙婚后行為異常并與其前男友未斷曖昧關系,張小甲與其并不存在親父子關系,并申請法院進行親子鑒定,但王乙以怕影響張小甲今后生活而拒絕配合鑒定。審理期間,王乙表示同意離婚,張甲稱因王乙對其早有戒備而未能獲取跟非親子相關的“必要證據”材料。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該解釋條款的通常理解及適用存在的問題可見一斑。張甲與王乙既然結婚就是奔信任而來,雖然聚少離多,本不存在戒心,即便像張甲陳述的王乙曾與其他異性有染,而時過境遷的今天若以法律人的邏輯要求張甲當時固定相關線索或證據顯然過于苛刻。實踐中,親子鑒定是最直接可靠的血緣關系證明。而涉及血緣關系的取證,單獨個體是無法完成的,需要其他相關人員的配合,但一旦出現其他親屬惡意干擾,不僅法院無法獲取親子關系真實情況的直接證據,而且請求鑒定一方就連最基本的關聯證據也可能無收獲。長此以往,不僅請求鑒定一方的合法權益無法受到保障,也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實而影響公正裁決。特別在是注重血親傳統的中國,無論是社會效果還是對個人今后生活的消極影響,后果應該是可以想象的。
3 “不配合親子鑒定”司法解釋規定的改進
盡管法不等同于理,多數法規卻出自于常理。若將該解釋條款內容理解為提供必要證據才是申請鑒定“前提條件”,那么在理和法之間必然形成沖突局面。這對于有合理、充分理由的張甲顯然是不公平的,顯然有悖于訴訟法“公正”宗旨。
當然,不可否認,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這一人人都應遵守的原則性,但同時民事訴訟法第七條明確民事案件應“以事實為根據”裁判原則。法律人眾所周知,證據的時效性和隱蔽性決定了很多客觀事實盡管確已發生,但相關證據材料卻因故難以被獲取或向法庭提供。因此,除法定不需舉證的情形外,若一味認為僅證據材料才是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顯然背離了訴訟法立法本意,可能會因有損于司法客觀公正而難以服眾。尤其離婚糾紛案例中涉及血緣關系事實查證方面的窘相較為突出。
該解釋條款“并已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中使用“并已”而未以“應當”或“必須”作為前綴詞語,足以排出其“責任性”的立法含義。該解釋條款顯然意在已提供必要證據的行為上而忽略未來能否舉證可能性。至此筆者的當然理解顯然是,“當事人一方主張不存在親子關系時,已提供必要證據系理所應當行為,但竭盡所能而未能提供的也合乎情理,即‘提供必要證據并非是申請親子鑒定的當然責任”。
如此,不僅保持了該解釋條款與訴訟法規舉證責任原則的統一性,又可避免當事人舉證能力所限產生的裁判尷尬。請求確認非親子關系的一方,不必為無必要證據而捶頭頓足,也有益于教育、引導不誠信并的一方放棄企圖逃避責任而不得不配合司法鑒定,保障當事人盡可能多的正當權益,節省司法資源,增強強制裁判的公信效應。
況且,該解釋條款中限定的“必要證據”指的應當是符合何種“必要性”標準的證據,并無相關規范性文件予以明確。“必要證據”的認定顯然更不具有實際可操作性。由此,更表明了該解釋條款意在不配合“親子鑒定”事實推定的適用上而非“提供必要證據”責任上。
參考文獻
[1]倪弦.論親子鑒定的相關法律問題[J].知識經濟,2011,(11).
[2]鐘富勝.生父拒做親子鑒定情形下法律責任判定[J].人民司法,2015,(16).
[3]樊坤.親子鑒定在法律訴訟中的應用[J].法制博覽,20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