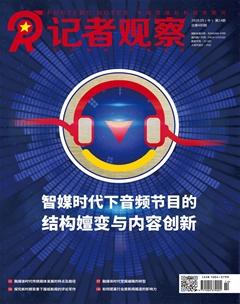淺析新媒體時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現(xiàn)狀及策略
任怡霏
摘要: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56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讓中國充滿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但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高速發(fā)展的今天,部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文化傳承卻令人擔(dān)憂。如何“搭乘”網(wǎng)絡(luò)發(fā)展下的新媒體快車,讓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文化瑰寶被大眾所熟知已成為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研究的焦點。本文以短視頻賬號“浪漫侗家七仙女”為研究對象,從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的現(xiàn)狀及新媒體傳播特點等方面探討新媒體時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策略。
關(guān)鍵詞:新媒體;侗族;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
(一)傳播者缺少新媒體傳播意識
黎平縣位于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東南角,人口逾40萬,分布有侗、苗、瑤、水、漢等民族,其中侗族人口占總?cè)丝?0%以上,因而素有“侗都”之稱。而“浪漫侗家七仙女”所在的蓋寶村則位于貴州省黎平縣西北尚重鎮(zhèn)的一個侗族聚居地,距離黎平縣城94公里,全村約3800人。“浪漫侗家七仙女”的組織者吳玉圣原本是貴州黎平縣一名普通的“80后”紀委工作人員,2018年受到縣委的組織調(diào)動來到了蓋寶村,成為了當(dāng)?shù)亍暗谝环鲐殨洝薄5怯捎诋?dāng)?shù)厍嗄耆舜蠖噙x擇外出務(wù)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一些年邁的老人以及留守兒童,如何發(fā)展經(jīng)濟,讓侗族傳統(tǒng)文化更好地傳承成了擺在他面前的首要問題。因為村民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受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居民更多傾向于發(fā)展農(nóng)村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如養(yǎng)殖業(yè)、種植業(yè)等。所以當(dāng)吳玉圣提出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旅游文化產(chǎn)業(yè)時立刻遭到了當(dāng)?shù)卮甯刹康姆磳Α?/p>
(二)傳播方式單一
在蓋寶村,侗族人民引以為傲的侗族大歌主要還依靠人際傳播方式傳承。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距今已具兩千多年歷史,在侗家人眼中,侗歌源于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對大自然的向往、辛勤勞作的贊頌。“飯養(yǎng)身,歌養(yǎng)心”,他們認為吃飯是身體上的需求,而侗族大歌則是心靈上、精神上的需要。這與儒家的樂論思想不謀而合,《論語》中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歌曲對我們心靈上的慰藉是亙古不變的。但是據(jù)記載,侗族人民于1958年12月才有了自己的規(guī)范文字,在這之前侗族大歌則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流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際傳播。
傳播學(xué)上傳播類型主要分為大眾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以及人際傳播。人際傳播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是由兩個個體系統(tǒng)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tǒng)。一般通過面對面或借助簡單的媒介傳播,具有非強制性和自發(fā)性的特點。但是與大眾傳播相比,人際傳播的受眾范圍小,并且容易受到地域、場景等因素的影響。
(三)受經(jīng)濟、地理空間等客觀因素限制
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在偏遠的貧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交通不便,道路的閉塞使之與外界的交流很少,信息獲取比較困難,存在信息不對等現(xiàn)象。在如今信息時代,信息已經(jīng)成為與物質(zhì)資源同等重要的能源,掌握更多的信息意味著有更多的機遇。
(一)受眾:模糊了傳播者與受傳者的邊界,互動性強
新媒體時代,受眾也是傳播者,以往的傳播主體邊界被模糊化。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信息傳播更多的是掌握在專業(yè)的從業(yè)者手里,強調(diào)“職業(yè)化、中心化”,并且受眾對信息的反饋具有延時性,難以形成及時的互動。但是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的今天,人們通過手機平臺可以及時地發(fā)表自己的所見所聞,成為信息的傳播者。
“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創(chuàng)始人吳玉圣是短視頻的愛好者,喜歡在閑暇時刷短視頻的他萌生了自己拍攝侗家美景并在網(wǎng)上發(fā)布的想法。于是他找來了當(dāng)?shù)?名侗族少女,以她們?yōu)橹鹘牵讯弊瀹?dāng)?shù)氐纳睢⒚谰啊⒘?xí)俗拍到了視頻平臺上。同時視頻平臺上的留言、直播彈幕功能,拉近了受眾與傳播者間之間的距離,形成了即時、有效的溝通互聯(lián)。
(二)內(nèi)容:形式豐富、信息量大
新媒體傳播利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在傳播的過程中可以同時搭載視頻、音頻、文字等內(nèi)容,以更為新穎的形式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媒介的出現(xiàn)都是人感官向外界延伸的過程。基于這一概念可以說新媒體豐富了人們感官上的體驗,例如VR沉浸式的游戲仿佛讓人置身于另一場景、AI主播24小時不間斷的新聞播報,這些都讓人們有了全新的體驗。“浪漫侗家七仙女”正是利用短視頻的這一優(yōu)勢傳遞著大量的信息,優(yōu)美的風(fēng)景、靚麗的人物加上動聽的侗族音樂讓受眾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感受著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洗滌,給人以聽覺、視覺上的享受。同時,短視頻通常以15秒為一個內(nèi)容進行發(fā)布,短小精簡的內(nèi)容有利于人們利用碎片化時間進行瀏覽,適用于多種場景。隨著人們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人們閱覽的習(xí)慣也在悄然改變,短視頻的出現(xiàn)正是順應(yīng)了時代的發(fā)展需要,以更加高效、輕松、娛樂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眾。
(一)有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立IP流量
首先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是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快速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新的思維模式,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強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結(jié)合少數(shù)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特點去思考用戶的需求,并不斷滿足。隨著國家的繁榮和技術(shù)的進步,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已基本上實現(xiàn)“村村通”,學(xué)會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去思考、推廣少數(shù)民族文化,順應(yīng)時代的新發(fā)展。IP中文稱“知識產(chǎn)權(quán)”,但是在這里筆者更愿意把它理解為文化品牌,當(dāng)某種文化或個人能以IP的形式出現(xiàn),意味著他們有龐大的流量,能衍生出更多產(chǎn)品,實現(xiàn)流量變現(xiàn)。例如故宮文創(chuàng)IP,故宮距今已經(jīng)有600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古老的故宮卻緊跟互聯(lián)網(wǎng)潮流,借用新興網(wǎng)絡(luò)平臺把自己打造成了網(wǎng)紅,衍生出表情包、影視劇、淘寶店等周邊產(chǎn)品。同樣當(dāng)“浪漫侗家七仙女”以IP形式出現(xiàn)在受眾視野里,將具有的品牌效應(yīng)將帶動更多產(chǎn)業(yè)發(fā)展。
(二)有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增強受眾互動
近期“李子柒”系列短視頻走紅海內(nèi)外給予筆者啟示,慢節(jié)奏的田園生活、跟奶奶深厚的情感以及來自大自然的饋贈都通過鏡頭表達出來,婉轉(zhuǎn)動聽的音樂、熟悉的鄉(xiāng)音使人有身臨其境的體驗。在如今快節(jié)奏時代,這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令人為之動容。精美的畫面視角、真實的鄉(xiāng)村生活狀態(tài)、立體飽滿的人物形象構(gòu)成了“李子柒”系列視頻的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在圖文并茂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人們的審美在不斷提高,對視覺、聽覺的感官要求也在提升,所以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更應(yīng)該將優(yōu)質(zhì)的內(nèi)容放在首位,在不斷提高拍攝技術(shù)的同時,內(nèi)容上也要充分展示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獨特之處。除此之外,也要加強與受眾的粘合度,采取線上互動、線下活動的交流方式,拉近彼此距離,推廣少數(shù)民族文化。
2019年7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內(nèi)蒙古考察時指出“我們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發(fā)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視少數(shù)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傳承。”少數(shù)民族文化是我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背景下下,我們要充分運用新媒體傳播的特點,來保護、發(fā)展、傳承少數(shù)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