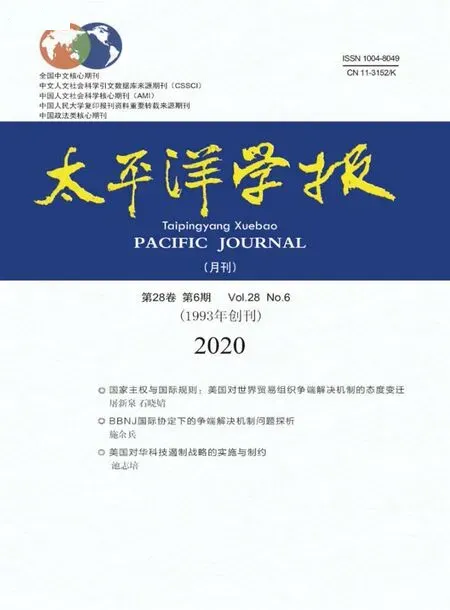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中國(guó)供給:緣起、問(wèn)題與對(duì)策
張 彬 胡曉珊
(1.武漢大學(xué),湖北 武漢430072)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①一般而言,凡是溢出國(guó)界的公共產(chǎn)品都稱之為“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根據(jù)區(qū)域范圍差異,可以分為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和全球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有的文獻(xiàn)也表述為“區(qū)域性公共產(chǎn)品”(Regional Public Goods),本文中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和區(qū)域性公共產(chǎn)品含義相同,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和區(qū)域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含義相同。中涉及金融領(lǐng)域的公共產(chǎn)品,指在特定的區(qū)域②本文中的區(qū)域包括依據(jù)地理劃分的區(qū)域和功能導(dǎo)向界定的區(qū)域。范圍內(nèi),由一國(guó)或多國(guó)提供且只服務(wù)于該特定區(qū)域金融穩(wěn)定或金融發(fā)展的組織、協(xié)議和金融制度安排。 隨著區(qū)域性合作日趨成為當(dāng)今國(guó)際合作的主流,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的作用不斷凸顯,中國(guó)把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作為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切入點(diǎn)。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基礎(chǔ)是區(qū)域內(nèi)主要國(guó)家的綜合國(guó)力。 隨著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不斷增長(zhǎng)并深度融入經(jīng)濟(jì)全球化進(jìn)程,中國(guó)提供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能力與意愿持續(xù)增加,先后籌建了亞洲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銀行(下文簡(jiǎn)稱“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基礎(chǔ)設(shè)施,為區(qū)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 但是,中國(guó)與美歐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金融綜合競(jìng)爭(zhēng)力上的差距依然較大,未來(lái)如何通過(guò)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來(lái)改進(jìn)自身不足是亟需解決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 在當(dāng)前國(guó)際金融市場(chǎng)激烈動(dòng)蕩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分析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理論緣起、實(shí)踐過(guò)程、發(fā)展趨勢(sh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并提出持續(xù)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具體對(duì)策。
基于以上研究主旨,本文的論證將分為四個(gè)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分析區(qū)域性崛起大國(guó)主動(dòng)參與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理論緣起;第二部分結(jié)合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方式,分析中國(guó)供給的實(shí)踐過(guò)程及存在的問(wèn)題;第三部分根據(jù)實(shí)踐過(guò)程中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提出中國(guó)供給的路徑選擇;第四部分提出保障中國(guó)持續(xù)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對(duì)策建議。
一、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理論緣起
“金融”作為體現(xiàn)國(guó)家競(jìng)爭(zhēng)力的關(guān)鍵要素,一直是國(guó)際交往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對(duì)于“金融”的討論往往與經(jīng)濟(jì)相結(jié)合,因此,國(guó)際關(guān)系中的金融存在兩層含義:一是各國(guó)如何消除或減少危機(jī),保持經(jīng)濟(jì)穩(wěn)定;二是金融資源配置跨越國(guó)界,促進(jìn)各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 金融從來(lái)不會(huì)局限于一國(guó)國(guó)境內(nèi),一國(guó)金融波動(dòng)往往是內(nèi)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一般而言,應(yīng)對(duì)金融危機(jī)的途徑分為兩條,一是國(guó)內(nèi)加強(qiáng)金融管制,二是面臨金融危機(jī)時(shí),接受美歐主導(dǎo)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提供的援助安排。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jī)爆發(fā)后,以區(qū)域合作提升應(yīng)對(duì)危機(jī)能力的區(qū)域金融安排開(kāi)始成為各國(guó)獲得金融安全的新選擇。①魯茉莉:“金融區(qū)域主義的興起和發(fā)展”,《國(guó)際觀察》,2014 年第 6 期,第 132 頁(yè)。這種區(qū)域金融安排是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針對(duì)如何應(yīng)對(duì)危機(jī)沖擊及維護(hù)金融穩(wěn)定達(dá)成的集體共識(shí),一國(guó)在安排中所獲得的收益并不會(huì)減少其他國(guó)家獲得相應(yīng)的收益;同時(shí),一個(gè)國(guó)家的金融穩(wěn)定對(duì)于其他國(guó)家維護(hù)金融穩(wěn)定具有正面影響,因而具有明顯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特征。
1.1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理論淵源
新區(qū)域主義和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兩個(gè)理論來(lái)源。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沿襲了新區(qū)域主義的分析方法,其理論邏輯則與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一致。
(1)新區(qū)域主義
區(qū)域主義是分析區(qū)域治理模式的理論框架,表現(xiàn)為一定區(qū)域內(nèi)的國(guó)家(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為實(shí)現(xiàn)相互合作的目標(biāo),在政治、經(jīng)濟(jì)、安全等方面建立的機(jī)制、進(jìn)程和安排等。②Christopher M. D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Routledge,2008, p.7.它產(chǎn)生于1951 年,以法德為首的歐洲國(guó)家為避免戰(zhàn)爭(zhēng)再次發(fā)生并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組成要素的區(qū)域內(nèi)流動(dòng),通過(guò)簽訂《巴黎條約》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率先開(kāi)始區(qū)域一體化的探索,并逐漸拓展至政治、安全領(lǐng)域。 20 世紀(jì)70 年代中后期,石油危機(jī)和滯脹導(dǎo)致全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緩慢,各經(jīng)濟(jì)體將重心放在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上,區(qū)域主義發(fā)展幾乎停滯。1991 年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全球經(jīng)濟(jì)復(fù)蘇,歐洲一體化加速,區(qū)域主義研究重新回歸理論研究前沿,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稱之為新區(qū)域主義。③鄭先武:“‘新區(qū)域主義’的核心特征”,《國(guó)際觀察》,2007年第 5 期,第 58 頁(yè)。新區(qū)域主義與傳統(tǒng)區(qū)域主義的區(qū)別在于,其理論背景以政治多極化格局替代了兩極冷戰(zhàn)格局,研究對(duì)象由區(qū)域國(guó)家集體行動(dòng)取代了單一大國(guó)主導(dǎo),研究范圍由經(jīng)濟(jì)、政治多領(lǐng)域的合作替代了某一特定問(wèn)題合作,新區(qū)域主義還倡導(dǎo)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等多元主體廣泛參與。
金融區(qū)域主義是新區(qū)域主義在金融領(lǐng)域的最新體現(xiàn),是應(yīng)對(duì)頻繁爆發(fā)的金融危機(jī)而出現(xiàn)的理論闡述。 歐盟、東盟與中日韓(10+3)在應(yīng)對(duì)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jī)的過(guò)程中,達(dá)成了一系列地區(qū)性應(yīng)急安排協(xié)定。 亞洲開(kāi)發(fā)銀行和美國(guó)布魯金斯學(xué)會(huì)一直重點(diǎn)關(guān)注,并于2010 年討論了金融區(qū)域主義對(duì)現(xiàn)行國(guó)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政治經(jīng)濟(jì)意義。 多梅尼科·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是金融區(qū)域主義研究的先行者,與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合作構(gòu)建金融區(qū)域主義的理論框架;①See Domenico Lombardi, “ Financial Regionalism: An Review of the Issu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ssues Paper, 2010.魯茉莉指出,“金融區(qū)域主義是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為避免對(duì)全球性金融治理機(jī)制的過(guò)分依賴,為應(yīng)對(duì)和防范金融危機(jī)而共同構(gòu)建的區(qū)域性金融合作機(jī)制”。②魯茉莉:“金融區(qū)域主義的興起與發(fā)展”,《國(guó)際觀察》,2014 年第 6 期,第 133 頁(yè)。
(2)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直接理論來(lái)源,它將公共產(chǎn)品理論研究的重點(diǎn)從全球或世界層面拓展到地區(qū)層面。 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最早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特征進(jìn)行了描述,指出其是在一個(gè)特定的地理范圍內(nèi)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jìng)爭(zhēng)性特征的產(chǎn)品。③Todd Sandler, “Global and Regional Public Goods: A Prognosis for Collective Action”, Fisc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98,pp. 221-247.瑞典外交部2000 年針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基本定義、在區(qū)域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區(qū)域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及安全保障的聯(lián)系等重點(diǎn)問(wèn)題,進(jìn)行了系統(tǒng)地梳理與初步地理論構(gòu)建。④See Patrik Staggren,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Working Paper,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Issues (EDGI),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Sweden,Stockholm,2000.以此為基礎(chǔ),托德·桑德勒和丹尼爾·阿爾塞(Daniel G. Arce)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類型、供給、融資等進(jìn)行了全面分析,基本形成現(xiàn)有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理論框架。 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樊勇明在借鑒國(guó)外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概念的闡述更加具體化,指出“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是有關(guān)國(guó)家為了滿足區(qū)域經(jīng)濟(jì)繁榮和區(qū)域安全穩(wěn)定,而共同提供并維持的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和合作”。⑤樊勇明:“東亞合作與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載《上海市社會(huì)科學(xué)界第五屆學(xué)術(shù)年會(huì)文集(2007 年度)》(世界經(jīng)濟(jì)·國(guó)際政治·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44-52 頁(yè)。而黃河則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和區(qū)域間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概念進(jìn)行區(qū)分,指出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具有兩方面的特點(diǎn):一方面,其服務(wù)范圍為某些特定區(qū)域,另一方面,其成本由特定區(qū)域內(nèi)的國(guó)家共同承擔(dān)。⑥黃河:“公共產(chǎn)品視角下的‘一帶一路’”,《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5 第 6 期,第 138-155 頁(yè)。李曉霞對(duì)東亞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模式進(jìn)行研究,提出東亞地區(qū)在安全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公共產(chǎn)品“分別遵循大國(guó)供給的‘次佳表現(xiàn)’模式和聯(lián)合供給的加權(quán)模式兩種不同的理想供給模式”。⑦李曉霞:“東亞區(qū)域性公共產(chǎn)品供求關(guān)系與核心問(wèn)題”,《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論壇》,2017 第 5 期,第 131 頁(yè)。馬斌、王潤(rùn)琦提出,“中國(guó)與歐亞地區(qū)國(guó)家共建‘一帶一路’,能對(duì)歐亞地區(qū)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體系形成有益補(bǔ)充”。⑧馬斌、王潤(rùn)琦:“‘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地區(qū)區(qū)域性公共產(chǎn)品供給體系重構(gòu)”,《復(fù)旦國(guó)際關(guān)系評(píng)論》,2018 年第2 期,第238 頁(yè)。
1.2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內(nèi)涵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核心是區(qū)域金融體系,其實(shí)際內(nèi)容是區(qū)域金融合作機(jī)制,其目標(biāo)是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金融危機(jī)的防范,其建設(shè)方式可以是區(qū)域性金融機(jī)構(gòu)的成立、區(qū)域金融協(xié)議談判的達(dá)成,也可以是合作基金、匯率制度功能性合作等非制度化方式。 考慮到區(qū)域金融體系建設(shè)是長(zhǎng)期的過(guò)程,以應(yīng)對(duì)危機(jī)為目標(biāo)的雙邊貨幣互換協(xié)議也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之一。 因此,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特征包括,其一,內(nèi)容上是涵括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國(guó)家(地區(qū))的區(qū)域金融合作機(jī)制,如區(qū)域性金融合作機(jī)構(gòu)、兩國(guó)間的貨幣互換協(xié)議、區(qū)域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等;其二,規(guī)劃上涵括區(qū)域內(nèi)若干國(guó)家(地區(qū))的合作,如商談建立單一貨幣區(qū)(OCA)、籌建地區(qū)開(kāi)發(fā)金融機(jī)構(gòu)、協(xié)調(diào)區(qū)域各國(guó)金融政策、開(kāi)展功能性合作等;其三,目標(biāo)上涵括金融便利化和金融風(fēng)險(xiǎn)防范,通過(guò)金融便利化的機(jī)制安排,消除各國(guó)因金融政策差異對(duì)資金流動(dòng)的約束,實(shí)現(xiàn)金融資源跨境合理配置,構(gòu)建區(qū)域性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以防范和應(yīng)對(duì)金融風(fēng)險(xiǎn)。
1.3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類型劃分
按照托德·桑德勒對(duì)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分類方法,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可以劃分成四種類型:“純公共產(chǎn)品”(pure public goods)、“準(zhǔn)公共產(chǎn)品”(impure public goods)、“俱樂(lè)部公共產(chǎn)品”(club goods)和“聯(lián)合產(chǎn)品”(joint goods)。①Todd Sandler and Daniel G. Arce, Regional Public Goods:Typologies, Provision,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for the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Isuues,Swedish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Stockholm, 2002, p.17.從個(gè)體貢獻(xiàn)與公共產(chǎn)品總體水平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角度來(lái)看,公共產(chǎn)品主要通過(guò)簡(jiǎn)單累加、最優(yōu)環(huán)節(jié)、最弱關(guān)聯(lián)以及加權(quán)總和四種方式進(jìn)行供給。②[西]安東尼·埃斯特瓦多道爾等著,張建新等譯:《區(qū)域性公共產(chǎn)品:從理論到實(shí)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8-19 頁(yè)。依照上述公共產(chǎn)品類型與供給方式,本文將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進(jìn)行綜合分類(參見(jiàn)表1)。

表1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分類
參照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按照成本分擔(dān)和受益范圍主要分為準(zhǔn)公共產(chǎn)品和俱樂(lè)部產(chǎn)品;按照供應(yīng)方式主要采用加權(quán)總和與最優(yōu)環(huán)節(jié)(參見(jiàn)表2)。

表2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分類
值得注意的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與一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不同在于:一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必須有籌資機(jī)制予以保證,而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本身就是資金方面的機(jī)制安排,它一方面作為一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融資渠道,滿足區(qū)域內(nèi)共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對(duì)區(qū)域內(nèi)部分或全部國(guó)家供給資金,滿足個(gè)性需求。 比較而言,金融資源的稀缺性使東亞、中亞、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區(qū)域?qū)鹑诠伯a(chǎn)品的接受性更強(qiáng),而成本和收益的可衡量性更讓各區(qū)域供給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愿望更強(qiáng)。
二、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中國(guó)供給實(shí)踐及問(wèn)題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將金融作為結(jié)構(gòu)性因素納入?yún)^(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分析框架,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金融協(xié)商制度或安排等無(wú)形的形式,而不是資金本身。
2.1 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歷程
縱觀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過(guò)程,可以劃分為被動(dòng)供給、主動(dòng)參與和倡導(dǎo)供給①劉雨辰:“從參與者到倡導(dǎo)者:中國(guó)供給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身份變遷”,《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5 年第 9 期,第 76-86 頁(yè)。三個(gè)階段,各階段變化伴隨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主動(dòng)性持續(xù)增強(qiáng)。
第一,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jī)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jī)之前,屬于被動(dòng)供給階段。 這是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起步階段,該階段推動(dòng)力源于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jī)和1999年歐元區(qū)的成立。 經(jīng)過(guò)20 多年的改革開(kāi)放,中國(guó)外匯儲(chǔ)備從1997 年的1 399 億美元增長(zhǎng)到2008 年6 月末的 18 088 億美元,②國(guó)家外匯管理局國(guó)際收支分析小組編:《2008 上半年中國(guó)國(guó)際收支報(bào)告》,中國(guó)金融出版社,2009 年版,第7 頁(yè)。金融基礎(chǔ)設(shè)施逐漸完善,金融企業(yè)實(shí)力顯著增強(qiáng)。 這個(gè)階段首先是參與和推動(dòng)?xùn)|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的落地。 2000 年5 月,東盟十國(guó)與中日韓三國(guó)在泰國(guó)清邁談判達(dá)成了《清邁協(xié)議》,正式成立東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 其次是中國(guó)與多國(guó)就雙邊貨幣互換達(dá)成了眾多協(xié)議。 從2001 年開(kāi)始,中國(guó)先后與泰國(guó)、日本、韓國(guó)和印度尼西亞等國(guó)中央銀行就雙邊貨幣互換簽訂了協(xié)議,合計(jì)金額超過(guò)210 億美元。③根據(jù)中國(guó)金融信息網(wǎng)(http:/ /www.xinhua08.com)、中國(guó)人民銀行網(wǎng)站(http:/ /www.pbc.gov.cn)數(shù)據(jù)整理,訪問(wèn)時(shí)間:2019年 8 月 20 日。
第二,2008 年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至 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屬于主動(dòng)參與階段。 中國(guó)在該階段參與區(qū)域金融合作,由被動(dòng)變?yōu)橹鲃?dòng),開(kāi)始與區(qū)域內(nèi)其他國(guó)家合作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 首先是擴(kuò)大東亞外匯儲(chǔ)備庫(kù)。 在中國(guó)和日本的不斷推動(dòng)下,《清邁協(xié)議》由一系列雙邊協(xié)議擴(kuò)展為多邊協(xié)議,東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的規(guī)模經(jīng)兩次擴(kuò)容后達(dá)到2 400 億美元。④“東盟與中日韓決定加強(qiáng)區(qū)域金融安全網(wǎng)建設(shè)”,人民網(wǎng),2012 年 5 月 4 日, http:/ /japan.people.com.cn/35463/7807753.html。其次是擴(kuò)大貨幣互換協(xié)議達(dá)成的規(guī)模。 截至2013 年底,中國(guó)已經(jīng)與全球范圍內(nèi)的24 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中央銀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xié)議,總規(guī)模達(dá)到26 682 億元人民幣。⑤同②。
第三, 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屬于倡導(dǎo)供給階段。 這一階段,中國(guó)對(duì)外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進(jìn)程明顯加快,主要呈現(xiàn)出以下特征:其一,主動(dòng)供給金融機(jī)構(gòu)類公共產(chǎn)品。 2014 年,中國(guó)在上海成立了旨在提高金磚國(guó)家金融穩(wěn)定性的金磚國(guó)家新開(kāi)發(fā)銀行(簡(jiǎn)稱“金磚銀行”)。 2015 年,中國(guó)在北京成立了旨在支持亞洲各國(guó)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亞投行。此外,中國(guó)還致力于推進(jìn)上海合作組織開(kāi)發(fā)銀行的建立。 金融機(jī)構(gòu)類公共產(chǎn)品是中國(guó)供給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典型代表。 其二,推動(dòng)雙邊和多邊金融合作基金的建立。 主要通過(guò)國(guó)家外匯管理部門和國(guó)有政策性銀行發(fā)起設(shè)立,包括中非發(fā)展基金、中國(guó)—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 其中,中非發(fā)展基金設(shè)立于2006 年,是中國(guó)最早供給的基金類公共產(chǎn)品。 基金類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規(guī)模也由2006 年的50 億美元,發(fā)展到2019 年底超過(guò)1 500 億美元。⑥根據(jù)中國(guó)人民銀行網(wǎng)站(http:/ /www.pbc.gov.cn)、新華網(wǎng)(http:/ /www.xinhuanet.com)等信息整理,訪問(wèn)時(shí)間:2019 年 6 月 4日、2020 年 3 月 19 日。其三,構(gòu)建新的金融穩(wěn)定性公共產(chǎn)品。 2014 年7 月15 日,中國(guó)會(huì)同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各國(guó)共同簽署條約,設(shè)立資金規(guī)模為1 000 億美元的金磚國(guó)家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 其四,繼續(xù)擴(kuò)大貨幣互換協(xié)議規(guī)模。 截至2019 年末,日本、英國(guó)、歐盟等39 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中央銀行與中國(guó)人民銀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xié)議,協(xié)議總規(guī)模高達(dá)30 025 億元人民幣①不含已失效、暫未續(xù)簽7 467 億元人民幣。(參見(jiàn)表3)。

表3 貨幣互換協(xié)議類公共產(chǎn)品(單位:億人民幣)
2.2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中國(guó)供給模式
現(xiàn)有文獻(xiàn)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模式缺少專門的闡述,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模式的探討則沿著兩個(gè)方面展開(kāi),一方面按照供給國(guó)家的特點(diǎn),另一方面按照個(gè)體貢獻(xiàn)與公共產(chǎn)品總體水平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其一,從供給主體的特點(diǎn)來(lái)看。 理論界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模式的探討主要集中在歐洲、北美、東亞三個(gè)地區(qū)。②黃河、戴麗婷:“‘一帶一路’公共產(chǎn)品與中國(guó)特色大國(guó)外交”,《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8 年第 8 期,第 50-61 頁(yè)。根據(jù)供給主體的特點(diǎn),比較典型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模式可以分為,以歐盟為代表的核心國(guó)主導(dǎo)供給模式、以北美自由貿(mào)易區(qū)為代表的霸權(quán)國(guó)主導(dǎo)供給模式、以東盟“10+3”為代表的小國(guó)集團(tuán)主導(dǎo)供給模式。 隨著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增強(qiáng)和區(qū)域金融合作的深化,中國(guó)在合作共贏的框架下,單獨(dú)供給或聯(lián)合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參照上述三種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模式的分類方法,中國(guó)參與供給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可以分為核心國(guó)主導(dǎo)供給模式、兩國(guó)聯(lián)合供給模式和區(qū)域合作組織主導(dǎo)供給模式三種。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模式不是固定的,如在金融機(jī)構(gòu)類公共產(chǎn)品中,亞投行是核心國(guó)家主導(dǎo)供給模式,金磚銀行是區(qū)域合作組織主導(dǎo)供給模式;在基金類公共產(chǎn)品中,絲路基金、中非基金基本都是核心國(guó)主導(dǎo)供給模式;貨幣互換類公共產(chǎn)品是兩國(guó)聯(lián)合供給模式;金磚國(guó)家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是合作組織主導(dǎo)供給模式。 中國(guó)供給的實(shí)踐表明,與其他經(jīng)濟(jì)大國(guó)一樣,中國(guó)無(wú)法長(zhǎng)期單獨(dú)承擔(dān)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主要成本,因此,與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進(jìn)行成本合理分擔(dān)的供給模式是更加現(xiàn)實(shí)的選擇。
其二,從個(gè)體貢獻(xiàn)與公共產(chǎn)品總體水平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來(lái)看。 根據(jù)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中國(guó)供給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主要分為,大國(guó)供給的最優(yōu)環(huán)節(jié)模式與聯(lián)合供給的加權(quán)總和模式。 前者主要由中國(guó)的貢獻(xiàn)決定公共產(chǎn)品總體水平,包括多邊合作發(fā)展基金和貨幣互換協(xié)議。 后者主要由于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無(wú)法通過(guò)平均分配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供給,為了實(shí)現(xiàn)聯(lián)合供給目的,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各參與國(guó)在成本和收益之間需要一個(gè)平衡點(diǎn),從而塑造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加權(quán)總和模式,包括區(qū)域共同儲(chǔ)備庫(kù)、區(qū)域性金融機(jī)構(gòu)、開(kāi)發(fā)性金融機(jī)構(gòu)等。
另外,按照作用和目的劃分,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可以分為穩(wěn)定型金融公共產(chǎn)品與發(fā)展型金融公共產(chǎn)品。 前者主要用于應(yīng)對(duì)金融危機(jī)而簽署的協(xié)議或制訂的制度,如東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金磚國(guó)家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等;后者則是為實(shí)現(xiàn)在區(qū)域范圍內(nèi)配置金融資源與促進(jìn)區(qū)域共同發(fā)展,由區(qū)域內(nèi)各國(guó)共同建立的組織或簽訂的協(xié)議。
2.3 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實(shí)踐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
當(dāng)今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格局正發(fā)生深刻復(fù)雜變化,單獨(dú)或聯(lián)合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一方面能夠推進(jìn)中國(guó)參與全球規(guī)則的制定,另一方面能夠構(gòu)建自身發(fā)展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是基于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內(nèi)在需求的聚合供給,大多中國(guó)學(xué)者目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滿足供給條件的理論分析,往往忽略了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需求偏好、有效供給機(jī)制的深入研究。
第一,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需求偏好匹配困難。 從中國(guó)供給的四類區(qū)域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來(lái)看,貨幣互換和應(yīng)急儲(chǔ)備安排由中國(guó)人民銀行負(fù)責(zé);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區(qū)域性金融合作機(jī)構(gòu)由財(cái)政部負(fù)責(zé);雙邊、多邊的區(qū)域性合作基金主要由外匯管理局、國(guó)家開(kāi)發(fā)銀行和中國(guó)進(jìn)出口銀行負(fù)責(zé)。 可以說(shuō),中國(guó)對(duì)于金融公共產(chǎn)品提供的國(guó)內(nèi)負(fù)責(zé)部門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安排,但是對(duì)于供給過(guò)程中國(guó)內(nèi)各部門對(duì)供給區(qū)域的分析,未見(jiàn)相關(guān)的制度安排,至少目前未能見(jiàn)諸文字,而這卻是對(duì)供給效果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不同的地理區(qū)域具有不同的文化認(rèn)同、戰(zhàn)略信任和區(qū)域外大國(guó)的競(jìng)爭(zhēng),這就導(dǎo)致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具有不同的需求規(guī)模和類型。 同時(shí),中國(guó)在某區(qū)域供給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若能夠與所在區(qū)域的需求更好匹配,則能提高供給的有效性。
第二,區(qū)域外大國(guó)和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限制發(fā)展空間。 區(qū)域戰(zhàn)略的重要著力點(diǎn)是將比較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為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這就意味著必須妥善處理與區(qū)域外大國(guó)以及既有國(guó)際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關(guān)系。 首先,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成本或收益具有外部性,經(jīng)濟(jì)全球化使得世界主要大國(guó)的利益遍布各區(qū)域,新增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不可避免地影響區(qū)域外大國(guó)的利益,區(qū)域外大國(guó)將采取措施避免利益損失或獲得收益補(bǔ)償。 其次,中國(guó)提升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自主性,并不謀求替代既有的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或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目的是實(shí)現(xiàn)與美國(guó)等主要經(jīng)濟(jì)體的互補(bǔ)性供給,但是很難獲得現(xiàn)有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大國(guó)的信任。 最后,在“碎片化”的國(guó)際金融體系中,即使在創(chuàng)立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時(shí),其定位以補(bǔ)充與改良為主,與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在實(shí)踐中的競(jìng)爭(zhēng)也不可避免,現(xiàn)有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打壓和排擠必然壓縮發(fā)展空間。
第三,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穩(wěn)定供給與金融風(fēng)險(xiǎn)防范的兩難選擇。 區(qū)域復(fù)雜多變的安全形勢(shì)和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問(wèn)題會(huì)對(duì)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帶來(lái)沖擊。 作為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后來(lái)者,不可避免地進(jìn)入一些高風(fēng)險(xiǎn)的供給地帶。其一,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往往面對(duì)區(qū)域尚未構(gòu)建整體合作安排、區(qū)域內(nèi)各國(gu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懸殊、法律制度不完善等不利因素。 由于這些因素存在,區(qū)域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防范缺乏強(qiáng)有力的制度體系支撐。 其二,區(qū)域內(nèi)部分國(guó)家和地區(qū)政治不穩(wěn)定。 中亞、西北亞、拉丁美洲、非洲多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和地區(qū),國(guó)內(nèi)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瓶頸、戰(zhàn)爭(zhēng)風(fēng)險(xiǎn)和國(guó)家間領(lǐng)土主權(quán)爭(zhēng)端等問(wèn)題影響國(guó)家政治穩(wěn)定性。 其三,部分區(qū)域缺少經(jīng)濟(jì)金融合作基礎(chǔ),各國(guó)利益協(xié)調(diào)困難,資金籌集、成本分擔(dān)和風(fēng)險(xiǎn)防范機(jī)制難以構(gòu)建,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穩(wěn)定供給面臨較大挑戰(zhàn)。
第四,在新區(qū)域主義背景下,國(guó)內(nèi)金融發(fā)展水平與對(duì)外金融合作水平具有非同步性。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能力依賴于供給主體的金融發(fā)展水平,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建立的基礎(chǔ)是美歐當(dāng)時(shí)的金融發(fā)展水平,這與當(dāng)時(shí)世界先進(jìn)的金融發(fā)展水平是同步的。 中國(guó)國(guó)內(nèi)已經(jīng)建立相對(duì)成熟的金融制度體系,但金融發(fā)展水平與美歐金融發(fā)展水平存在差距。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作為中國(guó)開(kāi)展對(duì)外金融合作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需采用世界流行的制度建設(shè)模式才可能具有普遍適用性,無(wú)論是亞投行,還是各種對(duì)外合作基金,都需要完善的內(nèi)部治理體系與有效的制度運(yùn)作機(jī)制來(lái)保證運(yùn)行。
第五,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對(duì)供給的影響仍將存在。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一旦供給,就應(yīng)該具備可持續(xù)性。 2018 年以來(lái),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的加劇,雖然不會(huì)直接沖擊現(xiàn)有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但其影響不容忽視。 其一,貿(mào)易爭(zhēng)端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穩(wěn)定性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 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使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企穩(wěn)回升變得更加嚴(yán)峻復(fù)雜,增大中國(guó)實(shí)現(xiàn)高質(zhì)量增長(zhǎng)的難度。 其二,貿(mào)易爭(zhēng)端破壞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外部環(huán)境。 美國(guó)在貿(mào)易爭(zhēng)端中提出的限制性措施可能沖擊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與中國(guó)的經(jīng)貿(mào)往來(lái),減弱這些國(guó)家的信任水平。 其三,中國(guó)為應(yīng)對(duì)未來(lái)美國(guó)可能增加的限制性措施,需要提升防范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等級(jí),這將導(dǎo)致國(guó)內(nèi)金融資源的稀缺性特征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 2020 年初,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jīng)貿(mào)協(xié)議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產(chǎn)生積極影響,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fā),經(jīng)貿(mào)協(xié)議落實(shí)難度加大,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面臨更大挑戰(zhàn)。
三、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路徑選擇
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既可以視為中國(guó)提升金融綜合競(jìng)爭(zhēng)力的“對(duì)策”,也可以視為促進(jìn)國(guó)際金融體系改革而進(jìn)行的制度創(chuàng)新,但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時(shí)間較短,在供給主體、供給模式方面遠(yuǎn)未形成成熟經(jīng)驗(yàn),供給效果有待實(shí)踐檢驗(yàn),未來(lái)如何選擇有效的供給路徑,①崔野、王琪:“全球公共產(chǎn)品視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現(xiàn)、成因與應(yīng)對(duì)”,《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9 年第 1 期,第 60-71 頁(yè)。離不開(kāi)對(duì)供給原因的再考量。
3.1 供給原因分析
中國(guó)作為發(fā)展中大國(guó),自身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需求是供給的根本原因。 現(xiàn)有的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無(wú)法滿足中國(guó)的需求,這就使得中國(guó)不得不聯(lián)合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合作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
第一,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遠(yuǎn)遠(yuǎn)滿足不了需求。 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基礎(chǔ)是成立時(shí)美歐金融體系的發(fā)展程度。 美歐金融體系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斷演化進(jìn)步,但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基本框架體系未發(fā)生根本變化。 面對(duì)國(guó)際金融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xiǎn)的上升,掌握現(xiàn)有國(guó)際金融體系控制權(quán)的美歐,很難推出長(zhǎng)遠(yuǎn)的金融改革措施,②章玉貴:“全球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與中國(guó)金融資本力鍛造”,《國(guó)際觀察》,2015 年第 2 期,第 30-42 頁(yè)。其直接后果是現(xiàn)有國(guó)際金融體系的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能力不足,成為制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障礙。③張群:“東亞區(qū)域公共產(chǎn)品供給與中國(guó)—東盟合作”,《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7 年第 5 期,第 44-54 頁(yè)。通過(guò)資本加總和供給模式分析,現(xiàn)在所有全球性金融機(jī)構(gòu)可供給的金融資源總量?jī)H約1 萬(wàn)億美元,④筆者根據(jù)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guó)際復(fù)興開(kāi)發(fā)銀行(IBRD)和國(guó)際金融公司(IFC)等全球性金融機(jī)構(gòu)的法定資本規(guī)模、籌資方式和供給方式分析整理。但當(dāng)前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需求巨大。 首先,世界發(fā)展對(duì)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需求強(qiáng)勁,到2040 年全球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資金缺口將達(dá)15 萬(wàn)億美元,⑤20 國(guó)集團(tuán)(G20)旗下全球基礎(chǔ)設(shè)施中心編:《全球基礎(chǔ)設(shè)施展望》,牛津經(jīng)濟(jì)研究院,2017 年版,第3 頁(yè)。而全球性金融機(jī)構(gòu)每年供給約600 億美元⑥筆者根據(jù)正常年度各全球性金融機(jī)構(gòu)每年實(shí)際發(fā)放貸款數(shù)據(jù)匯總分析并整理。的能力遠(yuǎn)不能滿足需求,并且全球私人部門在商業(yè)化的風(fēng)險(xiǎn)控制機(jī)制下資金供給有限,巨大的資金缺口亟需新的國(guó)際合作投資管理機(jī)制和安排來(lái)彌補(bǔ)。 其次,從2007 年美國(guó)次貸危機(jī),再到歐洲債務(wù)危機(jī),有效救助機(jī)制的缺位十分明顯,構(gòu)建新的國(guó)際救助機(jī)制特別迫切。 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形勢(shì)下,經(jīng)濟(jì)實(shí)力雄厚的歐元區(qū)面對(duì)大量債務(wù)違約時(shí),僅僅依靠已有的危機(jī)救助機(jī)制也難以應(yīng)對(duì)。 最后,發(fā)展中國(guó)家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融資需求是全方位的,現(xiàn)有全球性金融機(jī)構(gòu)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發(fā)展路徑的多樣化缺乏理解,難以采取措施滿足其融資需求。
第二,外交轉(zhuǎn)型發(fā)展需要。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在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需求深度對(duì)接的基礎(chǔ)上形成,其通過(guò)堅(jiān)持收益與成本相匹配的原則,既可以避免區(qū)域內(nèi)大國(guó)全部作為和區(qū)域內(nèi)小國(guó)的不作為,又可以有效促進(jìn)區(qū)域內(nèi)更高層次的合作,深化各國(guó)的政治互信,塑造穩(wěn)定的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jì)秩序。①陳小鼎:“區(qū)域公共產(chǎn)品與中國(guó)周邊外交新理念的戰(zhàn)略內(nèi)涵”,《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6 年第 8 期,第 44-45 頁(yè)。當(dāng)今,中國(guó)外交理念轉(zhuǎn)向堅(jiān)持多邊主義,構(gòu)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guó)際關(guān)系,這是基于自身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模、貿(mào)易規(guī)模及財(cái)政實(shí)力等資源稟賦做出的抉擇。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推動(dòng)區(qū)域合作見(jiàn)效快,有助于推動(dòng)外交進(jìn)程。
第三,比較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為對(duì)外供給優(yōu)勢(shì)。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經(jīng)常被認(rèn)為是,一國(guó)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的國(guó)內(nèi)公共產(chǎn)品在區(qū)域?qū)用娴难由欤簿褪钦f(shuō),供給國(guó)國(guó)內(nèi)優(yōu)勢(shì)公共產(chǎn)品和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能夠相互替代。 但值得注意的是,比較優(yōu)勢(shì)要形成對(duì)外供給優(yōu)勢(shì),不但取決于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國(guó)家的外交戰(zhàn)略選擇和國(guó)家意志,而且取決于該國(guó)國(guó)內(nèi)綜合國(guó)力的變化,以及國(guó)際合作政策制定者對(duì)于區(qū)域合作行為的成本和實(shí)際收益之間的權(quán)衡。 區(qū)域金融合作是中國(guó)在區(qū)域內(nèi)的比較優(yōu)勢(shì)所在,通過(guò)態(tài)勢(shì)分析法(SWOT)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進(jìn)行分析,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增長(zhǎng)、金融實(shí)力不斷增強(qiáng)、國(guó)內(nèi)高儲(chǔ)蓄率和巨額外匯儲(chǔ)備能夠支撐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穩(wěn)定供給。

表4 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態(tài)勢(shì)分析
第四,實(shí)力與影響力匹配的需要。 在政治上,中國(guó)積極倡導(dǎo)和參與構(gòu)建跨國(guó)家的區(qū)域合作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所提出的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獲得廣泛支持,自身在國(guó)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在經(jīng)濟(jì)上,中國(gu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在全球進(jìn)出口貿(mào)易中占據(jù)重要地位,理論上應(yīng)該在全球和地區(qū)事務(wù)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事實(shí)上,中國(guó)面臨將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轉(zhuǎn)換為國(guó)際綜合影響力的艱難挑戰(zhàn)。 當(dāng)今,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控制權(quán)成為世界主要經(jīng)濟(jì)體之間競(jìng)爭(zhēng)的目標(biāo),因此,中國(guó)需積極融入?yún)^(qū)域合作的進(jìn)程,將不斷增長(zhǎng)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轉(zhuǎn)化成對(duì)區(qū)域的影響力。 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最終的消費(fèi)者是所在區(qū)域內(nèi)全體公民,只有不斷向世界供給有形、無(wú)形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中國(guó)才能真正提升國(guó)家綜合實(shí)力。
3.2 供給路徑選擇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過(guò)程是區(qū)域內(nèi)各成員國(guó)為滿足共同的金融治理目標(biāo),通過(guò)集體協(xié)同合作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過(guò)程。 共同目標(biāo)、集體認(rèn)同和授權(quán)模式是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關(guān)鍵三要素。
(1)實(shí)現(xiàn)共同利益目標(biāo)是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前提。 按照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所言,“促進(jìn)國(guó)際機(jī)制形成的激勵(lì)因素取決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②[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zhǎng)和等譯:《霸權(quán)之后——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中的合作與紛爭(zhēng)》,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96 頁(yè)。共同的利益是作為理性行為體參與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前提,在共同利益基礎(chǔ)上制定的金融治理目標(biāo)為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加入供給框架,提供了充足的動(dòng)力。
首先,新增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利益相關(guān)方包括中國(guó)、區(qū)域內(nèi)其他國(guó)家和區(qū)域外大國(guó)。 中國(guó)、區(qū)域內(nèi)其他國(guó)家合作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收益,因而作為共同利益相關(guān)方較易理解。 本文將區(qū)域外大國(guó)作為利益相關(guān)方,主要考慮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產(chǎn)生的外部性會(huì)影響區(qū)域外大國(guó)利益,其將采取措施對(duì)區(qū)域內(nèi)各成員國(guó)施壓或直接阻止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 因此,將區(qū)域外大國(guó)納入?yún)^(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利益相關(guān)方范圍,保障其利益或?qū)ζ淅孢M(jìn)行補(bǔ)償,有助于形成利益共同體。
其次,預(yù)期收益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根本驅(qū)動(dòng)力。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是參與國(guó)國(guó)家利益的反映,是涵括經(jīng)濟(jì)、政治、安全等主要方面收益的結(jié)合體。 這些收益的顯性表現(xiàn)是經(jīng)濟(jì)收益,但即使是經(jīng)濟(jì)收益也無(wú)法直接計(jì)量,更不用說(shuō)政治穩(wěn)定、金融安全等宏觀層面的收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國(guó)從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獲得的收益,來(lái)源于供給和消費(fèi)的全過(guò)程。
最后,金融問(wèn)題是所有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核心問(wèn)題,經(jīng)濟(jì)利益也是各國(guó)的核心利益所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目標(biāo)既可以是促進(jìn)金融資源跨境流動(dòng),也可以是維護(hù)金融安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各成員國(guó)讓渡經(jīng)濟(jì)利益后獲得的收益不一定直接通過(guò)金融利益表現(xiàn)出來(lái),但它終究會(huì)通過(guò)經(jīng)濟(jì)利益回歸到金融體系。因此,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目標(biāo)的確定是供給路徑選擇的基礎(chǔ)。
(2)區(qū)域性集體認(rèn)同感的獲取是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基礎(chǔ)。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集體認(rèn)同感分為國(guó)內(nèi)和國(guó)際區(qū)域?qū)用妫?/p>
其一,在國(guó)內(nèi)層面完善國(guó)家的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機(jī)制。 中國(guó)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問(wèn)題上具有高度共識(shí)和強(qiáng)大執(zhí)行力,這是其他大國(guó)難以具備的,但同樣需要增強(qiáng)國(guó)內(nèi)各方的集體認(rèn)同。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huì)成立,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國(guó)家層面的決策、協(xié)調(diào)能力進(jìn)一步提升。 中國(guó)在提供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過(guò)程中,中國(guó)人民銀行、國(guó)家外匯管理局、商務(wù)部、財(cái)政部等機(jī)構(gòu)需加強(qiáng)協(xié)調(diào),在提供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方面發(fā)揮合力作用。 國(guó)家國(guó)際發(fā)展合作署在開(kāi)展對(duì)外援助時(shí),統(tǒng)籌考慮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與對(duì)外援助銜接問(wèn)題,提升中國(guó)在各地區(qū)的影響力。
其二,在國(guó)際區(qū)域?qū)用嫣嵘齾^(qū)域內(nèi)國(guó)家的集體認(rèn)同感。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需要具有可持續(xù)性的國(guó)際平臺(tái)支撐,制度建設(shè)和集體認(rèn)同可以為國(guó)際平臺(tái)建設(shè)創(chuàng)造條件。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創(chuàng)建是在政治互信前提下達(dá)成的合作共識(shí),供給過(guò)程是利益深化融合的過(guò)程,應(yīng)當(dāng)逐漸構(gòu)建合作的約束機(jī)制。 對(duì)于政局穩(wěn)定性不強(qiáng)、國(guó)家政策不連貫的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創(chuàng)建公共產(chǎn)品時(shí)需鼓勵(lì)其制定政策連貫的制度安排,提升所有國(guó)家的集體認(rèn)同感。 與此同時(shí),中國(guó)在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過(guò)程中,既要考慮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對(duì)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戰(zhàn)略層面和心理層面的沖擊,也要考慮隨著公共產(chǎn)品消費(fèi)者擴(kuò)增,如何建立有效供給體系,保障持續(xù)性供給,特別要避免將公共產(chǎn)品供應(yīng)“私物化”的行為。①?gòu)埓海骸皣?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供應(yīng)競(jìng)爭(zhēng)及其出路——亞太地區(qū)二元格局與中美新型大國(guó)關(guān)系建構(gòu)”,《當(dāng)代亞太》,2014 年第6期,第 58 頁(yè)。
其三,設(shè)計(jì)合理的授權(quán)模式是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關(guān)鍵。 針對(duì)不同類型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靈活使用授權(quán)模式,是解決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需求偏好匹配困難的關(guān)鍵,同時(shí)也能有效防范金融風(fēng)險(xiǎn)。 中國(guó)現(xiàn)有的授權(quán)分為兩個(gè)層次:一個(gè)層次是“委托—代理”式授權(quán)(如亞投行、金磚銀行和東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雖然由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聯(lián)合供給,但借助委托—代理的方式進(jìn)行授權(quán),即委托專門成立的代理機(jī)構(gòu)進(jìn)行運(yùn)營(yíng);另一層次是直接授權(quán)(如貨幣互換協(xié)議、雙邊合作基金),即由國(guó)家相關(guān)部門直接簽署合作協(xié)議或?qū)ν夤┙o金融資源,強(qiáng)調(diào)金融公共產(chǎn)品提供的精準(zhǔn)性。 按照國(guó)際慣例,中國(guó)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應(yīng)按不同時(shí)期進(jìn)行授權(quán),在日常運(yùn)行時(shí)期,通過(guò)委托—代理的方式授權(quán)區(qū)域性金融組織對(duì)區(qū)域內(nèi)危機(jī)國(guó)家進(jìn)行支持和救助,可以降低日常運(yùn)營(yíng)成本;當(dāng)出現(xiàn)全球性或區(qū)域性金融危機(jī)的時(shí)候,通過(guò)貨幣互換協(xié)議已經(jīng)形成的網(wǎng)絡(luò),可有選擇地向特定區(qū)域和國(guó)家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
四、中國(guó)持續(xù)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對(duì)策建議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出現(xiàn)至今不到20年時(shí)間,除美歐等主要國(guó)家國(guó)際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經(jīng)驗(yàn)豐富外,大部分經(jīng)濟(jì)大國(guó)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經(jīng)驗(yàn)有限。 中國(guó)在穩(wěn)定供給現(xiàn)有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同時(shí),需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jì),采取措施彌補(bǔ)自身金融體系建設(shè)的制度短板,選擇切合實(shí)際的供給對(duì)策來(lái)協(xié)調(diào)方式與目標(biāo)之間的關(guān)系。
4.1 構(gòu)建面向未來(lái)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路線圖
進(jìn)入2020 年以來(lái),國(guó)內(nèi)外風(fēng)險(xiǎn)明顯加劇,世界經(jīng)濟(jì)出現(xiàn)萎縮,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下行壓力加大,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長(zhǎng)期向好的基本趨勢(shì)不會(huì)改變。 可以預(yù)料的是,中國(guó)將繼續(xù)堅(jiān)持以改革開(kāi)放為動(dòng)力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總體方向不會(huì)變化。 面對(duì)世界經(jīng)濟(jì)新形勢(shì),中國(guó)為保持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持續(xù)性,可依據(jù)中國(guó)供給能力與意愿的變化,提前規(guī)劃持續(xù)供給的路線圖。

表5 中國(guó)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持續(xù)供給的路線圖
現(xiàn)在到2025 年為中國(guó)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調(diào)整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guó)需加強(qiáng)國(guó)內(nèi)金融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重點(diǎn)消化現(xiàn)有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 在具體實(shí)施方面,中國(guó)需著力推動(dòng)“一帶一路”沿線國(guó)家金融合作機(jī)制落實(shí),擴(kuò)大亞投行等區(qū)域性金融機(jī)構(gòu)類公共產(chǎn)品成員范圍,實(shí)現(xiàn)中非基金等區(qū)域合作基金類公共產(chǎn)品投資規(guī)模,嘗試提出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制度建設(shè)路徑,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對(duì)民生領(lǐng)域的支持。
2025 年至2030 年這5 年時(shí)間為中國(guó)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提升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guó)需完善國(guó)內(nèi)金融體系,重點(diǎn)升級(jí)存量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并研究供給新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 具體包括進(jìn)一步夯實(shí)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規(guī)劃,加強(qiáng)亞投行能力建設(shè),提升人民幣區(qū)域化層次,著眼設(shè)計(jì)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架構(gòu)。
2030 年至2035 年為中國(guó)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穩(wěn)定階段,與2035 年中國(guó)基本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目標(biāo)相匹配。 在這一階段,國(guó)內(nèi)金融體系水平與國(guó)際同步,在重點(diǎn)區(qū)域布局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制度體系形成。 具體包括中國(guó)在全球?qū)用嫔系挠绊懥εc實(shí)力進(jìn)一步提升,建設(shè)區(qū)域合作基金組織,人民幣國(guó)際化深層次推進(jìn),建設(shè)跨區(qū)域外匯儲(chǔ)備庫(kù)取得實(shí)際進(jìn)展。
4.2 圍繞周邊確定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重點(diǎn)區(qū)域
亞太地區(qū)是中國(guó)和平發(fā)展的地緣依托,中國(guó)正在打造周邊命運(yùn)共同體,①趙可金:“打造周邊命運(yùn)共同體:習(xí)近平對(duì)周邊外交的思考”,《世界知識(shí)》,2020 年第 3 期,第 18 頁(y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首先著眼于周邊地區(qū)。 中國(guó)堅(jiān)持將“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作為處理周邊外交關(guān)系的基本方針,鼓勵(lì)周邊地區(qū)和國(guó)家分享中國(guó)的發(fā)展成就,這反映了鮮明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取向。 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能進(jìn)一步加深中國(guó)與東盟、南亞、中亞等地區(qū)和國(guó)家發(fā)展的相互依賴關(guān)系,密切雙方的經(jīng)濟(jì)利益聯(lián)系,從而獲得更高層次的區(qū)域身份認(rèn)同。中國(guó)面向周邊地區(qū)提供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在拓展供給“面”的同時(shí)也要突出重點(diǎn),如把東南亞區(qū)域作為優(yōu)先供給方向。
4.3 構(gòu)建有效連接供給與需求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機(jī)制
中國(guó)作為個(gè)體,供給能力是有限的,在平衡區(qū)域需求和自身優(yōu)勢(shì)的基礎(chǔ)上,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輕重緩急進(jìn)行排序,才能實(shí)現(xiàn)效用最大化。 首先,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中,其效用往往難以用數(shù)據(jù)進(jìn)行衡量,所以不僅要從經(jīng)濟(jì)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角度去考慮,還需要從政治、外交等角度去考慮。其次,針對(duì)各區(qū)域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狀況和政策的特殊性,需要考慮供給區(qū)域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承受能力,包括經(jīng)濟(jì)總量、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融資能力等,根據(jù)各國(guó)的需求意愿測(cè)算需求空間,使供給和需求相匹配。 最后,要考慮區(qū)域現(xiàn)有多個(gè)供給者的平衡問(wèn)題,如在東南亞地區(qū),既要綜合考慮世界銀行、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以及東亞共同外匯儲(chǔ)備基金、亞洲開(kāi)發(fā)銀行等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帶來(lái)的競(jìng)爭(zhēng)性,也要考慮雙方之間的合作和銜接關(guān)系,共同供給金融公共產(chǎn)品服務(wù)區(qū)域發(fā)展。
4.4 完善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體系以應(yīng)對(duì)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帶來(lái)的挑戰(zhàn)
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對(duì)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挑戰(zhàn)是全方位的,為保障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可持續(xù)供給,要加緊建設(sh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經(jīng)濟(jì)、政治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體系。 首先,加強(qiáng)經(jīng)濟(jì)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體系建設(shè)。 中國(guó)應(yīng)盡早完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風(fēng)險(xiǎn)預(yù)警機(jī)制,及時(shí)對(duì)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項(xiàng)目進(jìn)行有效的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并定期發(fā)布評(píng)估及調(diào)查結(jié)果,為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部門提供決策依據(jù)。 其次,加強(qiáng)政治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體系建設(shè)。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部門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全球范圍可能合作國(guó)家的政治風(fēng)險(xiǎn)進(jìn)行有效識(shí)別,評(píng)估并判斷得出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可行性,同時(shí)通過(guò)充分利用多邊國(guó)際組織的投資保障體系和購(gòu)買多邊投資擔(dān)保機(jī)構(gòu)保險(xiǎn)等方式,使政治風(fēng)險(xiǎn)管控方式多樣化,防范中國(guó)主導(dǎo)供給的區(qū)域性金融產(chǎn)品資金支持項(xiàng)目風(fēng)險(xiǎn)。 最后,建立應(yīng)急處置預(yù)案。金融是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安全關(guān)系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安全,遇到戰(zhàn)爭(zhēng)、金融危機(jī)等極端事件的時(shí)候,采取有效的應(yīng)急處置方案并最大限度保護(hù)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利益至關(guān)重要。
五、結(jié) 語(yǔ)
當(dāng)前,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日益成為影響當(dāng)今世界經(jīng)濟(jì)格局變化的主要因素,區(qū)域內(nèi)合作形成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安排要求有相應(yīng)的籌資機(jī)制來(lái)保證落實(shí),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金融公共產(chǎn)品本質(zhì)上主要服務(wù)于美歐等國(guó)家利益,其救助實(shí)力與行動(dòng)能力遠(yuǎn)不能滿足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要求;同時(shí),區(qū)域金融危機(jī)的頻繁爆發(fā)需要新的金融穩(wěn)定機(jī)制。 中國(guó)供給的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滿足所在區(qū)域?qū)?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消費(fèi)需求,體現(xiàn)了負(fù)責(zé)任大國(guó)的擔(dān)當(dāng)。 中國(guó)在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上屬于“后來(lái)者”,現(xiàn)有的供給實(shí)踐表明在戰(zhàn)略決策、制度制定、理論積累及供給技術(shù)等方面存在差距。 更為重要的是,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意味著對(duì)現(xiàn)有國(guó)際金融體系的規(guī)范和調(diào)整,中國(guó)在供應(yīng)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方面的行為增多,美歐等全球金融公共產(chǎn)品傳統(tǒng)供給主體在國(guó)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受到挑戰(zhàn),其不可避免地會(huì)采取反擊措施以限制中國(guó)的發(fā)展空間。
中國(guó)與世界的關(guān)系處于深刻變革之中,“一帶一路”倡議與“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為中國(guó)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提供了發(fā)展方向。 區(qū)域需求和供給難度的衡量、成本與收益的均衡,是中國(guó)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shì)供給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關(guān)鍵。 與區(qū)域內(nèi)國(guó)家和世界大國(guó)構(gòu)建金融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合作或協(xié)作機(jī)制,能夠緩和供給競(jìng)爭(zhēng)、減少戰(zhàn)略試錯(cuò)成本。 未來(lái),中國(guó)需與相關(guān)國(guó)家一起積極探索區(qū)域性國(guó)際金融公共產(chǎn)品的有效供給模式,提升區(qū)域的集體認(rèn)同感,促進(jìn)國(guó)際金融治理體系優(yōu)化升級(jí)。
- 太平洋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BBNJ 國(guó)際協(xié)定下的爭(zhēng)端解決機(jī)制問(wèn)題探析
- 國(guó)家主權(quán)與國(guó)際規(guī)則:美國(guó)對(duì)世界貿(mào)易組織爭(zhēng)端解決機(jī)制的態(tài)度變遷
- 疫情防控的治理效能:國(guó)際表現(xiàn)、中國(guó)鏡鑒與制度補(bǔ)益
- 國(guó)家管轄范圍以外區(qū)域海洋遺傳資源的國(guó)際治理
——?dú)W盟方案及其啟示 - 國(guó)家管轄范圍以外區(qū)域海洋遺傳資源開(kāi)發(fā)的國(guó)際爭(zhēng)議與消解
——兼談“南北對(duì)峙”中的中國(guó)角色 - “印太”視角下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調(diào)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