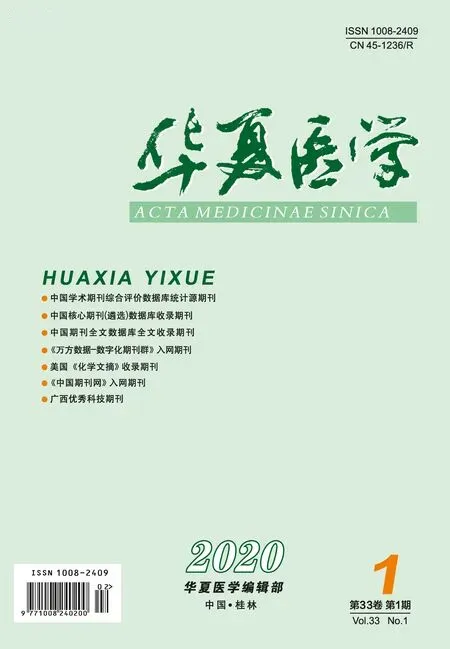肝硬化腹水中醫證型與檢測指標相關性的臨床研究
蔣淑蓮,譚善忠,文 劍
(1.南京市第二醫院中西醫結合科,江蘇 南京 210003;2.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廣西 桂林 541001)
“證”是中醫學特有的概念,是通過對四診所收集的癥狀、體征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診斷性結論。“證”是中醫治療的首要依據,辨證尤為重要。辨證論治就是指以主要癥狀為中心,結合體征及伴隨癥狀、舌苔脈象,識別病因病機,進而指導立法處方。醫家多將肝硬化腹水歸結為中醫之“鼓脹”范疇,認為其病因多為脅痛、黃疸、積聚遷延不愈,或感染血吸蟲,以及酒食不節、情志所傷,氣滯、血瘀、水飲互結,停于腹中而成。病機本虛標實,虛實錯雜[1-2]。近年來中醫藥在治療肝硬化腹水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目前臨床上卻面臨著缺乏較統一的辨證標準,最終降低了中醫治療該病的可操作性,影響了研究結果的推廣。因此,本研究通過分析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證型與檢測指標的相關性,明確檢測指標與“證”的關系,從而為肝硬化腹水建立統一的辨證論治標準提供參考,有利于中醫辨證的標準化和客觀化。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南京市第二醫院中西醫結合科2012年1月至2019年1月明確診斷為肝硬化(依據2000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診斷標準)并經彩超證實存在腹水的患者157例,并運用中醫理論四診合參進行中醫辨證分型分成4組:水濕內阻證30例、濕熱蘊結證40例、陽虛水盛40例、陰虛水停證47例; 157例肝硬化腹水患者構成情況中:肝炎肝硬化最多,占89.2%;自身免疫性肝硬化最少,占1.3%。157例肝硬化腹水的患者中醫分型中陰虛水停型最多,占 30%。在性別構成方面,男89 例,女68例,男女比例為1.31∶1,男女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年齡分布方面,平均年齡49.4歲,各年齡組間的性別構成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該臨床研究經南京市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對各組患者行生化檢查(肝腎功能、凝血4項、肝纖維化等),并應用Child-Pugh分級標準進行分級,隨訪跟蹤患者并發癥數據,再運用SPSS 13.0 軟件分析總結一般資料、肝纖維化指標、淤膽指標、肝功能合成指標、Child-Pugh 分級、并發癥,探討這些患者的中醫證型與客觀檢測指標的內在聯系。
2 結果
2.1 肝硬化腹水患者的中醫證型與肝纖維化指標的關系
肝硬化腹水各證型之間的透明質酸、層粘連蛋白、Ⅳ型膠原均值水平比較,陰虛水停型>陽虛水盛型>濕熱內蘊型>氣滯濕阻型(P<0.05)。詳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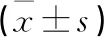
表1 肝硬化腹水不同證型肝纖維化指標的比較
與氣滯濕阻組比較,*P<0.05;與濕熱內蘊組比較,#P<0.05;與陽虛水盛組比較,&P<0.05
2.2 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證型與淤膽指標的關系
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證型中淤膽指標DBIL、TBA、ALP、GGT值比較,陰虛水停型>陽虛水盛型>濕熱內蘊型>氣滯濕阻型,其中氣滯濕阻證型低于其他各組(P<0.05),陰虛水停型高于其他各證型(P<0.05)。詳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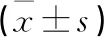
表2 肝硬化腹水不同證型淤膽指標的比較
與氣滯濕阻組比較,*P<0.05;與濕熱內蘊組比較,#P<0.05;與陽虛水盛組比較,&P<0.05
2.3 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證型與肝功能指標的關系
157例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證型中CHE和ALB均值比較,陰虛水停型<陽虛水盛型<濕熱內蘊型<氣滯濕阻型,其中氣滯濕阻證型高于其他各組(P<0.05),陰虛水停型低于其他各證型(P<0.05)。在PT均值上,陰虛水停型>陽虛水盛型>濕熱內蘊型>氣滯濕阻型,其中氣滯濕阻證型低于其他各組(P<0.05),陰虛水停型高于其他各證型(P<0.05)。詳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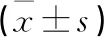
表3 肝硬化腹水不同證型肝功能指標的比較
與氣滯濕阻組比較,*P<0.05;與濕熱內蘊組比較,#P<0.05;與陽虛水盛組比較,&P<0.05
2.4 肝硬化患者中醫證型與child-Pugh分級以及并發癥的關系
157例肝硬化腹水患者中,Child-Pugh 分級 A 級主要分布在氣滯濕阻證、濕熱蘊結證中,高于陽虛水盛組和陰虛水停組(P<0.05);Child-Pugh分級C級主要分布在陽虛水盛、陰虛水停證中,高于氣滯濕阻證、濕熱蘊結證組(P<0.05)。總之,隨著證型由氣滯濕阻向陰虛水停證推移,其Child-Pugh分級C級所占比例逐漸增加。同時,陰虛水停型的消化道出血、肝性腦病發生概率明顯高于其他證型(P<0.05)。詳見表4。

表4 肝硬化腹水不同證型與Child-Pugh分級及并發癥的關系(n,%)
與氣滯濕阻組比較,*P<0.05;與濕熱內蘊組比較,#P<0.05;與陽虛水盛組比較,&P<0.05
3 討論
肝硬化腹水的出現常為肝硬化失代償期最早出現的體征,現代醫學研究認為肝硬化腹水的產生機制主要是肝小葉結構破壞,肝臟硬化,門脈壓力增加,毛細血管靜脈壓升高,促進腹水到組織間隙。肝功能異常致使白蛋白的合成減少,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使內外靜水壓和滲透壓平衡打破,形成腹腔漏出液[3-4]。
肝纖維化指標反映了肝硬化的程度[5],本研究發現,肝纖維化指標透明質酸、層粘連蛋白、Ⅳ型膠原按氣滯濕阻證、濕熱內蘊證、陽虛水盛證、陰虛水停證遞增(P<0.05),提示肝纖維化指標與中醫證型存在相關性。
人體中80%~85%的膽紅素是由衰老的紅細胞破壞生成,以上形成的膽紅素稱為游離膽紅素,在血液中與白蛋白結合形成非結合膽紅素(間接膽紅素IBIL)。非結合膽紅素隨血液進入肝臟,迅速被肝細胞攝取,形成結合膽紅素(直接膽紅素DBIL),直接膽紅素被排入小膽管,并隨膽汁排入腸道。膽汁酸TBA在肝臟中由膽固醇合成,隨膽汁分泌入腸道,因此,DBIL和TBA測定能反映膽道排泄系統是否通暢[5]。本研究發現:DBIL均值和TBA均值按氣滯濕阻證、濕熱內蘊證、陽虛水盛證、陰虛水停證遞增(P<0.05),提示DBIL、TBA 與中醫證型存在相關性。堿性磷酸酶(ALP)和谷氨酰轉肽酶(GGT)是診斷膽管系統疾病時常用的指標[6],正常人血清中的ALP主要來自于骨骼,由成骨細胞產生,經血液到肝臟,從膽管系統排泄。血清中的GGT主要來自肝膽系統,具有較強的特異性,因此,當肝膽系統疾病時此酶增高。本研究發現ALP和GGT 均值按氣滯濕阻證、濕熱內蘊證、陽虛水盛證、陰虛水停證遞增(P<0.05),提示中醫證型與ALP、GGT存在相關性。
凝血酶原時間(PT)能夠反映肝臟合成凝血因子Ⅱ、Ⅴ、Ⅶ、Ⅹ含量的指標,各種原因導致肝細胞受損時,上述凝血因子會不同程度減少,進而PT延長,引起凝血障礙[7]。本研究發現4組證型PT均值按氣滯濕阻證、濕熱內蘊證、陽虛水盛證、陰虛水停證遞增(P<0.05)。白蛋白(ALB)占血清蛋白質的 55%~63%,其與膽堿酯酶CHE都可作為診斷肝功能合成水平的重要依據[7]。從本研究中可以看出白蛋白和CHE均值按氣滯濕阻證、濕熱內蘊證、陽虛水盛證、陰虛水停證遞減(P<0.05)。以上表明,隨著證型向陰虛水停證的演變,肝臟合成功能逐步減退。相應的Child-Pugh分級A級主要分布在氣滯濕阻證、濕熱蘊結證中,而Child-Pugh分級C級主要分布在陽虛水盛、陰虛水停證中,隨著證型由氣滯濕阻向陰虛水停證推移,其Child-Pugh分級C級所占比例逐漸增加。
上消化道出血為陰虛、陽虛證候最常見的并發癥,其中陰虛證候上消化道出血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他證型組。PT時間陰虛組也明顯高于其他組,可見陰虛證候易于出血。上消化道出血是肝硬化患者最常見致命的并發癥,并發上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包括食管、胃底靜脈曲張出血、門脈高壓性胃病以及消化性潰瘍[8-9]。上消化道出血屬于祖國醫學“血證”范疇,當陰虛絡脈疲阻血道,則血不循常道而致出血,可見,陰虛水停證候上消化道出血發生率高,臨床上應注意預防及調護。
本研究結果顯示陰虛水停證肝性腦病發生率較其他證明顯升高。西醫認為肝性腦病的發病基礎是來自腸道的許多毒性代謝產物,未被肝臟解毒和清除,或經側支進入體循環,透過血腦屏障,引起大腦功能紊亂[10]。肝性腦病在祖國醫學中屬于“昏迷”“癲狂”范疇,陰虛證候多與濕熱、癖血相兼,致邪從熱化,蒸液生痰,內蒙心竅,引動肝風,見神昏、譫語、痙厥等厥證[11]。
綜上所述,肝硬化腹水的中醫辨證分型與肝纖維化指標、淤膽指標、肝合成功能指標、并發癥等指標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說明了肝硬化腹水患者中醫辨證分型的量化指標具有可行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