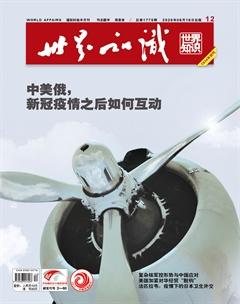新冠疫情怎樣影響世界經濟
魏晉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稱,這場疫情是二戰以來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鳳凰網財經云峰會上表示,“有人說,人類社會進入了至暗時刻,既回不到過去,又看不到未來。”這次新冠疫情是自1918年暴發的“西班牙流感”造成數千萬人死亡以來,全球遭遇的一場“百年未有之大疫情”。
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七大沖擊
全球經濟大減速,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美國今年一季度GDP收縮4.8%,終結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擴張期。中國一季度GDP收縮6.8%,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已陷入“大封鎖”,預計今年全球經濟萎縮3%,其中發達經濟體萎縮6.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萎縮1%,衰退程度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聯合國5月發布的《202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年中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2%,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IMF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特預測,2020年和2021年全球經濟損失累計可達9萬億美元,超過世界第三、第四大經濟體日本和德國經濟總和。

2020年5月1日,美國得克薩斯州開始“重啟”經濟,餐廳、零售店、電影院和商場可按要求恢復運營。圖為經濟“重啟”首日,休斯敦市中心的輕軌站。
金融市場“過山車”式震蕩,風險因素快速聚積。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恐慌情緒也在各國投資者中間不斷擴散。美國股市10天內發生4次熔斷,而美股自1987年熔斷機制建立以來共發生過5次熔斷,上一次還要追溯到1997年。美三大股市市值一度縮水20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總量。道瓊斯指數自2017年以來首次跌破2萬點。歐洲和新興市場股市也經歷多次熔斷,英國、德國、法國等國股指累計下跌一度超過40%,進入技術性熊市。全球市場避險情緒大幅上升,信貸市場信用風險增大。衡量市場恐慌情緒的VIX指數一度升至歷史最高位的82.69,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的峰值。投資者紛紛搶購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避險資產,美元受益于國際資本回流成為階段性避險貨幣。
世界市場“巴爾干化”提速,嚴重沖擊國際貿易。疫情加速全球經濟碎片化。各國為抵御經濟衰退的沖擊紛紛出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使國際貿易雪上加霜。世界貿易組織(WTO)5月發布的《全球貿易晴雨表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全球貨物貿易指數跌至87.6,遠低于100基線值,創歷史最低值。WTO總干事阿澤維多指出,今年全球貿易可能驟降13%至32%,其中北美和亞洲的出口降幅可能最大。從行業看,電子、汽車產品等擁有復雜價值鏈的行業將出現急劇下跌;由于運輸和旅行限制,服務貿易受到疫情的打擊可能最為嚴重。法國國際前景研究與信息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讓認為,今年國際貿易總量下降可能超過1/4,這是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經濟急劇下行的背景下,許多國家優先考慮國內利益對貿易進行限制,這可能最終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盛行。
政經交織,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遭受雙重沖擊。全球主要國家深陷疫情,將從生產資料供應、資本要素供給和消費終端市場多方面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嚴重沖擊。據不完全統計,《財富》雜志1000強企業中94%經歷了供應鏈中斷。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出于地緣競爭和產業安全有意降低對外依賴,政治安全因素對產業政策的影響增大。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等多次呼吁本國制造業回流。日本政府公布的經濟刺激計劃提出,將提供2200億日元資助日企將生產線從中國回遷。
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跌跌不休”。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和閉關、“封國”使大宗商品價格創紀錄下跌。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原油(WTI)結算價一度收于每桶-37.63美元,跌幅超過300%,被稱為“史詩級崩盤”。這是1983年石油期貨在紐約商品交易所交易以來首次跌為負值。世界銀行4月發布的《大宗商品市場展望報告》認為,今年能源類和金屬類大宗商品整體價格將分別下跌40%和13%。國際能源署(IEA)4月發布報告稱,當月全球原油需求同比下降2900萬桶/日,預計全年原油需求同比下降930萬桶/日,創近25年新低。受需求嚴重不足影響,銅、鋁、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跌幅一度超過20%。
“失業潮”襲來,失業總人數可能破億。國際勞工組織(ILO)4月發布報告指出,受工作場所關閉、企業裁員和消費減少等因素影響,疫情將使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時間減少6.7%,涉及1.95億全職員工。全球33億勞動力中,超過80%的人受到全部或部分影響,近40%面臨失業風險,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面臨失業風險最大的行業包括住宿、餐飲服務、制造業、零售業等。美勞工部數據顯示,今年4月美國失業率達14.7%,創二戰以來新高;此前7周,美全國失業人數超過3300萬人。英國4月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增加69%,創歷史最高增幅。IMF預計,美國、歐元區、日本、巴西、南非今年平均失業率將分別高達12.4%、10.4%、3%、14.7%和35.3%。
多國面臨債務困境,可能引發新一輪債務危機。全球債務規模在疫情暴發之前已達歷史新高,近期多國為保經濟實施“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進一步放大全球債務風險。國際金融協會(IIF)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債務總和同GDP總和之比已增至322%。目前,全球為應對疫情財政刺激總額已超過8萬億美元,全球債務總規模突破250萬億美元。公共支出激增升高了主權債務違約風險。阿根廷經濟部長古斯曼公開表示阿已處在“事實違約”狀態,無力償還債務。南非因外匯儲備不足出現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未來一年,新興市場違約風險明顯加劇,有可能導致新一輪債務危機。
經濟危擊的三個深層特點
一是產生機理和復蘇路徑有別于往常。不同于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并非源于經濟系統內部,而是外部因素所致,因此其產生機理和復蘇路徑異于傳統經濟危機。大蕭條的影響范圍主要是資本主義世界,也外溢到部分殖民地國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廣泛,但對部分金融體制穩健或閉塞的國家沖擊不大。此次疫情波及全球,使各國社會生產和消費投資暫時停擺,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受到抑制。在此背景下,單純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通過“直升機撒錢”等方式刺激經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二是引發“逆全球化”大辯論。疫情以幾何倍數跨國傳播,加之美歐醫療物資過度依賴海外供應鏈,因此放大了“逆全球化”思辯。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疫情暴發“表明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重提“歐洲經濟主權論”。蘇黎世大學教授貝茨指出,全球化加劇南北產業分工失衡,兩極化持續擴大,面對疫情,歐美國家連洗手液、口罩、止疼藥、抗生素等基本醫療物資的生產都難以滿足,教訓深刻。疫情是否會逆轉全球化的歷史潮流,成為當前國際社會和媒體熱議的話題。
三是推動“數字化”世界加速形成。在全球抗疫行動中,數字技術顯示出巨大優勢和潛力。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和資源調配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疫情危機凸顯數字工具、服務和解決方案的重要性,也加速全球經濟向數字化轉型。為遏制病毒傳播,各國政府紛紛提供網上政務服務,企業轉向遠程辦公,學校開展線上直播教學,消費者選擇網絡作為主要消費和娛樂平臺,外賣一度成為“必需”而非“選擇”。疫情極大加快了數字經濟市場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