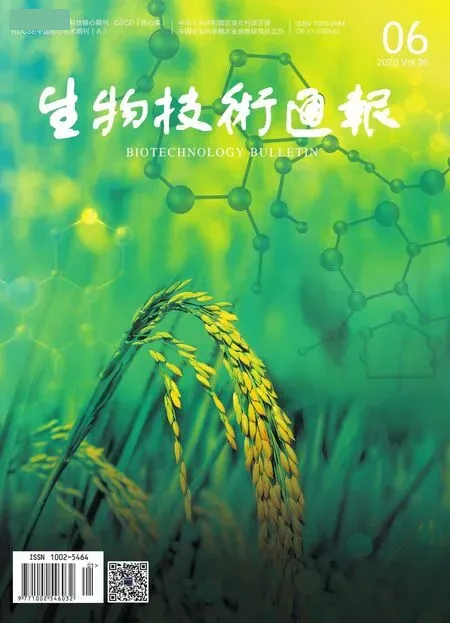華東地區豬丹毒桿菌分離株的生物學特征及其耐藥性分析
龔爭 張俊杰 鐘登科
(1. 安徽科技學院動物科學學院,滁州233100;2. 上海農林職業技術學院,上海 201600)
豬丹毒桿菌又稱紅斑丹毒絲菌(Erysipelothrix rhusiopathiae,ER),是豬丹毒(Swine erysipelas)的病原。豬丹毒是一種急性、熱性人獸共患傳染病,臨診特征主要為急性敗血癥、皮膚疹塊、慢性心內膜炎和關節炎[1]。該病在美國、巴西、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等大部分國家廣泛流行,既危害著全球養豬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威脅著人類健康。
20世紀80-90年代豬丹毒曾給我國養豬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2]。該病得以有效控制20余年,其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多數豬場停止接種豬丹毒疫苗。然而,近年來豬丹毒在我國各地頻頻暴發,豬群出現大面積急性感染死亡,給很多養豬場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在廣西、貴州、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安徽、云南等地均有豬丹毒散發的報道,豬丹毒似乎又有卷土重來的態勢[3-12]。
抗生素在豬丹毒等細菌性疫病的防治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3]。但是由于臨床上不同程度存在濫用抗生素現象,使得近年來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及不同時期分離的豬斑丹毒桿菌的耐藥性存在差異。本研究通過對2017-2018 年華東地區豬場臨床疑似豬丹毒的病/死豬進行細菌分離、分析其生化特性、血清型、小鼠毒力等生物學特征,以及遺傳進化分析、藥物敏感性測定,旨在了解當前該地區豬丹毒桿菌的生物學特性和耐藥情況,為當地豬場有效防控豬丹毒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主要試劑與實驗動物 商品化豬丹毒活疫苗(G4T10 株,血清1a型)、豬丹毒活疫苗(GC42株,血清1a型)分別購自中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廣東永順生物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腦心浸液肉湯培養基(BHI)、綿羊血營養瓊脂培養基、胰蛋白大豆肉湯培養基(TSB)購自英國Oxoid公司,新生牛血清購自浙江天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細菌基因組提取試劑盒、2×TaqPCR Master Mix、DNA膠回收試劑盒購自天根生物有限公司,DNA Marker DL2000、購自上海皓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革蘭氏染色液和微量生化反應管均購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試劑有限公司。18種臨床上常用的抗生素藥敏試紙包括頭孢噻呋(CEF)、頭孢曲松(CRO)、青霉素(PEN)、氨芐西林(AMP)、復方新諾明(、SMZ)、林可霉素(LIN)、克林霉素(CLI)、氟苯尼考(FFC)、四環素(TET)、強力霉素(DOX)、鏈霉素(STR)、慶大霉素(GEN)、卡那霉素(KAN)、紅霉素(ERY)、替米考星(TIL)、恩諾沙星(ENO)、環丙沙星(CIP)、多黏菌素B(PB)購自英國Oxoid公司。4周齡清潔級雌性昆明小鼠購自上海甲干生物有限公司。
1.1.2 病料來源 2017-2018年在上海、江蘇、浙江和江西4個省市的20個非免疫規模化豬場采集的疑似豬丹毒的病/死豬心血、肺和脾等組織,共計266份。并記錄發病豬群來源、發病時間、豬的生長階段及臨床癥狀等流行病學背景資料(表1)。

表1 20株豬丹毒桿菌背景資料
1.2 方法
1.2.1 細菌的分離培養 從病料組織無菌取樣,劃線接種于5%綿羊血營養瓊脂平板,37℃培養24-48 h后,挑取可疑形態的優勢單菌落進行傳代純化,然后挑取純培養的單個典型菌落進行革蘭氏染色鏡檢,觀察細菌的菌落形態和染色特征。
1.2.2 生化鑒定 分離株的生化鑒定參考文獻[8,14]和農業行業標準(豬丹毒診斷技術,NYT566-2002)[15]進行。將分離株的純培養物分別進行靛基質試驗、硫化氫試驗和明膠穿刺試驗、以及山梨醇、葡萄糖和乳糖等微量生化反應,37℃(除明膠置室溫之外)培養24-72 h,觀察、記錄生化鑒定結果。
1.2.3 血清型鑒定 按照文獻[8,10]的方法制備豬丹毒抗原。具體如下:分別將豬丹毒分離株接種在含有10%新生牛血清的BHI培養基中,37℃ 培養24 h,加入終濃度為1%的甲醛溶液,37℃滅活24 h,然后在室溫下靜置24 h,3 000 r/min 離心30 min收集菌體,棄上清,用含0.5%甲醛的生理鹽水溶液洗滌3次,用2 mL蒸餾水重懸菌體后于121℃高壓1 h,待冷卻至室溫后,3 000 r/min離心15 min,收集上清,寄送至英國愛丁堡大學豬病實驗室鑒定分離菌株的血清型。
1.2.4 PCR鑒 定 16S rDNA的 通 用 引 物[16](27F:5'-AGAGTTTGATCCTGGCTCAG-3'和1492R :5'-TACGGCTACCTTGTTACGACTT-3') 和豬丹毒桿菌Kmt1基因特異性引物(ER-F:5'-GTATTACTCATCACAGGCGG-3'和 ER-R:5'-CCCAACAAATCCCGAAGCACC-3'),由上海桑尼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合成。利用細菌基因組提取試劑盒提取分離菌株的細菌基因組DNA,按照王力波等[8]的方法進行PCR鑒定,同時測定分離株的16S rDNA序列。將純化后PCR產物送至上海英駿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進行測序。將這些分離株的16S rDNA序列進行 Blast 比對,然后應用 DNAstar 軟件(Version 7.10,DNASTAR,Inc.,Wisconsin,USA)進行16S rDNA基因序列同源性和遺傳進化分析(Clustal W method,MegAlign)。
1.2.5 小鼠致病性試驗 將20株豬丹毒分離株分別接種于含有10%新生牛血清TSB培養基,置37℃180 r/min振蕩培養12-18 h,3 000 r/min離心30min收集菌體,棄上清,用無菌生理鹽水洗滌菌體3次,經菌落平板計數,調整菌液濃度為1.0×108CFU/mL,取0.2 mL菌液分別于腹部內接種昆明小白鼠,每個分離株接種10只,并設立健康對照組,注射等量的無菌生理鹽水,連續觀察7 d,每天觀察并記錄小鼠發病及死亡情況,解剖死亡小鼠進行細菌的分離、鑒定。
1.2.6 免疫保護實驗 選取具有地區代表性的5株豬丹毒分離株(ZJ2018-1、SH2017-3、SH2017-4、JS2018-3、JX2018-2)進行攻毒保護試驗。將96只4周齡清潔級雌性昆明小鼠隨機分為16組,每組6只,其中1-5組為G4T10活疫苗免疫組,6-10組為GC42 株活疫苗免疫組,11-15組為5株豬丹毒分離株攻毒對照組,16組為健康對照組。受試疫苗的免疫劑量、免疫程序參考文獻[3]和疫苗的使用說明進行。兩種活疫苗免疫組均采取背部皮下多點注射0.1 mL經生理鹽水稀釋的疫苗,免疫劑量為106CFU/0.1 mL,間隔2周后加強免疫;攻毒對照組和健康對照組均以同樣方式注射等量生理鹽水。二免后14 d,活疫苗免疫組和攻毒對照組分別以腹腔注射方式接種致死劑量的豬丹毒桿菌分離株(104CFU/只),健康對照組以同樣方式注射等體積生理鹽水。連續觀察7 d,每天觀察并記錄小鼠死亡情況,計算死亡率,并解剖死亡小鼠進行細菌分離鑒定。
1.2.7 藥敏試驗 根據抗菌機制不同,選取豬場常用的10大類抗生素中臨床上常見的18種抗生素的藥敏試紙,按照常規的紙片法操作[16]對上述20株豬丹毒桿菌進行藥敏試驗,通過測量抑菌圈(mm)大小,參照美國國家臨床實驗室標準委員會(NCCLS)提供的判斷標準[17],分析這些分離菌株的耐藥情況。
2 結果
2.1 細菌的分離培養與染色鏡檢
從采集的266份病料中分離到的20株疑似豬丹毒桿菌的病原菌,分別編號為ER-1-ER-20,分離株在綿羊血營養瓊脂培養基上長成針尖大小、半透明、表面光滑、邊緣整齊、直徑1-2 mm的白色細小菌落,有α溶血現象(圖1-A)。革蘭氏染色鏡檢,可見分離菌均為G+、彎曲或長絲狀桿菌,有的呈短鏈排列,有的呈長絲形(圖1-B)。
2.2 生化特性
生化鑒定結果表明,20株豬丹毒分離株均符合豬丹毒桿菌的生化特征(表2)。

圖1 豬丹毒臨床分離株培養特征及形態特征

表2 豬丹毒分離株的生化特性
2.3 血清型鑒定結果
20株豬丹毒分離株的血清型均為1a型,僅與1a型標準血清發生凝集反應,與其余標準血清均未觀察到凝集反應。
2.4 PCR鑒定與16S rDNA的序列分析
2.4.1 PCR鑒定 應用ER的特異性引物對20株分離株進行PCR擴增,目的片段長度均為1 038 bp。分離株16S rDNA的PCR擴增片段長度均約為1 400 bp,與預期相符(圖2)。
2.4.2 分離株的 16S rDNA序列測定與序列分析 20株豬丹毒分離株的16S rDNA經序列測定與分析,發現這些分離株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為99.7%-100%,其中本研究所得20個分離株中有10株與本地區其他的分離株的同源性為100%;與國外參考株ATCC19414等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為99.4%-100%;與四川ZJ株(2016)、廣西GXBY-1株(2012)、江蘇SY1027株(2010)、黑龍江ZYL株(2010)和湖南YZ12.2 株(2012)等國內分離株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為99.6%-100%。其中,浙江杭州ZJ2018-1株和嘉興 ZJ2018-2株與烏拉圭2007年人源分離株(EU188793)同源性達100.0%;江西上饒JX2018-9株與英國2012年綿羊分離株(T127_5)同源性達99.9%;江蘇連云港JS2018-4株與江蘇豬源分離株(SY1027)同源性也達99.9%。如圖3所示,除GD-GZ外,分離株、參考菌株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均很高,處在同一個進化樹分支上。
2.5 小鼠致病性試驗
20株豬丹毒分離株攻毒組小鼠在接種36 h后,出現精神萎靡,食欲下降,被毛松亂,蜷縮等癥狀,均在72 h內相繼死亡,剖檢可見敗血性出血,脾腫大、充血、肺出血、肝點狀壞死及出血。用含有5%血清綿羊血營養瓊脂從死亡小鼠的心血、脾和肝等組織中分離細菌,分離到的細菌經鏡檢與PCR鑒定均與接種的菌株一致。對照組小鼠未見異常。
2.6 免疫保護實驗
5株豬丹毒分離株攻毒對照組小鼠在攻毒后第2天開始出現明顯臨床癥狀,并相繼死亡。從死亡小鼠的心血、脾和肝中均分離到豬丹毒桿菌。對照組小鼠均正常。G4T10活疫苗和GC42 株活疫苗免疫組小鼠全部存活,沒有出現任何臨床癥狀,保護率為100%(表3)。
2.7 抗菌藥物敏感性與耐藥譜
2.7.1 抗菌藥物敏感性 由表4可知,20株ER均對青霉素、氨芐西林、頭孢噻呋、頭孢曲松、紅霉素、替米考星和氟苯尼考高度敏感。這些抗生素可作為該地區防治豬丹毒的首選藥物。依據NCCLS的判定標準,這些抗生素的耐藥率大小依次為:復方新諾明、慶大霉素、卡那霉素(100%)>鏈霉素(95%)>強力霉素(80%)>四環素(70%)>林可霉素(50%)>克林霉素(40%)>多黏菌素B(20%)>環丙沙星(15%)>恩諾沙星(10%)。總體而言,本研究中ER對氯霉素類、β-內酰胺類藥物、大環內酯類藥物敏感,對氨基糖苷類、磺胺類藥物表現為耐藥,對林可酰胺類、喹諾酮類、多肽類和四環素類抗生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藥。

圖2 豬丹毒桿菌分離株的PCR鑒定結果

圖3 分離株與參考菌株16S rDNA基因序列的系統進化樹
2.7.2 多重耐藥性與耐藥譜 這些分離株進行多重耐藥性分析,結果顯示它們有11種ER的耐藥譜型,耐受4-7種的抗生素的菌株約占80%,其中,19個分離株均能耐4種抗生素,還有1株同時耐9種藥物(表5)。
3 討論
目前已發現豬丹毒桿菌血清型存在1a、1b、2-24及N型26個血清型,其中15種可感染豬[1]。不同血清型的菌株致病力存在差異性,毒力最強是1型,能引起急性敗血型豬丹毒,2型毒力較弱,主要引起疹塊型或關節炎型豬丹毒[2]。近年來,日本、美國等國豬丹毒的發生明顯增多,在臨床上分離豬丹毒桿菌血清型多是1a型和2型[18]。我國豬群中
流行的豬丹毒桿菌血清型主要為1a型、1b型 和2型[2,19]。20 世紀 80 年代,徐克勤等[19]對我國部分豬場豬丹毒桿菌進行血清型鑒定,結果表明血清型主要為1a型和2型。本研究中20株豬丹毒桿菌的血清型經鑒定均為1a型,而且以急性敗血型為主(95%),僅有1株為疹塊型(5%),與以前的調查結果一致[10,20],然而,這與美國、日本等國豬群中主要為關節炎型的報道不一樣[21-22]。小鼠致病性試驗也顯示20株豬丹毒桿菌分離株均能致死小白鼠,與臨床病例一致。由此可見,華東地區豬場流行的豬丹毒桿菌仍為毒力較強的1a型。

表3 5株豬丹毒分離株的小鼠免疫保護試驗結果

表4 20株豬丹毒桿菌分離株對18種藥物的敏感性

表5 20株豬丹毒桿菌分離株的耐藥譜
疫苗接種是預防豬丹毒最有效的方法[1],目前我國豬丹毒商品化疫苗有GC42株和G4T10株弱毒活菌苗、豬瘟-豬丹毒-豬肺疫三聯活疫苗和滅活菌苗等。一些報道顯示部分豬丹毒分離株出現了一些變異[6]。此次在華東地區卷土重來的豬丹毒桿菌的毒力是否也發生變異,我國現有的商品化疫苗對臨床流行毒株是否有免疫保護作用。針對這些問題,本研究選用臨床上常用的豬丹毒活疫苗(G4T10株和GC42株)分別免疫小鼠后,選取具有地區代表性的5株豬丹毒分離株(ZJ2018-1、SH2017-3、SH2017-4、JS2018-3、JX2018-2)進行攻毒保護試驗。結果顯示5株豬丹毒分離株攻毒對照組小鼠均出現明顯臨床癥狀,并相繼全部死亡。G4T10活疫苗和GC42 株活疫苗免疫組小鼠全部存活,沒有出現任何臨床癥狀,保護率均為100%,這與陸萍等[3]的攻毒保護試驗結果相符。此外,spaA基因編碼的SpaA蛋白是豬丹毒桿菌的主要免疫保護性抗原,魏文濤等[10]發現臨床分離的42 株豬丹毒桿菌分離株(1a型)與豬丹毒弱毒苗G4T10株(1a型)和GC42株(1a型)的spaA基因的相似性很高,核苷酸同源性為98.5%-99.9%。由此可見,當前的豬丹毒GC42株和G4T10株弱毒疫苗對我國豬群中流行的1a型豬丹毒桿菌依然有效。豬丹毒在我國局部暴發一個主要原因是疏于防范,沒有進行豬丹毒疫苗免疫。當然,一些免疫抑制性病毒如豬圓環病毒2型、豬藍耳病毒和非洲豬瘟等也會對豬丹毒的流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科學合理接種豬丹毒疫苗,可有效地預防豬丹毒的發生。
豬丹毒桿菌是一種人畜共患的病原菌,可感染豬、羊、魚等多種動物引發丹毒[2],人感染后表現為“類丹毒”[1]。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浙江杭州ZJ2018-1株和嘉興 ZJ2018-2株與烏拉圭2007年人源分離株(EU188793)同源性達100.0%;江西上饒JX2018-9株與英國2012年綿羊分離株(T127_5)同源性達99.9%,而且小鼠致病性試驗表明這些分離菌株均為急性敗血型強毒株。同時,這些豬丹毒桿菌分離菌與四川ZJ株(2016)、廣西GXBY-1株(2012)、江蘇 SY1027株(2010)、黑龍江 ZYL株(2010)和湖南YZ12.2 株(2012)等國內分離株以及與國外參考株ATCC19414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為99.4%-100%,表明華東地區豬丹毒桿菌變異性較小,處在同一個進化樹分支上。可見,我國的致病豬丹毒桿菌存在跨地區傳播的可能。豬丹毒桿菌抵抗能力極強,廣泛存在在環境中,有跨區域傳播的風險[23],因此,要重視豬丹毒病的防治,加強豬場生物安全管理,并且針對豬等主要傳染源采取有效措施。
不同地區、不同時期豬丹毒桿菌分離株對常規藥物的敏感性存在差異。因此,對于來自于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不同菌株均需要進行敏感藥物的篩選顯得極為重要。本研究中ER對β-內酰胺類藥物、氯霉素類和大環內酯類藥物高度敏感,這與以往的國內報道[3,11]相一致,所有菌株均對青霉素、氨芐西林、頭孢噻呋、頭孢曲松、紅霉素、替米考星和氟苯尼考敏感,這7種藥物可作為該地區控制本病的首選藥物。然而由于臨床上長期濫用抗生素,使得我國豬場中豬丹毒桿菌產生了較強的耐藥性且出現了多重耐藥菌株,并且耐藥菌株廣泛傳播[13]。斯特勞《豬病學》第9版中描述的豬丹毒對四環素、林可霉素有很好的療效[1],王力波等[8]發現2012年廣西地區的豬丹毒分離菌株較之20世紀50-80年代的4株參考毒株,對四環素、林可霉素、諾氟沙星敏感性出現顯著差異,敏感程度下降,已對氨基糖苷類、多肽類、磺胺類等藥物表現為耐藥。陸萍等[3]報道了 2012-2013年安徽地區的29株豬丹毒桿菌僅對氨芐西林、頭孢曲松敏感率達100%,而對青霉素、紅霉素和頭孢噻肟的敏感率出現了下降,分別為93%、89.7%、75.9%,且對其他13種藥物也表現不同程度的耐藥性。姚焱彬等[4]進一步分析了2012-2015年安徽地區的42株豬丹毒分離菌株的耐藥性發現,雖對青霉素、氨芐青霉素、頭孢噻肟、頭孢曲松等抗生素的敏感率均高于80%,但100%的菌株可耐受4種及以上的藥物,耐受5種及以上藥物的比例達95.2%,其中耐慶大霉素+卡那霉素+鏈霉素+克林霉素+林可霉素占81%。本研究中ER對對氨基糖苷類、磺胺類藥物表現為耐藥,對林可酰胺類、喹諾酮類、多肽類和四環素類抗生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藥,而且也存在多重耐藥性,耐受4-7種的抗生素的菌株約占80%,還有1株同時耐9種藥物。郭良興等[7]、胡曉芬等[24]、楊佳冰等[11]分別在吉林、湖北和寧夏地區也發現一些臨床分離菌株對β-內酰胺類藥物敏感性下降,甚至對氨芐西林、阿莫西林、頭孢噻肟等不同程度耐藥。由此可見,雖然青霉素類藥物仍是防治豬丹毒的首選藥物,但是臨床分離菌株對青霉素、氨芐西林、頭孢噻呋、頭孢曲松、紅霉素等敏感藥物敏感性下降,顯示具有產生耐藥性的趨勢,對四環素類、林可酰胺類、喹諾酮類的耐藥率較以往的報道明顯增高,這可能是由于抗菌藥物選擇的壓力所導致。因此,適時監控豬丹毒桿菌的耐藥性及其變化趨勢,藥敏試驗篩選藥物,合理、科學、規范用藥,完善獸藥的監管制度,有利于控制和減少耐藥菌株的產生,這對有效防控豬丹毒具有重要的意義[4]。
豬丹毒的臨床癥狀與非洲豬瘟非常類似,均表現為高熱、皮膚發紅及脾臟、淋巴結等內臟器官出血,有時候容易混淆,兩者鑒別與確診還需要借助于實驗室診斷[1]。盡管豬只都會急性死亡,但是豬丹毒的死亡率通常比非洲豬瘟低得多。本研究利用細菌的分離培養及形態學檢查、生化試驗、PCR 鑒定和動物回歸試驗,確定源自上海、江蘇、浙江和江西4個省市豬場臨床疑似豬丹毒病/死豬中的分離菌均為豬丹毒桿菌,而且進一步結合其他細菌和病毒的檢測排除、臨床上敏感抗生素治療與疫苗免疫的實際控制成效,確診這幾起疫情均由豬丹毒桿菌引起。
4 結論
本研究從2017-2018 年華東地區豬場臨床疑似豬丹毒感染的266份病料中分離鑒定出20株豬丹毒桿菌,均為能100%致死小白鼠的 1a 型,具有豬丹毒桿菌的生化特性,16S rDNA 序列與國內外參考菌株、臨床流行株的同源性達99%以上;現有商品化豬丹毒弱毒疫苗對流行的強毒株可提供完全的免疫保護;所有菌株對氨基糖苷類、磺胺類藥物表現為耐藥,對林可酰胺類、四環素類、喹諾酮類和多肽類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多重耐藥,對青霉素、氨芐西林、頭孢噻呋、頭孢曲松、紅霉素、替米考星和氟苯尼考敏感,這7種藥物可作為該地區控制本病的首選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