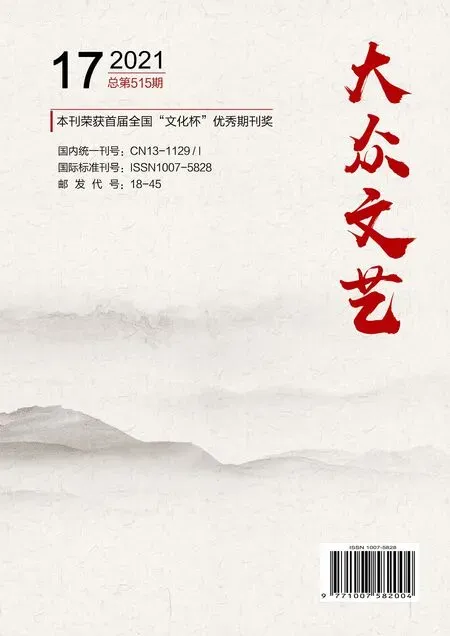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檀香刑》戲劇元素的敘事功能研究
羅嘉敏
(汕頭大學,廣東汕頭 515063)
莫言在論及《檀香刑》的文本創作時曾言:“我是在把它當成‘戲’來寫。”[1]吳士余曾言:“當代作家都表現了對戲劇敘事思維的背離意向。”[2]而莫言的《檀香刑》可謂是對這種背離意向的一種反叛。作家有意識的建構使得《檀香刑》成為“一部戲劇化的小說,或者是一部小說化的戲劇。”[3]本文從《檀香刑》戲劇元素的敘事功能進行探討,挖掘小說戲劇化的敘事意圖及敘事效果。
一、演出元素對人物形象的建構與瓦解
《檀香刑》里除了貓腔班子在升天臺前搬演孫丙故事的演出,幾乎沒有正式的戲臺表演。但是小說主角戲子的身份卻牽引著小說的敘事走向。從孫丙女兒眉娘的口中,可知孫丙從前一直是個眠花宿柳、風流成性的輕浮戲子。由此可知,在塑造孫丙人物形象之初,作者運用戲子的職業特性,初步建構起孫丙吊兒郎當、只求風流快活的形象基調。
在拿到錢丁的賞錢后,孫丙聽從了女兒眉娘的規勸,解散了戲班子,開了一個孫記茶館。但是實際上,孫丙終究難以擺脫戲劇舞臺給他帶來的影響。“現在他把戲臺上的功夫用在了做生意上,吆喝起來,有板有眼,跑起堂來,如舞如蹈。”[4]如此種種,可見戲劇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早已內化在孫丙的人格深處,使得孫丙表演性人格的特質能夠牽引著小說的敘事走向。戲劇的思維方式、表達特性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思維和交流方式。這也為孫丙戲內戲外不分的種種敘事發展埋下了伏筆。
在德國鐵路技師調戲孫丙妻子,孫丙反抗的暴力敘事當中,孫丙在身份認同上逐漸回到了戲子的角色,他意識到自己再次進入到“被看”的場域。因為,當他在大街上打傷了德國鐵路技師的時候,“他恍惚覺得,自己一家仿佛置身于一個舞臺的中央,許多人都在看他們的戲。”[5]而在官府通緝追捕孫丙之時,孫丙受到鄉親的啟發和資助去曹州搬神拳救兵。等到他回來出現在大眾面前之時,孫丙真正有意識地拾起曾經丟棄的戲子身份。他以戲臺出場的方式,進入了戲中人的角色,用貓腔的腔調和說唱的語言敘說了他“岳元帥”的身份從而號召大眾紛紛來學拳,與洋鬼子開戰。長期以來,戲劇價值觀念的濡染和表演性人格的內化,使得孫丙在重大事件當中喚醒了從戲曲唱詞中習得的英雄氣概、擔當意識以及家國情懷。也就是說,人物形象自身通過戲曲的媒介實現了轉變。此時的孫丙不再是小說開頭風流成性、吊兒郎當的民間戲子,而是個從戲里出來的肩負著民族大義的血性男兒。
此外,孫丙這種通過演戲的交流方式具有公共屬性,是一種面向大眾、邀請大眾參與的交流。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孫丙要拒絕朱八的營救,反而要去接受殘酷的刑罰,痛苦至死。因為孫丙最終不再把演戲當作是謀生的工具,而是看作實現民族大義、體現生命價值的方式。孫丙作為貓腔的發揚人,演遍戲文里忠孝大義。這使得他在面對民族恥辱與社會不公上有著一種天然的使命感:要將戲演好,編進貓腔里,傳唱開去,喚醒和教化大眾。這是孫丙執著于接受血腥刑罰的內在目的。
但是這一目的被民眾看客所利用,用以滿足他們看戲的熱情和癡迷。另一方面,也被袁世凱和克羅德所利用,用以滿足震懾民眾的政治需求。刑場“是統治者滿足獸性之樂、劊子手實現藝術化理想、犯人展示生命最后輝煌的劇場。它帶著強烈的表演性質,只不過這種表演不是為了震懾人們,而是為了供人們欣賞。”[6]正因為孫丙戲子的身份和戲劇化的語言表達使得檀香刑本身喚醒的不是民眾對殖民勢力的反抗,而是民眾對戲曲本身的癡迷和熱情。小說直接點破了看客的這一心理:“擁擠到臺前的百姓,根本不是要把孫丙從升天臺上劫走,而是要聽他的歌唱。你看看他們那仰起的腦袋、無意中咧開的嘴巴,正是戲迷的形象。”[7]戲劇元素作為一種敘事手段,在成就孫丙,升華人物形象的同時,也在解構孫丙,消解意義。也就是說,由于看客戲迷的心態,孫丙的人物形象得以在戲劇世界里建構,也得以在其中毀滅。
二、臉譜化元素對人性不同面的揭露
《檀香刑》中莫言對傳統戲曲資源的借鑒和創造還體現在臉譜化的小說人物上,使得小說呈現出傳統戲文程式化的敘事特質。莫言自己曾說:“小說中很多人物實際上是臉譜化的,比如,被殺的孫丙,如果在舞臺應該是一個黑頭,用裘派唱腔。錢丁肯定是個老生了。女主角眉娘是個花旦,由荀派的演員來演的花旦。劊子手趙甲應該是魯迅講過的二花臉,不是小丑,但鼻子上面要抹一塊白的,這樣一個人物。他的兒子趙小甲肯定是個小丑,他就是個三花臉。”[8]可見,作家是有意識地運用戲曲的藝術思維和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莫言如此翻轉小說敘事,寧可觸碰小說人物類型化的敘事大忌,也要將小說人物臉譜化。從《檀香刑》整體的文本形態來看,是一種特殊的敘事策略。因為,這種類型化的人物表現方式,不僅主導著小說人物的建構,還承載著作者集中筆墨反思人性的敘事功能。
首先,把人物形象進行臉譜化的塑造會使得人物特性突出。作者將人物鮮明的性情品格給予特殊的強化并放置在小說敘事中進行展示,使得小說對人性的探討便顯得尤為集中且深刻。類型化的角色表現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性格,而是某一類人的性情品性。例如,錢大人作為智慧、沉穩的老生形象,對社會的現實及檀香刑一事皆有著清醒的認識,但是他卻屢屢助紂為虐。他在抓捕孫丙和準備檀香刑的過程當中顯示出的是他懦弱自私的一面。作為老生的他有理性的思索和大局的考量,但這同時也成為他行動上的牽絆,成為他內心反復糾葛與苦悶的因素,成為他懦弱的原因之一。作者借由錢大人的老生形象集中反思的是人性懦弱自私的一面。趙甲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在莫言看來是“二花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二花臉”。莫言特指他的鼻頭應抹一點白,表明這個角色性格狡詐的一面。在小說當中,他將自己的行刑視為國家統治權力的展現,因而他對這個泯滅人性的職業有著畸形的驕傲和自豪。他渴望表演自己刑術的背后是一種畸形的虛榮心在作祟。趙甲作為狡詐惡毒的“二花臉”展現的是人一旦站在那個失去道德約束的位置上,人性會向惡的一面如何的發展。再如眉娘作為一名熱情潑辣的“花旦”,行為嬌俏且略帶輕浮。她勇于拋棄世俗的倫理與眼光,追逐自己的愛情。但是,卻竭力照顧自己的父親,不斷為父親受刑之事奔波籌劃。在這一層面,眉娘展現出的是人性道德的層面,是人性美好的層面,這寄托了作者對人性應富有溫度的期許。而對于檀香刑的主角孫丙而言,作為正凈的“黑頭”,富有正義感是他的直觀特性。但作者在他英勇行為的背后摻雜了對人性復雜面的思考。孫丙除了想要通過受刑讓父老鄉親覺醒,更要展現他自己的名節和威風,要編進貓腔揚名立傳。因而孫丙實現民族大義的受刑行為,除了正義性和理性的一面,背后還有著非理性的虛榮和逞強斗勝的一面。作者通過“黑頭”的孫丙對人性中的復雜性給予深刻地揭露。
三、戲曲語言對小說敘事的影響
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莫言的《檀香刑》在語言風格上實現了小說和戲曲的滲透和融合。小說的戲曲語言不僅展現著民間的藝術特色、流露出別致的戲韻風味,而且承擔著小說敘事的功能。說唱式的敘事語言作為小說敘事話語中的一種基調,解構著非戲曲化的、日常的小說敘事話語,達到一種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的敘事效果。
《檀香刑》中人物獨唱的片段是小說戲曲語言的直接展現。在“鳳頭部”和“豹尾部”的每一章的開頭都有一段用貓腔的曲調寫成的戲文唱詞。此外,有時候小說人物的對話直接用貓腔的表達方式,如朱八:“叫一聲眉娘莫心焦,先吃幾個羊肉包。”[9]朱八直接用貓腔演唱的方式和眉娘進行對話。除了直接的戲文唱詞,小說中還有大量的“仿說唱體”的語言,其中含有俗語、俚語和諺語,這些語言有時摻雜著方言和戲曲的音律性,形成一種獨特的戲曲語言。如眉娘在“眉娘浪語”里的自我獨白中說道:“爹,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祿山日了貴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綱,兇多吉少,性命難保。”[10]再如,當眉娘見了錢夫人時,小說是這樣描述的:“夫人的腳,尖翹翹,好似兩只新菱角。”[11]
說唱式的敘事語言在營造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敘事效果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尤其是在檀香刑這場大戲之中,孫丙通過檀香刑拭去了戲曲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邊界,使得施刑和受刑的現場成為有民眾參與的人生大戲。不僅如此,雖未直接參與刑罰但早在行刑前就已被迫卷入這場大戲的其他人物也是檀香刑之戲的重要演出角色。“為救爹爹出牢房,孫眉娘冒死闖大堂,哪怕是拿著雞蛋把青石撞,留下個烈女美女天下揚。”[12]“三堂商定虎狼計,要給俺爹上酷刑。”[13]“日落西山天黃昏,虎奔深山鳥奔林。只有本縣無處奔,獨坐大堂心愁悶。”[14]如此種種,這些極具韻律感的說唱式的敘事語言穿插在小說的敘事當中,這使得小說人物說唱的內容自然地組合成一個戲文的文本,說唱的人自然便成為戲中之人。因而作家通過這種極具戲曲風格的敘事語言在小說的文本世界中建構起一個戲文的世界,小說的人物通過這些說唱式的敘事語言自由地穿梭在兩個世界當中。
在《檀香刑》中除了孫丙是有意識地要作為戲中主角完成檀香刑這場人生大戲,其余的小說人物在人物意志上雖說是被動卷入這場大戲之中,但實際上他們卻通過戲曲的語言主動地加入這場大戲當中。這不能不說是作者有意識的敘事安排,流露的是作家關于人生的哲理性思考。為人的過程便是為戲的過程,人生的歷程便是舞臺的演出。少數的人主導著自己的人生,導演著自己的人生大戲。大多數的人在這些少數人導演的戲當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之戲,走過自己的一生。因而,小說戲曲語言的運用是作家以人生為戲,以戲為人生的藝術化體現,同時也為小說整體營造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敘事效果。總而言之,這種有意味的語言形式作為一種敘事策略,不僅在民間場域中承擔意義,在小說美學層面上肩負戲韻的審美品位,更在表意層面上展現出獨特的敘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