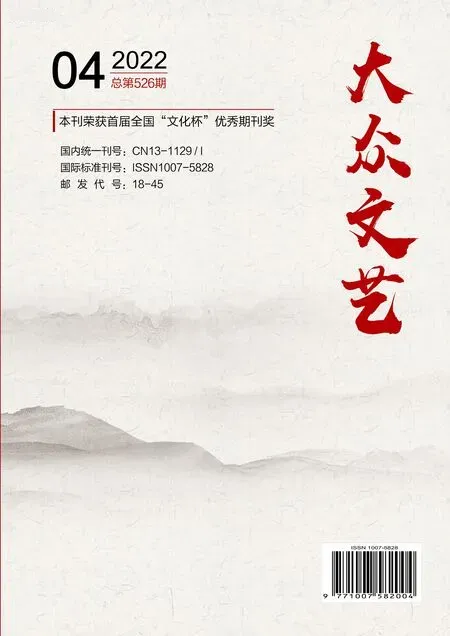絕望的抗爭
——簡析嚴歌苓小說中生存至上的女性價值觀
(北京市東城區職工大學 100061)
旅美華人女作家嚴歌苓的小說,素來以刻畫女性形象見長。她的小說大都關注下層女性的疾苦,女性形象也以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居多,然而恰恰是小人物的世界才最能反映出人世間的疾苦,才能在最真實的生活之中映照出歷史的真善美來。小人物的世界,沒有貴族式的花前月下,笙簫互答;更沒有歷史人物的轟轟烈烈,光彩照人;更多的是掙扎在生存線上的哀嚎,以及對苦悶絕望生活的悲鳴。總的來看,嚴歌苓的小說中,女性的價值觀可以概括為活著,或者是為了更好地活著,這是一種最為基本的生存價值觀。千百年來,中國的普通百姓早已熟悉了這樣的生存價值觀,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余華筆下的徐富貴,都是典型的中國式的底層生存者,他們樸素的愿望也僅僅是活著。與魯迅、余華等人不同,嚴歌苓刻畫出的是女版的阿Q、閏土和徐富貴,只不過她的書寫帶有著強烈的女性觀照意識。但如果按照女權主義的標準來評論嚴歌苓的作品,又不太合適,因為嚴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并沒有強烈地追求男女社會地位的平等,也沒有大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她們只是蜷縮在世間的某一角落,努力地、認真地活著。
一、無知中無我地生存
無知中無我地生存,是嚴歌苓小說中一類女主人公形象的生存狀態。這類女性,缺乏明確的生活目標,也沒有清晰的道德原則,要么在一種本能的驅使下去生活,要么在外力的拉動下被動地生活。這樣的女性形象在嚴歌苓早期以文革為題材的作品中比較常見。
小說《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就刻畫了一位被政治強力改造的女性形象。“陶小童是文藝女兵,她有著自我的意識,喜歡寫日記,特別是喜歡把朦朧的愛情寫到日記里。但是在部隊的生活里,她的日記被偷看了后,她就迎來了一系列生活問題,大家好像把她當成了另類,并且各方領導都來教育她,特別是團支書更是對她開展了嚴肅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謂的教育無非是讓她放棄自我,樹立集體之上的思想,正如約瑟夫·海勒所寫的《二十二條軍規》一樣荒誕,個體的人承受著來自集體冠冕堂皇的壓迫,卻只有順從。出于對政治的無知與妥協,陶小童最終通過艱難地改造成了一個積極的政治模范時,她才發現別人都是把那一套當作政治口號來宣傳而已,事實上大家并沒有那樣去做,而她自己也在完成自我改造的過程中失去了她喜歡的男人徐北方。就這樣,陶小童在單純的無知中,被高壓的政治塑造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符號。
在小說《天浴》中,“文秀作為一個知青剛被下放好牧場的時候,她十分珍愛自己的身子,但是,后來她為了回城過上更好的生活,居然盲信一位供銷員的話,用自己的身子打開回城的門路。小說中的文秀顯然是一個懵懂的姑娘,她并不能認清社會的真實面孔,憑著自己的身體資本進行無謂地犧牲,可悲的是她的犧牲換來的缺是回城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最后在絕望中死去。”小說《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是個十分典型的無知無我的存在。“小點兒沒有什么文化,還曾經在文革中殺過人,出逃之后,她可以為了一頓飯與任何一個男人發生關系,她還為了獲得姑父的照顧與姑父亂倫,她的蒙昧與淫邪可見一斑。”但是從小點兒的生活環境來看,不難理解,她的行為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自己過得更好,哪怕是在道德上承受污點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她能做出那個時代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來。也是為了生存,小點兒放棄了自我,過上了無知無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開始喜歡上那個騎兵連長的時候,她才認識到自己的靈魂早就污穢不堪了,最后作者借一把大火,讓小點兒實現了人生靈魂的救贖。
二、自知中自我地生存
嚴歌苓的小說不僅描寫了一群無知少女墮入無我深淵的悲劇故事,也向讀者展示了另一類堅強不屈的女性形象,她們可以超越世俗的限制,擁有完整的人格,對自己的生活有著明確的目標,并在風云變幻的政治大潮中,始終堅定自我,憑借一種對自我內心良知的把握,堅定地守住了自我的精神高地。她們雖然也面臨著生存的考驗,卻憑借著她們高超的生活智慧,對殘酷的現實生活給予有力的回擊。她們是嚴歌苓筆下最有力量的女性。
小說《第九個寡婦》就塑造了一個王葡萄的形象。“王葡萄敢于忠實自己內心的想法,她不能像蔡琥珀那樣可以犧牲自己的丈夫而救活一個八路軍,而是很率真地選擇了救自己的丈夫,這是對人性最忠誠的敬意,而不是為了所謂的政治壓力,榮譽鼓勵,就改變自己的心志。其次,王葡萄還敢于向不公正的政治行動發起抗議,她在得知公公孫懷清并沒有死的時候,主動救助公公,并把公公藏在紅薯窖里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她遇到各種問題和危險,但是都被她巧妙地躲過去了。就算改革開放之后,她也為躲避計劃生育的婦女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她一根筋地挑戰著所有不合人性的政治運動,所要遵循的就是中國傳統遺傳下的民間潛規則。”再次,王葡萄在性的態度上也是開放的,她的開放并不代表她是淫蕩的,她正視自己的生理需求,在性的伴侶上也有自己的選擇,所以她在那個時代的人看來并不是一個道德完人,相反她是一個道德上有污點的人,這一點是與她所處的時代是格格不入的。評論家張勇認為,“在王葡萄的身上體現了一定的現代性”,她超前的思想觀念影響著她的生活,也給那個缺乏人性美的時代注入了一股暖流。
《小姨多鶴》中朱小環也屬于有自知自我的女性形象。作者在這部作品里講述了一個機智靈活的女性,“朱小環不能生育,張家就買來了多鶴作為兒媳,為張家傳宗接代。朱小環并沒有對此耿耿于懷,相反她放下個人恩怨,幫助丈夫和多鶴度過危險,對丈夫和多鶴生下的孩子也視如己出。”從她的身上顯示出的是女性無限的包容性,朱小環也尊重傳統,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盡管在別人眼中,她的行為似乎有點荒誕和不可思議,但是朱小環的所有行動都是在追求基本的人權,那就是活著,“湊合”活下去。她知道自己生活的不幸,在不幸中她并不是自暴自棄怨天尤人,她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相夫教子,做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姐妹。希望憑借自己的努力讓一家人過上和諧穩定的生活。正是在這個信仰中,朱小環在自知中,不改本色地努力生存著。
《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田蘇菲對待愛情的態度,也說明了田蘇菲是一個有著自己明確愛情觀的人,并有著堅定的信念。這樣的女性活得很美,美在她們能夠遵從自己的內心,在堅守中保持自我。“田蘇菲在文工團里遇到了兩個男人,一個是有錢有勢的首長都漢,一個是政治干事歐陽萸,但是田蘇菲就是喜歡歐陽萸,為了跟歐陽萸走到最后,她經受住了各種考驗。首先是來自父母以及周圍同事的壓力,父母主張要她嫁給都漢,但是被她果斷拒絕了。其次是歐陽萸生病,田蘇菲不離不棄,悉心照顧。甚至是歐陽萸移情別戀,她都能忍受,并始終對歐陽萸投入高度的關懷,直到歐陽萸受到政治批判時,所有的跟隨都離開了他,此時唯獨有田蘇菲始終如一地堅守在他身邊,最后歐陽萸方才大夢初醒,被身邊這個女性的定力所感動,與田蘇菲共度余生。”這么瘋狂的戀愛,正如史詩一般,波瀾壯闊。田蘇菲駕駛的戀愛之舟,由于她目的明確,內心堅定,最后成功到達了目的地。
在這類女性的形象中,無論她們的性格的好壞,品行的優劣。她們的身上都有著生活磨礪的痕跡,之所以她們沒有被生存的不幸所擊垮,是因為她們能在不幸中發現自己的生命本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們一旦發現自己的生命本性的時候,就能始終如一的堅守,最終在平淡艱苦的生活中,打磨出了一個極富生命魅力的個體形象。當她們按照自己的生命本性所生活的時候,盡管會顯得有點荒誕,但是總有一股強大的人性魅力,正是這股人性魅力才讓她們身邊的人受到感召,從而激發人們對她們進行應有的保護,讓她們的所有堅守都有收獲。可以說說這一類的女性形象是嚴歌苓筆下最幸運的人。
三、有知中超我地生存
在有知中超我地生存,指的是有一類女性,她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存追求,但是經過努力卻始終實現不了。最后在無奈中坦然面對,甚至是甘愿承受生活帶來的各種不幸。這類女性形象往往被評論家們稱為具有強烈的包容性和犧牲精神,甚至稱其為地母精神,筆者認為這恰恰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某種程度上來看,這類女性身上的悲劇色彩更為濃厚,她們所秉持的大無畏犧牲精神恰恰就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另一種變形。這樣的犧牲是對人性的自我放棄,在自我麻痹,并不是評論家們常說的“神性”。
小說《扶桑》中的扶桑是一個華人妓女。進入到美國這個異域國家,扶桑沒有生存下去的技能,她唯一的資本就是自己的身體,為了生存下去,她只能被迫用自己的身體去做交易。這是一個底層女性墮落的開始,并沒有人愿意靠賣笑度日。作為一個妓女,扶桑是一個弱勢群體,她不能在任何交易中表現出反感來,在一種無奈的壓迫下,扶桑最終坦然接受了所有施加在她身上的虐待和侮辱。“扶桑習慣了坐在格籠般的窗子里等待生意,習慣了赤裸著身子被人叫賣,在這些活動中,她表現的沒有任何擔憂和恐懼,相反,她總是露出心甘情愿的笑容。甚至當她被一群反華暴徒強暴時,她也不反抗,”“一律地包容,就像礁石包容洶涌的海浪一樣。”人們往往習慣把扶桑神化了,卻沒有在這種神化的光環背后讀出她絕望的內心世界。因此,可能就有人得出結論說,她的笑容是經常掛在臉上的,有人可能會說她是笑對生活。這般言論似乎有點言過了。扶桑的不反抗,是因為她沒有反抗的能力,要她拿什么去反抗呢?放棄了生存嗎?顯然不是這樣。只有默默地容忍才能維持生存,眼看著這種容忍即將成為一種無法改變的現實,扶桑的內心是一種絕望,也正是這種絕望才讓她表現得什么都無所謂了,反正都得忍受,甘心認命地忍受總要好過屈辱地忍受。這樣的生存價值觀是不值得提倡的,魯迅曾經把阿Q寫進小說,批判的就是這種精神鴉片,扶桑的精神勝利甚至連阿Q的精神勝利法都比不上,至少阿Q還知道在精神上反抗,而扶桑已經把自己反抗的意識掐滅了。
在嚴歌苓小說中,這類女性形象還出現在了《陸犯焉識》、《小顧艷情》等多部作品中。《陸犯焉識》中的馮婉喻和《小顧艷情》中的小顧都因為愛,做出了足夠的容忍與犧牲。馮婉喻為了救出陸焉識,委身于戴同志,實際上是一種性交易。小顧為了救楊麥也出賣了自己的身子。這是生活在底層社會中,女性最無助的行為。她們沒有權利,沒有金錢,惟一有的就是自己的身體。但是與金錢權利相比,出賣身體是最讓人感到恥辱的,也是最不明智的。這一點可以從馮婉喻和小顧的悲慘結局中得到印證。
經過對幾部作品中此類女主人公的身份的考察,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她們的行為不代表她們是地母,相反,凸顯的是她們的絕望與無助,這是一群最值得同情的女性。
四、小結
嚴歌苓的小說,反映不同時代的女性生活狀態。在時代大潮的洗滌下,為了生存下去或者是更好地生存下去是嚴歌苓小說中女性的共識。嚴歌苓試圖用一種神性來升華她筆下的女性,即一種無私奉獻的地母精神。但是這終究是一種徒勞,真正的生活讓那些地母都淪為了悲劇的主角。因此,唯有保持真正完整的人性,才是療救女性的有效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