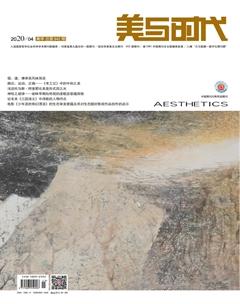淺談弗朗索瓦·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現狀
摘? 要:目前有關弗朗索瓦·于連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從哲學角度討論,這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國智慧、西方哲學以及中西方比較哲學方面;第二是有關研究方法的論述,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也是目前研究于連的重點;第三是從藝術思想方面進行研究,盡管已經有學者將其置于藝術意境、藝術語言與藝術手段、藝術批評三個層面進行討論,但研究不夠深入,成果不足以將于連的藝術思想進行較為完善的表達。因此,從一般性藝術理論角度對于連的藝術與美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是當前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于連;美學;藝術理論;中國古典藝術
Fran?ois Jullien(下文簡稱于連)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由于其治學思路的獨到性為國內外學者所關注。以Jean F. Billeter(下文稱畢來德)為代表的海外漢學家主要針對于連的研究立足點、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進行了分析和探討。而縱觀國內,早在20世紀90年代,第一批專研法語的學者就開始了對于連的探索,以秦海鷹、杜小真等為代表的第一批“觸碰”到于連的學者不僅將于連的作品引入中國,更為后繼學者的研究開辟了道路。而后,以吳興明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延續并發展了于連的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哲學觀點、研究方法、美學觀點方面。雖然目前針對于連思想觀點進行梳理和總結的文章并不多見,但是由于于連治學思路的獨特性,導致了他的思想必定會給國內諸多現行藝術理論研究帶來啟示。因此,總結于連的藝術思想對推動國內藝術理論研究方面有重要意義。
總體上看,過去對于于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從哲學方面入手,基于于連的研究方法來闡述其哲學思想,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智慧、西方哲學以及中西方比較哲學三個方面;第二,關于于連研究方法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也是目前有關于連研究的重點,以畢來德、杜小真等人為代表;第三,對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也尚不成體系,但是吳興明、王逸群、蕭湛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對研究于連美學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關于于連哲學思想的研究
哲學思想是于連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許多著作都充滿著對中國哲學元素的探索,如“勢”“易”“道”等。對于連的哲學思想方面的探討也是圍繞著這幾個方面展開,這其中不僅包含著對中國智慧的闡述,也包含著對西方哲學的思考以及中西方思想的對比。于連在自己的書中也多次提及,作為一個哲學家,最終目的還是為西方哲學尋找出路。由于于連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漢學家而不是哲學家,因此,姑且將漢學也歸納為哲學部分。
關于于連的“中國智慧”[1],中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于其“勢”“理”“道”的研究上。首先,諸多學者認為“勢”在于連的觀點中應是中國思想最有影響力的觀點之一。“勢”在西方人的觀念里指“局勢”,而在中國的思想里則涵蓋了政治、軍事、藝術等諸多方面的演變趨勢。惠天羽闡述了于連關于“勢”的思考[2]。惠天羽提出,“勢”恰如“迂回”,其中蘊涵的是一個迂回思考的過程。孫景強在《從笛卡爾的方法到于連的策略》一文中也提到了這一觀點[3]。惠天羽還認為于連通過“勢”闡述了中國人的民族智慧,比如“勢”在兵法中的運用。在對于“勢”進行闡釋時,諸學者從生活延展到哲學,將哲學意義通俗化。他們在對“勢”進行闡釋時既以歷史實踐為例,又在哲學研究中保持了中國古老的“哲學”習慣。其次,關于“理”,中國自古有“離勢無理,離理無勢”的說法,其中的“理”與西方哲學辯證法中的“真理”“合理”之間形成對應關系。惠天羽提出,雖然于連認可“勢”的自洽性和內在發生性,但他從未拋棄過“理”的指導意義。在這一方面,諸學者以中西語言上的細小矛盾點進行切入,以中國古代經典論著為依據進行討論并不斷提出哲學問題,再進行解答。最后,諸位學者也對“道”進行了討論。中國哲學更多的是強調“智慧”,而不是西方本體論哲學,而這種中國“智慧”就是“道”。孫景強認為“道”是一種自然的內在性流露,保持了“中”的開放姿態,“道”是需要人去追求的,而不是脫離人而客觀存在的[4]。這一方面,學者們在討論哲學的同時更加意識到中國智慧的重要,并在哲學研究中使中國智慧重新恢復了全部意義和具體內容:以中國智慧的特殊概念為出發點探索中國智慧的哲學意義。
于連的治學思路也被置于西方哲學體系中進行討論。一方面,盡管于連并不承認自己是漢學家,但是其研究內容仍然對中國智慧有廣泛的涉獵,這就使得許多學者在研究時將于連與其他漢學家的觀點進行對比。另一方面,由于于連一直接受著西方傳統的哲學體系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的、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因此于連的思想也經常與邏各斯主義進行比較。第一,海德格爾和于連作為同屬現象學領域的哲學家,且都對老莊思想有濃厚的興趣,并對其中的許多名詞有獨特的見解。何光順在《老莊的“庸道”》中以“庸道”為出發點從三個方面對于連和海德格爾進行了比較:首先是二人的交匯點“道”。何光順認為,海德格爾將“事件(Ereignis)”與“庸”互訓,而于連則注意到“常道”即“庸道”。其次,何光順以“庸、恒、常”與“中”為出發點,展開關于“存在”的討論:海德格爾從存在和存在者的區分角度來看,以“庸”“恒”“常”來解釋“道”;而于連則以“中”作為“道”的基本準則。再次,關于“終極”,何光順提出,不論是于連還是海德格爾,抑或是老莊,其根本都是“讓作為此在的人贏獲自由”[5]。蕭盈盈則將海德格爾作為于連思想的“背景”,認為于連正是受到了海德格爾與福柯的影響——后者曾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極深——才以中國這個“他者”作為歐洲哲學“未思”的支持[6]。第二,除海德格爾之外,諸多學者也將于連的哲學思想與貫穿西方哲學史的邏各斯主義進行了討論。韓旭提出,于連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7]。韓旭認為,雖然于連將中國視為“他者”并使中國文化成為西方走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范本,但另一方面,于連關于語言的分析僅僅采用了符號學的意義分析,因此,于連通過意義論比較得出的結論存在不足。吳興明也提及了“道”與邏各斯。他認為,于連注意到了因中西方語言表達差異而造成的“道”與邏各斯主義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吳興明認為,在于連看來,“道”與邏各斯之間是分道揚鑣的[8]148。蕭湛也贊同于連對于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對態度[9]46。蕭湛認為中國遠在西方倡導的理性主義的框架之外,如果試圖用“下定義”的方式來強行拆解,就會導致哲學家為了迎合自身的偏見而貶斥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現象。
在中西方哲學比較方面,諸位學者主要著眼于中西方哲學思想的“相異性(laltérité)”。有學者認為“相異性”源自于中西方語言差異本身,因此這“相異性”在不同的學者眼中有著不同的解釋:“本體論移位”“他者”“間距”。 于連本人不但注重中西方哲學觀點的差別,而且始終試圖使自己擺脫“中國思想”和“西方哲學”對他的雙重影響——在這種條件下,學者們便很容易以于連的理論為基礎比較中西方哲學思想。于奇智專門探討了laltérité一詞的含義,并提出應用“相異性”來譯該詞。不僅如此,于奇智還提出,雖然在二重結構中,他者與自我應當是相異性的關系,但在比較的過程中二者還是應遵循相似性的原則[10]。孫景強將于連注意到的“相異性”總結為“本體論移位”[11]。而蕭盈盈在《當代中西對話的另一種可能》中則進行了關于相異性(laltérité)和間距(lécart)的討論:“于連在哲學框架里討論laltérité時,更多地指向‘他者性;在漢學框架里,則常常意為‘相異性。”[6]而作為“相異性”解釋時,“他者性(laltérité)”能使于連將中西方思維方式自然呈現。而與“他者性”相伴的“間距(lécart)”,則是于連“看待兩種文化的不同特性”并“將之轉化為推動思想前行的動力并在文化間起作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因此,盡管在中文上略有差距,但“相異性”“本體論移位”“他者”“間距”在于連的觀點中都指向laltérité一詞。
總之,諸學者對于于連哲學思想的論述觸及了其哲學思想的核心。他們對于連的哲學思想的論述體現了敏銳的洞察力,并結合于連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其思想的本質內容。不僅如此,諸學者也意識到應將于連的哲學思想轉換為推動中國智慧前行的動力。但是,雖然諸多學者已經注意到于連在研究過程中既保留了古老的思想習慣,又具有了古人所不具有的特點,而且在研究過程中也紛紛提出:我們應該站在怎樣的角度、以怎樣的視野去面對中西方哲學的差異?但他們通常卻只是按照于連的思路進行一些理論層面的比較,而極少結合實際情況充分將于連的思想進行發展。盡管針對這方面的探索尚未正式開始,但現行研究也必然將為后來學者的研究開創道路。
二、關于于連研究方法的研究
關于于連的研究方法的探討,國內學術界已有約二十篇論著,幾乎占據國內研究于連的文章的半數,其主要觀點也較為統一。可以說,研究于連的第一步,就是對于連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于連的研究方法極其獨到,被稱之為是一種“迂回策略”——通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解讀,重新發掘西方哲學的“未思”,進而開拓一個未來哲學的思路。由于于連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使得這方面的論著眾多,就目前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角度:其一是現象學意義論角度;其二是政治學角度;其三是比較學角度。
現象學是于連的主要研究方法,因此將于連的研究工作置于現象學背景中進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吳興明、杜小真等學者從現象學角度出發對于連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總結。隨著二十世紀德國現象學進入法國,法國現象學體現了極強的生命力和創造性,并對“他者”“世界”進行探索。杜小真指出,于連從現象學角度出發并通過與中國這個極端的“他者”的對話,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對自身傳統進行反思的全新角度[12]75。吳興明在杜小真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對于連的“迂回策略”做了詳細的研究,并將之歸納為現象學意義論。不僅如此,吳興明還表示,由于國內的文學理論尚未實現從意識中心論轉向意義論,因此于連的研究方法是一個“罕見的范例”。吳興明認為,正是出于文化意義發展方向的差異,才使得“迂回”作為一種文化發展的視角并進行展開[13]。
關于是否應該從政治學角度出發評價于連的研究方法,是于連研究方法的評價中最富爭議的一個角度。瑞士漢學家畢來德和吳興明以及杜小真等都從這個角度對于連的研究方法進行過探討,并提出于連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個缺陷就是研究背景嚴重脫離了中國的政治制度,這就導致了于連的研究成果也許并不適用于中國現代社會和時代要求。畢來德也許是在政治學角度批判于連最為尖銳的一個人,2006年,這位瑞士漢學家以一本《駁于連》的小冊子對于連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提出了綜合性的批判[14]。第一,畢來德提出,于連的著作都是建立在“中國的相異性”的“神話”之上,并將“中國神話”飾以哲學和漢學擺在西方面前供其思考。第二,畢來德提出,于連否定了歷史、政治意識形態對中國思想的影響。這種立場不僅不能將中西方哲學進行有效的溝通,反而加強了中西雙方彼此的封閉。吳興明站在中國角度,在《如何從后現代視野中打量中國文化?》一文中駁斥于連。第一,吳興明認為于連“迂回”的立足點是一個畸形的政治制度,這種源始哲學傾向與現代社會是嚴重分化的。第二,吳興明認為,盡管于連的指向為中國的后現代理論家們的保守主義思潮提供支撐,但卻并不能適應中國人的時代需求,他在這一方面的觀點與畢萊德可以說如出一轍。第三,吳興明表示,于連對歷史的“未分化的整體論的研究方式”喪失了邏輯根據[8]153。杜小真則對畢來德和吳興明的觀點持反對態度,她認為,政治制度不應成為對于連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重點,學者們應當關注的是于連帶來的啟發[12]81。
從比較學角度對于連的研究方法進行討論也是一個重要方面,主要是通過對中西方的比較對“迂回策略”進行探討。杜小真、吳興明等都曾有過具體的論述。杜小真在《遠去與歸來》中明確提出“一種文化想要對自己進行反思,對自己的傳統進行整理的欲望,首要條件必是與他者的‘異的碰撞。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意法國希臘哲學學者、漢學家于連教授的意見。”[15]這就要求學者們脫離自身思想傳統,并且不能按照自己的傳統去理解、評論它。不僅如此,杜小真在理解“異”時稱贊于連“真正拋棄了比附和平行的比較”并“脫離了幼稚的形而上學和簡單存在論的局限,實際上是追求真正的對‘他者的尊重”[8]150。吳興明在《迂回作為示意》中表示,于連將“迂回”作為一種策略,并不是意味著一種裝腔作勢和故作高深,而是一種“智慧運作”的結果。吳興明認為,于連恰恰是通過這種獨特的策略,使傳統的比較研究喪失了使用的根據。而且不論是“迂回”還是“對視”,于連都不直接將中西方進行思想、文化內容的比較,而是“迂回”到思想的“背后”,實現了觀念中心論到意義論的“漂移”[13]。
總之,關于于連研究方法的探索,我們應當明確的一點是:沒有完美的研究方法。于連的研究方法的確有他自身的優越性。毫無疑問,于連的“迂回”策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給予了中國學者新的思路。第一,于連“迂回”的過程為中西方文化的比較提供了一個范本。中國學者也開始繞道西方,通過現象學尋找中國的“未思”。第二,于連研究的內容固然重要,但是他脫離了“形而上”束縛的跨文化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的啟發才是重中之重。這種思路使中國學者從逐漸西化的道路中跳脫出來并開始思考中國文化自身的價值。第三,畢來德所說的于連的研究脫離中國政治背景自說自話的問題,其實是每一種建立在客觀性基礎上的論證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一種策略。第四,于連孤立地借用中國某些古老的概念,進行自身哲學的闡發其實并無不妥。因此,于連的研究方法飽受爭議是由于意識形態方面諸多學派的差異。這種爭議的多樣性恰恰能使我們面對于連的研究方法時保持較為理智的思考。
三、關于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
藝術思想同樣是于連思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于連對藝術美的見解與中國藝術及中國畫論密不可分,因而在這里將美學從哲學的范疇中移除出來而與藝術一同進行討論。于連對藝術學理論本身的見解也具有極大的研究意義。據現有資料來看,對于連的藝術思想研究做出較為具體論述的國內學者有三位:吳興明、王逸群、蕭湛。他們的研究各具特色,都推動了國內對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藝術意境、藝術語言與藝術手段、藝術批評三個方面。
于連有關藝術意境的觀點被多位學者從美學角度進行了討論,主要集中在對“淡”和“裸體”藝術的探討并結合儒、道兩家思想進行對中國古典美學的思考三個方面。蕭湛提及了“象”與“境”“遠”“味”與“淡”幾個問題,并通過對于連“淡”之美學窺探到了中西美學的根本分歧,并將這種分歧歸納于“淡”[9]43。但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蕭湛以山水畫來進行對“淡”的詮釋是否符合于連本身的藝術思想,這個問題仍有待考慮。劉耘華則在中西比較文化方法論的角度,通過對于連漢學視角的研究認為于連將“淡”視為中國藝術的理想[16]。在“裸體”藝術角度,吳泓渺以于連的作品《本質與裸體》為例,認為于連是“從美學及哲學角度出發,看待西方人體藝術無緣進入中國審美主流的原因”[17]。吳泓渺以于連對中國藝術的看法為基礎,對裸體藝術的價值功能進行了論述,并從中西方藝術創作中有關“形與神”“人文思想與天人合一”的差異方面分析了中國藝術審美排除裸體藝術的原因。不僅如此,吳泓渺還思考了中國藝術重山水而輕人物的原因,通過對于連的研究反觀了自身。吳興明基于于連的作品《大象無形——或論繪畫之非客體》并結合道、儒兩家思想來進行論述。吳興明認為,于連在山水畫角度實現了中西方哲學的概念互換,將山水畫與“理”“道”結合起來。但是在這一方面,諸位學者將研究停留在意識層面,而沒有結合藝術史及藝術作品進行討論。
目前,已經有多位學者結合藝術語言與藝術手段對于連的藝術思想進行討論,重點主要集中在繪畫、詩歌兩個方面。蕭湛通過對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從色彩、明暗、透視法等幾個方面作為中西美學差異的切入點,發現了西方古典繪畫與中國山水畫之間藝術語言與藝術手段的差別。他結合具體技法分析了于連的藝術思想觀點。但蕭湛卻沒有在藝術理論層面涉及到中國畫論的一般性和總體性的思想論述。從詩歌藝術角度對于連進行討論的以蕭盈盈等為代表。蕭盈盈將于連與葛蘭言對于《詩經》的不同解讀進行了比較和探討,并認為于連在去結構主義角度研究《詩經》[18]。蕭盈盈在文章中專門談到于連對于“比”“興”“情”的看法,將“興”與“比”“情”二者進行比較,并突出強調了“興”的作用。她認為,詩歌創作中“興”作為一種藝術語言,創作者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喚起讀者對詩歌的感受。“情”則是在“興”的引發下被轉化成最初的驅動力。
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以下不足。第一,雖然已經有學者意識到于連的藝術思想對詩畫藝術研究產生了影響,但研究尚未滲透到其他藝術領域。中國古代藝術及思想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在很多情況下可以進行跨門類討論。第二,于連結合具體藝術門類的主要目的是引入一個話題,其終點仍然是探討藝術理論,但諸位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將藝術語言與形而上的意識分離開來,不能形成系統的藝術理論。因此,將藝術語言與審美意識結合起來對于連的藝術思想進行探討就顯得十分必要。
就現有文獻來看,從藝術批評角度探討于連藝術思想的論著稍顯單薄,僅有王逸群一人在該角度對于連的藝術思想進行評價。王逸群對于連藝術思想的評價主要集中在“裸體”藝術方面[19]。他從藝術批評的角度將于連和約翰·伯格、蘇珊·桑塔格的觀點進行了對比,認為于連和約翰·伯格同屬觀念化、總體化批評,但于連更加高明而深刻并賦予了裸體繪畫“形而上的尊嚴”,而蘇珊·桑塔格則反對“觀念化批評”而倡導“形式批評”。經過三者的對比,王逸群得出的結論是:藝術批評的問題既不在于“形式”和“內容”,也不在于“觀念化”,而在于批評自身的具體展開方式,而現象學式的描述則是一切闡釋的唯一奠基性工作。但在王逸群的論述中,于連僅僅是作為論據出現,關于于連藝術思想的闡釋篇幅較少也不夠深入。
四、結語
綜上所述,縱觀有關于連的研究可以發現,前輩學者對于于連的哲學觀點、研究方法、藝術思想等各個方面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論述,為此后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奠定了基礎。于連的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藝術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對中國藝術的解讀更是對藝術理論的建構起到了重大作用。以于連藝術理論為基礎,通過將于連藝術思想與中國古代藝術理論結合,采用現象學研究方法對二者進行探討,并將于連的藝術思想歸納為一般性藝術理論不論對于連藝術思想的研究還是對中國藝術理論的研究都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于連.圣人無意——或哲學的他者[M].閆素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惠天羽.“勢”的智慧——讀于連《勢——中國的效力觀》[J].安徽文學,2014(1):70-71.
[3]孫景強.從笛卡爾的方法到于連的策略[J].法國研究,2009(2): 57-67.
[4]孫景強.中西哲學比較中的幾個關鍵問題——俞宣孟與于連的對話[J].世界哲學,2006(3):103-107.
[5]何光順.老莊的“庸道”——兼及西方思想與老莊思想的互訓[J].哲學研究,2014(4):67-76.
[6]蕭盈盈.當代中西對話的另一種可能——從于連的laltérite(他者性和相異性)和lécart(間距)出發[J].中國比較文學,2015(4):196-204.
[7]韓旭.從哈貝馬斯理論角度看弗朗索瓦·于連的意義論研究[J].中外文化與文論,2013(2):221-229.
[8]吳興明.如何從后現代視野打量中國文化——以弗朗索瓦·于連《迂回與進入》為例[J].文藝研究,2013(6):143-154.
[9]蕭湛,葉默玄.論弗朗索瓦·于連對中國美學“淡”之詮釋[J].美育學刊,2017(6):42-49.
[10]于奇智.易、他者與自我——循于連、德勒茲與伽塔利而道[J].哲學研究,2008(3):94-100.
[11]孫景強.精神分析:一項未竟的哲學事業——重啟魯迅與弗洛伊德“對話”的意義[J].中國圖書評論,2011(1):49-54.
[12]杜小真.為什么、如何與他者對話?——由于連思想引起的幾點思考[J].國際漢學,2009(1):73-81.
[13]吳興明.迂回作為示意——簡論于連對中國文化“意義發展方向”的探索[J].文藝理論研究,2007(5):10-18.
[14]畢來德.駁于連[J].郭宏安,譯.國際漢學,2010(1):216-249.
[15]杜小真.遠去與歸來——關于中國和西方互相對話和研究的方法的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52.
[16]劉耘華.漢學視角與中西比較文化方法論的建構——以于連為個案[J].中國比較文學,2014(2):40-53.
[17]吳泓渺,趙鳴.人體審美上的東西方差異——弗朗索瓦·于連《本質或裸體》讀后記[J].長江學術,2012(3):62-71.
[18]蕭盈盈.結構主義和去結構主義——比較葛蘭言和于連對《詩經》的解讀[J].國際漢學,2017(3):79-87.
[19]王逸群.觀念化的藝術批評遮蔽了什么?——對幾種裸體藝術批評話語的反思[J].中外文化與文論,2018(2).
作者簡介:徐博雅,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
實習編輯:甄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