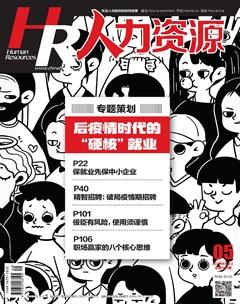君子三畏,行有所止
王立志
關于鬼神之說,人類分成兩派——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當然,筆者無意討論哪種論調是非對錯,而想表達的是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人們要在內心明白有些東西是不能褻瀆的。對此,孔子有“君子三畏”之說。《論語》一書里有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說,作為君子對于這三個東西是需要敬畏的,第一是天命,第二是大人,第三是圣人的話。
“三畏”是一種自律
敬表現的既是一種處世態度、價值追求,也是一種恢宏氣度;畏既是一種害怕、恐懼,也是對自己行為的內心認同、自我遵從與主動限制,是一種“不畏人知畏己知”的自我約束。這作為一種心理活動狀態,折射出一種真實的、普遍的、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感。
畏天命,就是敬畏事物的發展規律。我們通常說的自然規律是指人類以外萬事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自然規律”一詞產生于自然科學,而中華自然哲學對自然的理解寬泛得多,它不僅包括人類面對的自然界,也包括人類自身人性發展變化的過程。以前人們相信命,但至于命是什么,人們也說不清楚,反正事好事壞,都認為是命。人們的思想有一個中心,做什么事前,都是思量一番,覺得舉頭三尺有神明,不可行可惡之事。“畏天命”三個字,包括了一切信仰,信上帝、主宰、佛等。現代人雖然破除了迷信,但依然要有所敬畏,“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規,萬物有法則”,現在,自然、真理、規律就是我們需要敬畏的天命。
畏大人,就是敬畏那些德行很高、地位很高的人,因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這里所說的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職有多高,對父母、長輩、有道德學問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一個人再成功,總有他的父母、上級,讓他敬畏,從而做事各自心中掂量再三,不輕舉妄動。
《菜根譚》里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無所畏懼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時,畏史官于后世。”一個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個人無所怕是不會成功的。只有心存敬畏,才能保持謹慎態度,才能有戒懼意念,也才能在變幻莫測、紛繁復雜的社會里,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雜念所擾,不為個人名利所累,永遠謙遜平和,保持內心的執著和清靜,恪守心靈的從容和淡定。孔子說小人“狎大人”,玩弄別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圣人的話,那會一無所成。
畏圣人,就是古今圣賢留下來的至理名言,我們可以稱之為權威,他們就是我們人生的導向標。尤其是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我國先民,很早就選擇了敬畏自然、追隨人的自然天性。因為沒有神諭和圣徒的指引,我國先民便將身邊品格高尚、知識淵博的人尊為圣賢,于是,歷朝歷代的圣賢就成了引領蕓蕓眾生從凡俗走向崇高的盞盞明燈。
古人云:“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人一旦沒有敬畏之心,往往就會變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無法無天,最終吞下自釀的苦果。在當今社會錯綜復雜的形勢下,面對紛繁世事,面對自己內心,每個人只有心懷敬畏才能有危機感,才能知方圓、守規矩,踏踏實實干事,干干凈凈做人,守住自己內心的道德底線。
概括起來,“君子三畏”既是君子人格的標準,也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就是操守的體現。真正的君子,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三畏”是一種自律,也是一種自愛。人類在馴服了大多數飛禽走獸后,卻一直難以馴服自己。人世間最頑強的“敵人”是自己,最難戰勝的也是自己,而“自律”就是耐得住清苦、扛得住誘惑,頂得住歪理、管得住小節的一種修養。北宋詩人林逋在《省心錄》中說“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具有敬畏意識的“自律”,是不自大、不自傲,不輕視身邊任何一個人的一種表現。沒有“自律”這一道箍,單靠外在壓力或者利益平衡,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地球上,社會這個大家庭是很難長久攏得住的。懂得敬畏者,不以個人情感左右是非曲直,不以一己之私衡量榮辱得失,不以自己的好惡干擾政策法律;不懂得敬畏者,卻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顛覆法律政策,乃至天理良心,只要滿足個人的貪婪,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
人類有了敬畏之心,使我們有別于鴻蒙野獸;個人擁有敬畏之心,才能開始避開禍端,恪守自己的一方天空。“君子三畏”與其他傳統文化的精華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支撐起中華民族的價值信仰體系,并內在地規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判斷與行為走向,幾千年來引導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與文化理想。
無畏導致妄為
有敬畏方無畏,越自律越自由。沒有了敬畏就等于放縱了欲望,做不到自律也就放棄了自由,這兩者之間也是一種辯證統一關系。沒有敬畏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人,一個精神上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只有相信感官上的欲望了,金錢、肉欲、名利因此成了瘋狂追求的載體。當一個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最可怕的事,因為沒有敬畏,他們在別人的眼里,最后在自己的眼里,漸漸地異化為可怕、胡來的代名詞。
在我們的身邊,總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對待親長,毫無尊敬之意;對待弱者,毫無憐憫之心。就像《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從來不信什么是陰司地獄報應” 。正是這種無畏的心態,使得他們膽大妄為,要么暗中作惡,要么明火執仗,最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縱觀漫長的歷史長河,幾乎每一個朝代從盛世走向覆滅,都與為政者敬畏之心的缺失息息相關。一個王朝的開始,總是群英聚會,大氣磅礴。到后來,沒有了敬畏,便沒有了銳氣,皇宮漸漸滋生享樂和荒淫,最終走向腐朽。
當年,唐太宗登上了天子寶座,屹立于人生之巔時,明白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知道人民力量的強大,所以心存敬畏,雖主掌大權,卻不敢任性而為。他時時刻刻感受到人民的壓力,兢兢業業地守住了自己的職責。終于,歷史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一個強大的大唐橫空出世,震撼了世界!后來,他的子孫什么都不怕了,結果黃巢以“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殺氣給出了最終的答案。
其實,每個人在世上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當擁有了天地意識和生命情懷后,就會見識到“一覽眾山小”的景象,感悟到“居高聲自遠”的境界,精神自然得到提升之后,必然會對某些偉大的力量心存敬畏。不然,無畏變成了妄為,將會帶來可怕的災難。心存敬畏,才會居安思危,才會殫精竭慮、發憤圖強,才會保持理智與清醒,讓事業不斷發展、向前。
反觀當下,一些人沒了敬畏意識,不僅對宇宙萬物不再有敬畏感和神圣感,對生命的終極意義不再有追問的好奇和熱情,而且將“活著就好”“活在當下”的活命哲學當作普適性奉行的最高哲學。于是,無視秩序,無視規則,無視禮法,什么感恩、天地、生命、父母、老師、道德、法律,全不在話下,自己才是天下第一,什么事情都會做得出來,什么壞事都敢干。人一旦沒有了敬畏感,一個國家沒有了敬畏感,甚至人類沒有了敬畏感,暴力的魔盒就此打開了。
一個民族想要拋棄叢林原則結束蒙昧時代,就必須有所敬畏,必須遵循統一的道德準則。如果沒有了敬畏之心,被物欲迷惑了雙眼,被權力沖昏了頭腦,滋生蔓延的就是膽大妄為、為所欲為、自我膨脹,最終就會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欲成君子必“三畏”
“君子”一詞,從孔子開始把其概念由對貴族的尊稱轉變為對有德之人的尊稱。而今領導干部依然要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不斷提高道德修養,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正如朱熹所言:“君子之心,常懷敬畏。”
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是幾朝元老,但他對自己要求很嚴,他在家廟的鼎上鑄下銘訓:“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大意是,接受權位的冊命,一命時欠身前傾,二命時彎腰鞠躬,三命時俯身如弓;作為有權者,平日走路也不是大模大樣,而是順著墻根小步快走;謙恭而行,也沒有人敢對我加以侮辱;用這件大鼎煮米,用這件大鼎熬粥,以此來度日糊口。這是一段刻寫在青銅器上的押韻銘文,其中心含義是權位越高,生活的態度和需求也就越發謙恭、儉樸。體現的是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對百姓賦予的權力的敬畏,彰顯的是其“權重愈慎、位高愈謙、志得愈恭”的高度自律。
看正考父的謙恭,又讓人想起司馬遷《史記》中寫的晏子做大官時的一個小故事:晏子身為齊國之相,出行坐在馬車上,屈著身體,盡量使自己不顯得張揚,可是他那位駕車的仆人,坐在前面駕者位置上,洋洋得意、吆三喝四。駕車者的老婆看到這樣的反差,深以為恥,要跟他離婚。這個小故事,在司馬遷寫的晏子傳記中,仿佛一幅小小的漫畫插圖,其用意除了要突出晏子的謙恭之外,也應是提醒讀者不要像駕車者那樣,一旦與權力沾點邊兒,就是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吧。
古人固然還沒有權力為民所授予的觀念,卻也懂得對權力的敬畏。實際上早在西周初年,貴族政治家就有這樣的觀念意識:周人所以獲得政權,是“天命”的眷顧。而所謂的天命,說到底根據的也是民意。因為周人相信,只有好好對待民眾,也就是講究政德,才會得到天的首肯,否則,即便手中有治理天下蒼生的大權,也會被拿走。古本《尚書》說“天聽自我民聽”就是這個意思。這就是古老的“民本”思想。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做到“君子三畏”,應當以一顆清虛、靜篤、坦蕩、正寧之心,以一顆不帶任何雜質和雜念的澄澈、謙卑、純良之心,為天地工作,為眾生操勞,為永恒服役,達到與天地大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對一些東西常懷敬畏之心,這樣才能使我們內心充盈、寧靜,并在行為上有所戒懼和節制,從而與外界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我何畏彼哉?”幫君子能獨立不懼。有殺身成仁,有舍生取義,皆由我做主,而仁義又即我之大生命所在,此又何畏焉?故畏乃對外逐事有之。
精言之,畏之“知”的成分實多于“情”的成分。非如喜怒哀樂,外面渾然一體乃盡在吾情之內也。孔子常兼言“仁智”,仁屬情,智屬知,仁中有智,智中有仁,甚難嚴格分別。亦可謂智亦屬于仁,惟仁乃為其渾然一體。今人多以“悲”與“畏”其屬于情,此亦見仁智之難分耳。
當然,做到“君子三畏”,并不是膽小怕事,而是發自內心的尊敬,對待每一件事都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做人。曾國藩說過:“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人生道路漫長而多彩,猶如在天邊的大海上航行,有時候會風平浪靜,有時候卻會是洶涌澎湃。只要我們內心“三畏”的燈塔不滅,就能壓住驚濤駭浪,沿著自己設定的航線揚帆遠航,駛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