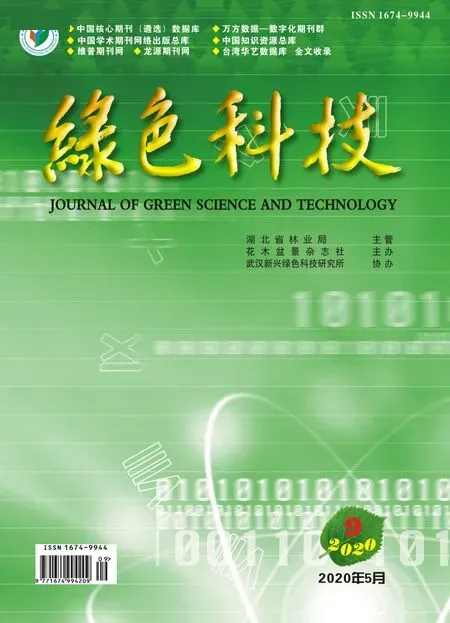黃土高原縣域退耕還林(草)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成六三, 時偉宇
(1.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重慶 402260;2.西南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巖溶環境重慶市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715)
1 引言
針對西部地區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國家從生態安全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以生態優先,同時解決農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全面實施了退耕還林工程。黃土高原的生態植被建設不同于其他區域,戰略意義重大。由于其自然特點和社會經濟條件制約,如何科學、客觀反映黃土高原退耕還林工程綜合效益?是當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黃土高原自身特點的生態、社會和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既是生態學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黃土高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是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提供決策科技支撐的需求。
2 國內外退耕還林(草)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進展
以美國為代表的CRP工程環境受益指數指標體系建立,可為類似于退耕還林(草)工程提供參考。森林的可持續利用效益評價體系,也可參考國家標準指標體系。或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國際評價指標體系,甚至一些社會指標如國民幸福指數、快樂指數等。但在國內對退耕還林(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還沒有形成統一認識,更沒有形成系統性。如防護林生態效益評價指標、黃土高原水保林指標體系、公益林,城市生態系統功能服務指標和生態經濟耦合指標,甚至國家林業局頒布的林業,退耕還林工程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評價指標體系也不是很系統[1~21]。
3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3.1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原則
在國內外綜合效益評價常規原則(系統性、獨立性、可比性、真實性和實用性)基礎上,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退耕還林工程(草)已有明顯的階段性生態效益[21~24],表現為植被覆蓋度的大面積增加和土壤質量逐步改善,但生態功能服務有待于進一步客觀、真實評價。國家林業局2003年發布工程綜合效益監測的具體指標。但是有些指標依然存在缺乏監測條件、獲取難度大等問題,特別在生態效益監測方面,隨著“3S”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成本的降低,能解決工程生態效益關鍵的指標。退耕還林工程植被第一生產力[25,26]是生態系統功能服務的基礎資源和橋梁紐帶,科學、準確的監測工程生物量,是退耕還林工程進一步總結退耕還林工程工作的需要,是進一步優化退耕還林工程建設模式的需要,是科學評價退耕還林工程實施效果的需要,是切實鞏固退耕還林工程建設成果的需要。
(2)退耕還林(草)工程社會效益評價主要體現在轉移農村勞動力、提高農戶的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環境等方面[27,28]。退耕還林工程不反彈主要由于糧食補貼兌現,而糧食補貼確保了農戶耕地損失量,黃土高原環境惡化主要是由人口壓力造成的,科學、綜合區域糧食安全問題,是確保工程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效益的進一步體現。僅僅從農業生產投入和糧食產量提高,以及耕地損失量平衡來影響糧食安全的判斷,是否可行?應考慮選取何種指標能綜合反映糧食安全,體現退耕 還林工程不反彈。
(3)退耕還林(草)工程經濟效益評價以往都以成本—效益進行分析。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經濟增長的方式和增幅,是否反映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包含多方面內容,其在相當程度上是各自獨立的、缺一不可。以往僅把經濟GDP增長2%~5%[29],定為經濟發展。黃土高原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應考慮選取怎樣的指標反映經濟效益。
3.2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依據和方法
退耕還林(草)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系統是一個非常龐大、復雜的 系統,涉及面最廣、政策性最強、規模最大、任務最重、投入最多、群眾參與度最高的生態建設工程。不僅要求工程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為區域社會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既要考慮國家的目標,也要考慮地方和農戶的目標。三者存在一定閾值,才能確保生態、社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
目前退耕還林(草)工程生態、社會和經濟效益評價缺乏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以往綜合效益評價建立森林效益基礎上進行評價,客觀事實,黃土高原植被建設具體問題包括造林成活率低、小老頭、土壤旱化等[30~32],以及受到貧困、人口增長、基礎設施落后等問題,短中期綜合效益評價和長期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要有所不同,能夠運用微觀和宏觀、生態經濟和3S技術相結合的方法,以縣域位單位,設計建立黃土高原退耕還林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對進一步推動工程可持續發展提供研究思路。
4 評價指標體系框架設計和評價方法
4.1 評價指標體系框架設計
參考美國的CRP工程環境受益指數指標體系、國家林業局發布退耕還林工程生態效益、社會經濟監測與評價指標規范、國內防護林、可持續發展指標、公益林綜合效益指標體系以及相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以突出植被生物量生物量基礎資源為核心的生態功能服務紐帶作用;以體現社會 、經濟發展的黃土高原縣域退耕還林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黃土高原縣域退耕還林(草)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及計算方法
4.2 指標體系指標獲取途徑及方法
4.2.1 生態效益
4.2.1.1 固碳制氧效益
表1中,衡量生態效益指標為固碳制氧效益,固碳制氧效益由植被生產力計算。植被生產力能夠比植被覆蓋度更客觀反映工程生態效益資源。可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33~38],采用CASA模型估算縣域植被第一生產力[39]。在其基礎上提取退耕還林工程產生的植被第一生產力的方法,首先,以工程前一年作為植被生產力基底值。其次,估算退耕還林工程實施的每年植被第一生產力。最后,與其基底值做差值,累計植被第一生產力,即為退耕還林工程對縣域產生的植被第一生產力總量。監測指標縣域NDVI植被歸一化指數,運用遙感影像獲取[40~42]。其生態經濟評價采用的方法[43,44]。
4.2.1.2 固土保肥效益
退耕還林(草)工程的目標控制水土流失,反映指標為固土保肥效益,同時,工程使植被蓋度增加,土壤質量恢復方面也有所體現,其指標土壤N、P、K以及有機質含量。評估方法比較成熟[45,46]。
4.2.1.3 涵養水源效益
植被生產力和土壤質量改善促進了水文循環過程,其反映指標為涵養水源,涵養水源功能由土壤非毛隙空隙度、林下徑流量和林木實際蒸散發估算。土壤非毛隙空隙度需要連續監測數據,獲取難度較大,一般都采用水量平衡法[47~49]。
4.2.2 經濟效益
縣域GDP增長率:反映工程對縣域經濟的影響,縣域GDP增長率等于(報告期GDP-基期GDP)/基期GDP×100%。
農林牧產值GDP比例:反映工程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農林牧產值GDP比例等于結構農林牧業產值/GDP×100%。
農戶人均純收入變化率:反映工程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程度。農戶人均純收入變化率等于(報告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0%。
工程補助對農戶收入貢獻率:反映工程對農戶對國家補貼依賴程度。工程補助對農戶收入貢獻率等于人均退耕補助收入(戶)/農村居民人均收入×100%。
期末大小牲畜存欄頭數變化率:反映工程對畜牧業的影響,期末大小牲畜存欄頭數變化率等于(報告期末大小牲畜存欄頭數-基期期末大小牲畜存欄頭數)/基期期末大小牲畜存欄頭數×100%。
恩格爾系數:反映了居民貧困與富裕程度國際上通常用這一系數作為衡量國家貧富狀況和生活水平的尺度。恩格爾系數等于食物消費支出金額/總消費支出金額。
4.2.3 社會效益
外出務工勞動力比率:反映工程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程度,外出務工勞動力比率等于外出務工人數/期末鄉村勞動力人數×100%。
高中升學率:反映工程對農村文化教育影響,高中升學率等于期初在校入學高中生/期末在校畢業初中生×100%。
鄉鎮衛生院人員數比率:反映工程對農村醫療影響,鄉鎮衛生院人員數比率等于鄉鎮醫療人數/期末縣醫療總人數×100%。
鄉村公路里程比率:反映工程對農村交通影響能力,鄉村公路里程比率等于(報告期鄉村公路里程-基期鄉村公路里程)/基期鄉村公路里程×100%。
旱澇災害發生頻率:反映工程對農村生活自然環境改善程度,旱災害發生頻率等于發生旱災害次數/自然災害總數×100%。
耕地壓力指數[50,51]:反映工程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K=Smin/S
(1)
式(1)中K為耕地壓力指數;Smin最小人均耕地面積; 即一定區域范圍內為保障食物需求的最小人均耕地積。S為實際人均耕地面積。
(2)
式(2)中:Smin為最小人均耕地面積(hm2/人);β為食物自給率(%);Gr為人均糧食需求量(kg/人);P為糧食單產(kg/hm2);q為糧食播種面積占播種總面積之比(%)[20];k為復種指數(%),是一年中各個季節的實際播種總面積除以耕地面積求得的。
4.3 退耕還林工程(草)綜合效益評價方法
黃土高原退耕還林(草)工程是一項范圍廣,時間長,集農業技術、林業技術、生態技術和信息技術于一體的綜合性質工程。科學、真實地選定指標和確定評價指標體系非常關鍵。各指標在體系內所起的作用差異性比較大,同時隨著空間、時間的不斷變化,對各自系統的作用和期望會有更高的要求,賦予指標其重要程度分別以不同的權重會有所變化,以客觀、準確地反映工程綜合效益的特點,揭示其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目前在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方法最廣泛是層次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52~55]。也有一些學者嘗試避免因人為因素影響指標權重方法,如模糊數學法、軟系統法和灰色關聯度法[56]。依據指標體系的復雜程度,可靈活運用幾種以上的方法進行評價。
5 討論
退耕還林(草)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既是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 一個非常復雜的技術問題。建立區域統一、科學的退耕還林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同時 采用先進的監測和 評價方法。評價指標的選取應以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能普遍接受的評價指標,特別是生態效益的指標。由于研究區域、對象以及方法不同,決定指標的選擇并不是固定不變的 。因此,評價指標的確定,一定要客觀、真實、準確。本文所設計的工程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還需要進一步改進,有些指標雖然在理論上可以計量,但由于缺少動態、連續的監測數據,因而未能列出該指標體系。需要在實際評估工作中,不斷地對指標體系進行驗證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