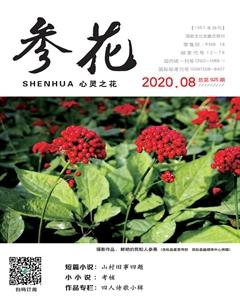青春·夢(mèng)想·悲劇——評(píng)電影《孔雀》
摘要:《孔雀》作為顧長(zhǎng)衛(wèi)的處女作,影片彰顯出平淡自然而又憂傷的風(fēng)格。三段式的敘事結(jié)構(gòu),慣用的長(zhǎng)鏡頭、灰色的敘事色調(diào),塑造了兄弟姊妹三人的青春往事。
關(guān)鍵詞:《孔雀》 敘事結(jié)構(gòu) 長(zhǎng)鏡頭 色彩語言
“中國第一攝影師”顧長(zhǎng)衛(wèi)在幾部成功的攝影作品之后,毅然選擇轉(zhuǎn)型。第一部作品將視線定格在平民身上,無不流露出款款深情與悲劇色彩。《孔雀》講述了20世紀(jì)70年代的河南安陽小鎮(zhèn),一家五口平凡卻又瑣碎的生活。平淡的敘事、長(zhǎng)鏡頭的使用以及色彩語言的運(yùn)用描繪出平凡人悲劇性的人生。藝術(shù)作品是去彌補(bǔ)生活中所缺乏的,但是跟受眾的感受是合拍的。本部作品也恰恰是這樣表現(xiàn)的。
一、三段式結(jié)構(gòu)敘事訴說悲傷
三段式的敘事結(jié)構(gòu),分別闡述了“姐姐”高衛(wèi)紅、“哥哥”高衛(wèi)國、“弟弟”高衛(wèi)強(qiáng)三人各自的一段生命歷程與生活狀態(tài)。炎熱的夏天,無盡的蟬鳴聲,一家五口在走廊安靜地吃飯,兄弟姊妹三人的故事由此拉開帷幕。
三個(gè)人各自有著不同的人生追求與理想。姐姐是一個(gè)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幼兒園與刷杯子的工作并不是衛(wèi)紅心里想要的,她夢(mèng)想成為一名傘兵,想做一名拉手風(fēng)琴的文藝工作者。所以不甘平庸的她積極主動(dòng),不惜代價(jià)追尋夢(mèng)想。她的一生也是不幸的,生活并沒有如她所愿,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祭奠青春和夢(mèng)想。
如果說這個(gè)家是不幸的,那么老大便是不幸的根源。然而他卻是最幸福的。比起姐姐的偏執(zhí)與狂熱,老大則實(shí)際得多。對(duì)于愛情,他用激將法讓母親幫他;對(duì)待友情,寧愿受欺負(fù)也不跟家里人說;對(duì)待親情,雨天給弟弟送傘,卻落下個(gè)“流氓”的罵名。妹妹與弟弟萌生歹意,他也毫不計(jì)較。老大在姊妹三個(gè)中算是過得最順利幸福的一個(gè),娶了一個(gè)鄉(xiāng)下姑娘,能干又持家。沒有遠(yuǎn)大的理想但是踏實(shí)、實(shí)在。
弟弟是家里最聰明的一個(gè),但是也是最沉默的一個(gè)。他跟無數(shù)高中生一樣,有一顆叛逆的心。情竇初開的年紀(jì),對(duì)愛情懵懂,對(duì)生活虛榮。弟弟一個(gè)人坐在電影院大笑的場(chǎng)景,將弟弟悲劇性的人物形象最大化,笑聲則是一種自我的嘲諷。弟弟的歸來并沒有因?yàn)槌杉遥鄙倭诵≈付淖儭_^度的自尊與盲目使得他走向了幻滅的道路。
二、長(zhǎng)鏡頭的形式詮釋悲傷
安德烈·巴贊在他的《攝影攝像的本體論》中,指出攝像和客觀現(xiàn)實(shí)中被攝物的同一性。電影的藝術(shù)特征決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真實(shí)地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但是相比于其他藝術(shù)來說,電影卻能夠更好地反映和揭示現(xiàn)實(shí)。導(dǎo)演多處對(duì)于長(zhǎng)鏡頭的巧妙運(yùn)用,將情感潛移默化地爆發(fā)出來,真實(shí)且富有想象力的細(xì)節(jié)將影片情感上升到頂點(diǎn)。影片中有多處長(zhǎng)鏡頭的部分被視為經(jīng)典。在一家五口打煤球的場(chǎng)景,近3分鐘的長(zhǎng)鏡頭,展現(xiàn)了一家人的居住環(huán)境,走廊上的煤球,晾曬的衣服,五個(gè)人分工明確地打著煤球。天有不測(cè)風(fēng)云,大雨傾盆而下,一家人忙著蓋煤球,衣服也被人收走了。人物的出畫入畫,寓于平淡的敘事中,彰顯出的是平民百姓的無奈。
長(zhǎng)鏡頭以第三者的身份,完全生活化的姿態(tài)記錄著一家人的生活。吃飯、哥哥相親、父親檢查弟弟作業(yè)、姐姐在車間刷瓶子、姐弟倆目睹大白鵝被扼殺、孔雀開屏等場(chǎng)景都以長(zhǎng)鏡頭的方式呈現(xiàn)。影片中沒有撕心裂肺的場(chǎng)景,所有的坎坷與心酸都在平靜的長(zhǎng)鏡頭中,人性在這種狀態(tài)之下顯得愈加有張力和深情,人物內(nèi)心的慘痛,撕裂與掙扎更容易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三、色彩語言表達(dá)悲傷
魯?shù)婪颉ぐ⒍骱D吩凇端囆g(shù)與視知覺》一書中指出,“一切視覺表象都是由色彩和亮度產(chǎn)生的”,即使是物體的形狀也是“眼睛區(qū)分幾個(gè)在亮度和色彩方面都在截然不同的區(qū)域推導(dǎo)出來的”。[1]色彩是表現(xiàn)情感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灰色奠定了整部影片的風(fēng)格,詮釋了生活、命運(yùn)與人性。影片開頭俯拍鏡頭中一家五口生活的小鎮(zhèn)被灰色所籠罩,灰色的房子、灰色的街道,霧氣升騰不禁給人壓抑之感。人物衣著打扮的灰色不僅是這個(gè)時(shí)代特有的色彩,更多的是帶來感情上的表達(dá)。兄弟姊妹三人最終都逃不過命運(yùn)的安排。在對(duì)抗的過程中,也不乏有其他的顏色闖入。姐姐的藍(lán)色降落傘、嫁娶時(shí)穿戴的紅花、哥哥追求愛情時(shí)黃色的向日葵、身穿紅衣的金枝、弟弟的白襯衫等。這些與灰色相反的顏色,在整個(gè)色彩的基調(diào)之下,顯得格格不入,卻也代表著夢(mèng)想與命運(yùn)的反抗。影片結(jié)尾處,俯拍鏡頭再次出現(xiàn)灰色的住宅,首尾呼應(yīng)的效果,這種效果也正是暗示了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的生活。在弟弟的獨(dú)白中,時(shí)光流逝,父母已經(jīng)不再年輕,而我們也即將變老。在回憶青春往事時(shí),那些曾經(jīng)的過往歷歷在目,“爸爸走的那天,很快就是農(nóng)歷立春了。”春天來了,希望就不會(huì)太遠(yuǎn)。
人的一生是充滿希望的,也不是人人都能沖破灰色的圈子如愿以償,灰色的生活卻顯得更加平淡、自然、真實(shí)。影片詮釋了普通人最平淡卻不平凡的生活。不論生活多么艱辛,總要?dú)w于平淡然后再充滿希望地前進(jìn)。
參考文獻(xiàn):
[1][美]魯?shù)婪颉ぐ⒍骱D?藝術(shù)與視知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51.
(作者簡(jiǎn)介:孫茗楊,女,碩士研究生在讀,河北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研究方向:藝術(shù)學(xué)理論)(責(zé)任編輯 劉冬楊)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hù)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