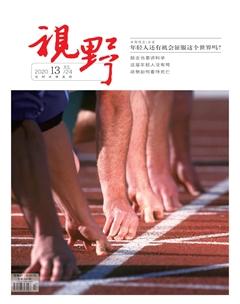致所有正在經歷青年危機的人
朵拉陳

研究生剛畢業的時候,我信心滿滿,手握著榮譽畢業生的獎狀,頭頂常春藤名校的光環。當時的我真以為自己就是“天之驕子”,未來之路四通八達。
不到一個月,現實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我坐在一個四面無窗的小隔間里,拿著行業中最低的起步工資,做著最辛苦的危機干預工作。上班八小時,不是在處理各種疑難雜癥,就是在寫病歷報告,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更倒霉的是,因為伴侶當時還在上學,為了結束多年的異地戀愛,我只能選擇生活在全美物價最高的加州灣區。在這里,我的工資根本不夠用,每天節衣縮食,只為付得起夸張的房租。
美國加州心理咨詢行業規定,咨詢師需要在碩士畢業之后,積累滿3200小時的臨床咨詢時間,通過兩場考試,才能獲得心理咨詢師執照。那個時候的我,常常望著那3200小時出神:天哪,到什么時候我才能完成這么多臨床時數啊!
我的生活怎么會變成這樣?我想到了讀書期間對未來生活的暢想:我穿著漂亮的職業套裝,在窗明幾凈的心理診所里,與來訪者進行靈魂的碰撞……這也差得太遠了吧。
我打開手機,看到朋友圈里發小買房了,臉書上同學辦了一場古堡婚禮,領英上同行又升了職……再看看我自己,便真正感到了“自慚形穢”:不應該啊,我的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初出茅廬的那點傲氣,被生活一點一點地磨平。我感到,自己看起來有很多選擇,但每一條路都像是通往死胡同。
雖然這樣想著,但在現實中,我并沒有走進死胡同。就這樣掙扎著、困惑著、自慚形穢著,3200小時到手了,執照考過了,收入提高了,甚至如今,我真的擁有了一間窗明幾凈的心理診所。
這段路走得很不容易,但和人生的漫漫長路相比,又好像很容易。
現在想來,我十分感激剛畢業的那段經歷。在臨床咨詢工作中,每當遇到年輕的來訪者抓著頭發,痛苦地喃喃自語“不應該啊,我的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的時候,我就知道,對面的人和當年的我一樣,在經歷著青年危機。
青年危機,是從“中年危機”一詞演變過來的。心理學家艾利克斯·福克定義青年危機為“一段關于職業、人際關系和財務狀況的不安全感、懷疑和失望的時期”。一般來講,青年危機出現在人生20歲到35歲。
早在1950年,發展心理學家愛利克·埃里克森就提出了人主要有八個社會心理發展階段,每當人們從一個發展階段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的時候,就會遇到心理危機,產生對人生的不安全感、懷疑和失望等情緒。埃里克森認為,當進入青春期(12歲~18歲)的時候,人開始積極地思考與確認自我的身份特征:我是誰?我想要做什么?我的人生將往哪兒走?對埃里克森而言,這是青春期應當完成的任務。
但是,當今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和20世紀50年代大不相同了。大部分當代心理學家認為,埃里克森的心理發展階段理論有其科學依據,但與現代人的人生周期不相符。隨著現代人壽命的增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權以及多元化社會運動的發展等,對于身份特征的探索不僅僅是青春期的任務,而是和“建立親密關系”這一心理發展階段任務融合在一起,出現于20歲~35歲,形成了青年危機。
心理學家奧利弗·羅賓遜認為,青年危機主要分為五個階段。
階段一,你感到完全被生活中的選擇困住。比如,你不知道該選擇什么樣的職業,不知道該維持什么樣的親密關系,覺得自己正在被生活的壓力推著往前走。
階段二,你感到必須走出這樣的被動局面。你越來越覺得,如果自己能夠“豁出去一次”,也許生活就會有轉機。
階段三,你開始行動了:你辭掉不喜歡的工作,結束了一段雞肋般的感情,現在要干什么呢?你還是不知道。你進入一段“暫停時間”,試圖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標。
階段四,你找到一些大方向,但不大清楚具體應該做什么。你一點一點地摸索著、構建著新的生活,雖然很緩慢,但是,心里感到踏實與滿足。
階段五,你感悟到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你下定決心,開始為這樣的生活而努力。
通過個人經歷以及臨床咨詢,我感受到了心理上的痛苦主要來源于青年危機的第一和第二階段。那是一種身不由己的焦慮感,就像一只在太陽底下被關進玻璃罐的蜜蜂——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卻不知道該怎樣沖破這層厚厚的玻璃,向著那光明飛去。
內心的焦慮感是痛苦的一方面,不被人理解的孤獨感是痛苦的另一方面。正如偉大的埃里克森無法預知21世紀人們的生活方式一樣,父母和其他長輩也很難理解這些“80后”“90后”的年輕人“到底在折騰個什么勁兒”。上一代人的青年時期,生活中可供選擇的少之又少,所以也不必費力糾結。我們這一代人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幸運地獲得了更多的選擇和機遇,困惑與迷茫自然也就變多了。
諷刺的是,心理上最容易被青年危機所影響的人群,恰恰是那些“上進生”:如果你是一個懷揣著堅定理想,對人生有既定規劃,而且對自己嚴格要求的人,很不幸,你最有可能被現實世界中的挫折擊中,感到無比失望與困惑——就像我當年那樣。
那么,可以做些什么來應對青年危機呢?
首先,坦然接受青年危機的到來。別誤會,雖然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我并不認為自己完全走出了青年危機。生活中的挫折、困難與失敗不會停止,我依然常常在冰冷的現實世界面前感到不安全、懷疑和失望。
但是,與剛畢業時不同的是,現在的我明白,這是一段人生必經的心理發展狀態。這樣的意識幫助我“正常化”了內心的不安感受,我不會再因為“怎么還在為我的人生焦慮”而焦慮、自責和慚愧。
其次,適當遠離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創造了一種幻象,讓我們以為別人的生活充滿喜悅的閃光時刻,讓我們篤信人生就是一個“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線性回歸方程式。反觀自己的生活,卻并非如此。相形見絀之下,焦慮、嫉妒、憤怒、自責等復雜情緒就由此產生。
第三,合理管理我們的人生預期。
心理學家奧利弗·羅賓遜指出,青年危機會在我們20歲~35歲反復出現。很有可能,當我們達到青年危機的第四階段——找到一些大方向之后,又因為某些轉折回到第一階段——感到被生活困住。因此,奧利弗·羅賓遜認為,我們必須學會合理管理自己的期望,舍棄一些“我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的偏執念頭。
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放棄自己的夢想,而是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讓自己多一點耐心和靈活度。
或許,我們常常高估了自己在一天、一周內可以完成的事情,卻低估了自己在一年、兩年、十年間可以完成的事情。
與其責備自己“我的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不如告訴自己,我現在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最后,把青年危機當作鍛煉情緒智慧的契機。
在冷冰冰的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調整自己,找到適合的方法來應對壓力:有些人撿起了小時候的興趣愛好,有些人找到了相互理解的社群,有些人愛上了瑜伽等身心結合的活動,有些人通過寫日記更好地了解自己,有些人尋求專業的幫助……這些讓人感到身心舒緩的方法,在心理學上叫作“自我關懷”。
在自我關懷的過程中,我們的情緒智慧也在增長。情緒智慧是一種認識、了解、管理情緒的能力。良好的情緒智慧會讓人意識到,“我不等于情緒”——我現在感到自己很糟糕,并不代表我就真的很糟糕,也不代表我永遠都會感到這么糟糕。
也許,青年危機的出現,正是為了幫助我們做好熱身準備,來面對今后人生路上大大小小的危機。
在剛畢業的那段日子,有一句話給了我很多寬慰與力量:“我們的20歲和30歲適宜栽種,不適宜收獲。我們不能不給夢想的種子生根發芽的時間,就把它們從土壤里挖出來。”
我想把這句話,送給所有正在經歷青年危機的人。
作家是擴展吻的人??
/蔣方舟
我特別喜歡契訶夫的一個短故事,叫作《吻》,講的是一個胖胖丑丑的下級軍官在聚會的時候,于黑暗中被一個女人錯認,吻了一下。這個吻深深地震撼了軍官,他想告訴全天下,但是當他開始向別人講這個故事時,他發現竟然不到一分鐘就講完了,而且如此乏味、如此干癟。
作家是干什么的?簡單地說,就是有能力擴展這個吻的人。吻時的空氣的濕度與氣味,黑暗中濕潤的眼睛隱約閃爍的光,吻落在臉頰上的觸感……一個吻可以像一個世紀那么長,可以像一場世界大戰那樣重要。
這就是交流的美妙,它不僅僅是由話語組成的,而且是由無數個可以回味的細節組成的。那些空氣忽然安靜的瞬間,那些詞不達意的心知肚明,那些遠處恰到好處響起的音樂、升起的月亮、亮起的燈。我愛這些事物勝過詞語本身。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