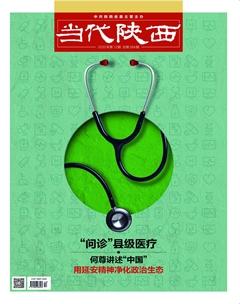消費扶貧不是簡單的“買”和“賣”
盧陽


從“扶著貧困戶走”到“帶著貧困戶跑”,勉縣的消費扶貧逐漸走出了以購代捐、以買代幫的“初級階段”
3月31日,在消費扶貧簽約大會上,勉縣與相關部門、企業,共簽訂消費扶貧意向書21份,消費扶貧協議10份,涉及金額6700余萬元,直接或間接帶動11600余戶貧困戶實現增收。
一個月后的勞動節,“農特產品進古鎮、扶貧達人來助力”大型抖音直播活動在諸葛古鎮火熱進行。十幾個身穿漢服的本土網紅主播,對著鏡頭在線推廣銷售勉縣農產品。
…………
這是勉縣開展消費扶貧的場景。
幫扶單位“以購代捐”的消費扶貧模式雖然改進了送錢送物的“輸血式”扶貧,但勉縣并不滿足于此。近年來,圍繞農產品“誰來賣”“在哪賣”“賣什么”,探索出一條消費拉動產業發展的新路子,解決了分散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難題,為貧困戶精準“造血”。
目光從“幫扶單位”移向市場
陜西巴山秦水生態農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個“主動出擊”的消費扶貧企業。
2014年,巴山秦水成立之初,依托原有1800多畝核桃基地,發展林下養鵝,通過人工干預,實現大鵝反季節產蛋,帶領當地53戶貧困戶戶均增收4萬余元。
之前,山大溝深導致農產品銷售困難,村民只能拿到最近的市場零售。為解決這一難題,巴山秦水總經理陸桂琴開始整合周邊農產品建立銷售平臺。
2019年4月,21家具有SC認證的企業和合作社,與巴山秦水簽訂銷售協議。這21家企業和合作社,都是陸桂琴精心挑選的優質農產品生產加工廠家。
巴山秦水利用自身資源優勢,通過線上平臺,以集中采購、福利采購的形式,將農產品銷售至全國30多個城市。
“市場需要什么,我們就去挖掘什么,尋找什么。”陸桂琴說,也要想辦法讓市場接受優質農產品,實現雙向受益。
2019年5月,陸桂琴到漆樹壩鎮唐家壩村查看茶葉生產加工情況時,發現茶園里長著許多野生蒲公英。她琢磨著,蒲公英做成茶葉會不會有市場。
于是,委托茶園師傅用制茶的方法炮制蒲公英,經質量檢測、食品生產許可認證、包裝,一款野生蒲公英茶葉上架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廣,果然不出她所料,野生蒲公英茶葉深受消費者喜愛,一時間供不應求。
一些村民開始上山挖野生蒲公英賣錢,有的村組織動員農戶種植蒲公英。未曾想到,過去山上無人間津的野菜,現在卻成了致富增收的產業。
阜川鎮駱駝項村距離勉縣縣城大約20公里,地處淺山丘陵地帶。近年來,村集體帶領村民集中精力發展產業,2018年,這個位置偏遠、底子薄弱的村子實現整村脫貧。
“過去,村里都是零散養殖。每逢過節,幫扶單位‘以買代幫,村民養殖的土雞總是一賣而光。”駱駝項村黨支部書記包自舉說,土雞都是跑山雞,肉質鮮美,很受消費者喜歡。
2018年年初,駱駝項村3個養雞大棚和1個冷鏈加工廠建成,當年買進土雞苗8000只。4個月后,經過養殖、宰殺,真空包裝的土雞就能走進消費者的廚房。
冷鏈包裝后的土雞可以保存半個月,這足以讓駱駝項村的土雞銷向全國。包自舉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只雞能帶來10塊錢的利潤,一年可以養兩茬,光養雞這一個項目每年就能帶來16萬元的收入。
好東西不愁賣,駱駝項村的土雞還是雞苗時就已經“名花有主”了。蘇陜對口城市單位以“代養”的方式進行“購銷”;來自幫扶單位中鐵西安鐵路局鐵路社區、各站段職工的預購訂單也紛沓而至。
僅2019年,駱駝項村發展產業項目給村民帶來10余萬元的務工收入。年底,村里又擴建了6個雞棚。
“消費扶貧的動力強勁與否,取決于生產端產品的品質好壞。”在勉縣扶貧辦主任薛永軍看來,消費扶貧要以銷促產,是一個全產業鏈共同發力的行為。
平臺從“賣米不賣油”整合為百貨齊全
4月16日早上八點多,在沔水麗農商貿公司農產品體驗館,泡茶的水還沒燒開,副總經理晏曉可就接到來自北京的訂單。
北京市永定河公園采購部下單訂購了2桶食用油,晏曉可處理好訂單后,立即聯系物流發貨。4天后,勉縣生產加工的菜籽油,將會出現在北京市永定河公園職工食堂的后廚。
“這家用戶不是勉縣消費扶貧簽約單位,像這種線上主動下單的客戶,是開拓市場的關鍵,也是重點維護對象。”晏曉可說,雖然只是2桶菜籽油,我們一點兒也不敢馬虎。
2019年4月,勉縣供銷社牽頭,整合17家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的合作社和企業,組建沔水麗農商貿公司,主要承擔農產品線上、線下流通,眼下,17家合作社和企業已增加至22家。
這22家合作社和企業,與沔水麗農簽訂銷售協議,公司指導他們申請食品生產許可認證、質量檢測,統一推介銷售產品。從無認證、無商標、無包裝的“三無”農產品,搖身一變成為走進商超的正規商品。
一些企業和合作社只懂生產,農產品只能在自己熟識的圈子內銷售,導致“好東西賣不出去”“好東西賣不出好價錢”。沔水麗農讓“養在深閨人未識”的農產品逐漸走進更多人的生活,也給消費者“一站式”購買提供便利。
“‘米廠不管油廠的事,讓消費者在選購生活用品時常常面臨‘賣米不賣油的困境。”勉縣供銷社主任向利說,商貿公司整合縣域農副產品資源,破解了銷售各自為陣、質量標準不統一的難題,架起農產品對接市場的“橋梁”。
晏曉可處理完公司事務,匆匆前往堯蕈生物科技開發有限公司食用菌養植基地。過幾天,有訂單要從這里出貨,此次前去,就是要抽檢木耳質量。
堯蕈生產車間,幾名女工正在從堆滿干木耳的案頭上分揀出殘次菌朵。總經理毛俊平說,干木耳由機器分篩后,再經兩次人工分揀,才能進行包裝。
堯蕈公司地處漾家河以南,光照和濕度正適宜食用菌生長。2015年,毛俊平在這里建起食用菌養植基地。起初,他主要以鮮貨銷售為主,初級農產品銷售輻射范圍有限,利潤薄。
2019年年初,毛俊平開始修建加工車間,購買烘干設備,并注冊商標。年底,與沔水麗農簽下銷售協議,經過加工包裝的干香菇、干木耳開始流通市場,不足半年,銷售額增長了30多萬元。
“有了沔水麗農助力銷售,我們有更多的精力專注生產。”毛俊平說,實現雙贏,就是要找到雙方利益連接點,企業有可銷售的渠道,消費者有可保證品質的產品。
扶貧方式從“扶著走”變為“帶著跑”
順著駱駝項村繼續向西南方向前進,山路崎嶇蜿蜒,漆樹壩鎮唐家壩村就坐落在19公里外的大山深處。
唐家壩村地處偏遠、四面環山,全村一半以上人口在外務工。2018年,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整合村上現有資源,新建一座1000平方米養牛場,與張紅永種養殖專業合作社共同發展養牛產業。
張紅永有豐富的養牛經驗,為提高牛肉品質,他從甘肅、遼寧引進新品種肉牛,規模從20頭肉牛擴充到現在的100余頭。
村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放牛都是行家,可是買牛犢成本較高。他便想到一個好法子:讓村民領養合作社的牛回去養。
村民從牛場把500斤左右的牛領養回去,養到1000余斤再送回牛場,合作社按照重量差10元每斤付給村民勞務費用。
陳啟貴今年71歲,是唐家壩村一組貧困戶。2019年6月,他與合作社簽訂領養協議,從牛場領養一頭牛。
兩個月后,因需照顧生病的老伴,陳啟貴將牛送回牛場,一過稱,牛竟長了100斤。當天,老陳就從合作社領到1000元勞務費。
“草料加工、防疫、看病都由合作社免費提供,我們只管按照培訓的方法養牛就行。”陳啟貴說。今年3月,老伴的病好了些,他又從牛場領養了一頭牛。
今年,唐家壩村與西鄉牛肉干加工企業簽訂了長期供貨協議,牛肉銷售有了著落,村民持續增收也得到了保障。
牛肉有了穩定銷售渠道,讓越來越多的貧困戶看到了市場,也從深層次激發了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張紅永說,“村里的老漢聽說養牛能掙錢,都爭相來合作社咨詢。目前,合作社有16頭牛被村民領養。”
阜川鎮小河廟村是勉縣茶葉種植主產區,全村325戶1014人,人均茶園10畝以上,茶葉種植加工是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
魯瓊是小河廟村村委會主任,也是勉縣小河廟云霧香芽茶葉發展專業合作社負責人。依靠合作社3680畝茶基地,她以多種帶貧模式激發群眾發展動力。
春天來臨,寂靜了一個冬天的茶山被人們喚醒,每年3月中旬到6月下旬,是鮮葉采摘、制茶的時節,也是需要人工勞動力最多的時期。
在今年鮮葉采摘旺季,合作社雇傭的采茶女工一度達到116人,其中貧困戶72人,她們大多來自勉縣、寧強縣。
“只要人勤手快,每天收入100元不成問題。去年,合作社付給采茶工人工資達到70余萬元。”魯瓊說,
小河廟村全村有13000多畝茶園,合作社采取訂單收購鮮葉的方式,來解決困擾村民已久的技術難、銷售難問題。一般衣戶按照市場價格收購,貧困戶按照高于市場價20%的價格收購。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合作社從茶園管理、采摘、加工、銷售各個環節,對村民進行免費技術培訓。”魯瓊說,給農戶提供就業創業機會和技術培訓,才能讓貧困戶走上穩定脫貧、增收致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