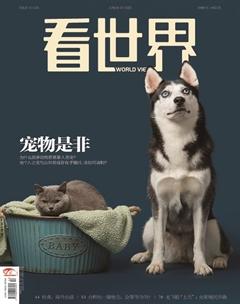社會(huì)性昆蟲如何面對(duì)死亡?
“社會(huì),社會(huì)”一度是個(gè)流行甚廣的社交媒體“表情”符號(hào),被用來(lái)即時(shí)表達(dá)對(duì)地位甚高、處事圓熟者的“崇敬”。這個(gè)詞在東北地區(qū)相當(dāng)常見(jiàn),大概也是伴隨著大量東北籍短視頻主播的走紅而變得常用。人是社會(huì)性的動(dòng)物,“社會(huì)”一詞也仿佛成了人類的專屬。
其實(shí),在生態(tài)學(xué)意義上,人類只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生物學(xué)“真社會(huì)性”的兩個(gè)條件:一是世代重疊,即親代和子代住在一起;二是一個(gè)社會(huì)單元中的個(gè)體共同照顧后代。“真社會(huì)性”的第三個(gè)條件生殖分工,在人類社會(huì)是不存在的;而在社會(huì)性昆蟲中,蟻后、蜂王等少數(shù)個(gè)體繁衍后代,其他個(gè)體并不繁殖。
所以,真的“社會(huì),社會(huì)”表情,應(yīng)該發(fā)給這些社會(huì)性昆蟲。瘟疫造成人類的大規(guī)模死亡,這令人聯(lián)想,如果是傳染性疾病發(fā)生在社會(huì)性昆蟲之間,它們又會(huì)如何處理同伴的死亡?
社會(huì)性昆蟲處理同伴尸體有四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躲避,這種方式很原始,非社會(huì)性昆蟲也常這么做。像紅火蟻的巢里大規(guī)模感染病菌,它們就會(huì)整體搬遷,不去碰那些尸體;土棲白蟻碰到被殺蟲劑殺死的大量同伴出現(xiàn)在通道時(shí),它們也會(huì)封鎖通道,避免以后再次使用。

某種螞蟻會(huì)在幼蟲患病后,治愈能治愈的,殺死治不好的。
第二種方式是,將尸體搬運(yùn)走,使之遠(yuǎn)離本族群中個(gè)體活躍的區(qū)域。在死亡個(gè)體不多的情況下,一只螞蟻就可以搬動(dòng)一具尸體,投入的勞動(dòng)力成本很低,但“搬運(yùn)工”也有被尸體攜帶的病菌感染的風(fēng)險(xiǎn)。它們會(huì)經(jīng)常清潔身體。還有一些特殊種類的螞蟻,會(huì)在臨死前主動(dòng)離開(kāi)巢穴;某種螞蟻會(huì)在幼蟲患病后,治愈能治愈的,殺死治不好的—有壯士斷腕的理性色彩。
第三種方式是食用。白蟻就采取這種方式。它們的食物主要是富含碳元素卻缺乏氮元素的纖維素,同伴的尸體卻飽含氮素。如果尸體處在尚可食用的階段,白蟻們就會(huì)選擇吃掉尸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方式在其他社會(huì)性昆蟲中不太常見(jiàn)。只有在大饑荒這種極端情況下,才會(huì)同類相食。一些螞蟻會(huì)先吃掉卵和幼蟲,然后吃掉不育的工蟻,讓生殖蟻堅(jiān)持到情況好轉(zhuǎn)的那一天。
第四種方式是掩埋。當(dāng)尸體已經(jīng)腐敗嚴(yán)重、不可食用時(shí),白蟻就會(huì)利用由唾液混合的泥土及它們的排泄物,掩埋尸體。唾液中的抗菌成分,可以有效抑制微生物的生長(zhǎng)。蜜蜂也會(huì)掩埋尸體,不過(guò)尸體不是同伴的,而是蜂巢的入侵者的。像老鼠這種無(wú)法搬運(yùn)的尸體,蜜蜂會(huì)用蜂膠和其他材料覆蓋。
群體規(guī)模也會(huì)影響社會(huì)性昆蟲的做法。在實(shí)驗(yàn)室條件下,紅火蟻發(fā)現(xiàn)傳染源,如果這時(shí)巢中個(gè)體數(shù)量較多,它們就會(huì)快速移走傳染源;如果個(gè)體數(shù)量較少,它們就先把卵和幼蟲搬遷到安全地點(diǎn),然后清理傳染源,清理完畢再把卵和幼蟲搬回來(lái)。
人類社會(huì)面對(duì)死亡的做法也很類似:躲避,拋棄,掩埋,在遙遠(yuǎn)的過(guò)去和一些極端時(shí)期,取食尸體也是有的。當(dāng)然,人類也在物理操作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了復(fù)雜的斂葬和祭奠儀式,以此向生者闡釋生存的意義和可期許的未來(l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