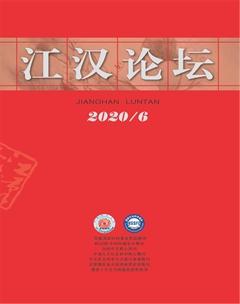中國戲劇人類學的進程與展望
周建新 李麗
摘要:戲劇人類學是文化人類學與戲劇美學的交叉學科,20世紀后期傳入中國并逐漸興起。中國戲劇人類學尚處于學科定位、研究內容、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等問題的探索階段。以學術視角為標準,可分為探究戲劇文化現象的“戲劇(文化)人類學”和探究戲劇本質的“戲劇(表演)人類學”。在全球化語境中,梳理中國戲劇人類學的產生背景、研究現狀和學術走向,有利于準確把握這一新興學科的主要問題與發展趨勢,以促進我國戲劇人類學參與國際對話與交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影響的戲劇人類學。
關鍵詞:中國戲劇人類學;進程;展望 ;學科建構
中圖分類號:I206.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0)06-0094-06
20世紀下半葉,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從社會科學領域對戲劇作出新解釋、進行新探索的研究趨向。為了解決戲劇自身研究問題,戲劇學科開始尋求更為廣闊的社會科學作為理論支持。而在民俗學、人類學等社會學領域,則以戲劇為載體研究戲劇文化現象。在這種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背景下,由戲劇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交叉形成的戲劇人類學在中國興起。中國的戲劇人類學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是將戲劇人類學看作一門系統的學科仍充滿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學科定位、研究內容及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筆者認為,在全球化語境中,對中國戲劇人類學的發生背景、研究現狀以及學術走向進行全面梳理,有利于我們更為清晰地了解戲劇人類學的發展情況,同時更有利于促進我國的戲劇人類學參與國際對話與交流,以推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影響的戲劇人類學。
一、中國戲劇人類學產生的雙重背景
戲劇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存在著雙重背景。一是西方戲劇人類學語境下的中國實踐,二是對本土戲劇的人類學研究。前者是30多年來西方“戲劇的人類學化或者是人類學的戲劇化”進程中,西方戲劇的人類學轉向與中西對話。后者則是在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對本土戲劇文化,包括對戲劇文學、戲劇形式、地域或民族性特色戲劇以及古典戲曲,從學院走向田野的學術自覺。
第一,西方戲劇的人類學轉向與中西對話。我們知道,公認最早提出戲劇人類學概念的是意大利戲劇學家尤金尼奧·巴爾巴。巴爾巴提出的戲劇人類學,是對20世紀西方先鋒、實驗戲劇的重要傳承和發展。然而戲劇人類學的產生與形成,卻遠早于此,它與西方的社會文化思潮緊密相連,本身也是時代的反映。到20世紀下半葉,戲劇家們逐漸意識到,戲劇以及戲劇活動是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對戲劇的理論及實踐是對社會生活的主體——人在特定情境下的關注與凝視。在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西方戲劇在時間上指向了遠古的“原始”,在空間上走向了“東方”。
1965年美國藝術史家羅伯特·戈德沃特在《現代藝術中的原始主義》一書的序言中寫道:“自梵高和高更對1889年巴黎博覽會上‘原始人的建筑和雕刻杰作加以贊賞至今,已經半個世紀了。現代藝術家后繼者們的靈感被他們自己所想象的原始的理想意象所激發,也從他們自身高度的個性觀出發而被非洲、大洋洲及前哥倫布雕刻富于個性的作品所激發。”① 藝術中“原始主義”傾向的出現,和20世紀初以來西方文化研究,特別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熱潮有關。這股“文化熱”甚至被看成繼歐洲文藝復興以來關于人的“第二次發現”。如果說,人的“第一次發現”是豪邁地宣告了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掙脫了神靈的枷鎖,那么,“第二次發現”就是清醒、冷靜地對人自身進行全面、客觀的審視。羅伯特·戈德沃特所說的藝術的“原始主義”傾向,在戲劇領域的突出表現,就是戲劇的“人類學化”傾向。這一傾向的出現是必然的。戲劇是一種在舞臺上創造人的形象的藝術,它和研究人的行為的人類學有著先天性的密切聯系。正如理查·謝克納所說:“戲劇人類學化,與此同時,人類學也戲劇化。”②
在西方這股文化研究的熱潮中,不僅活躍著大批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而且可以看到戲劇家的身影。其中以阿爾托的影響最為深遠,蘇珊·桑塔格評價道:“阿爾托對戲劇藝術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至于歐美的嚴肅戲劇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阿爾托之前與阿爾托之后。”阿爾托是西方戲劇“人類學化”的先驅。20世紀30年代,法國導演阿爾托提出了“殘酷戲劇”的主張,開始與傳統西方劇壇分裂,他主張回歸“戲劇的宗教化”的源頭,指出:“物體與字詞、與思想以及其代表者符號之間的斷裂”,面對物質與精神分裂,物與詞、思想、符號混亂無力的所指,應該“放棄戲劇從前所具有的人性的、現實的和心理學的含義而恢復它宗教性的、神秘的含義,這種含義是我們的戲劇所完全喪失的”③。阿爾托從“宗教性”與“神秘性”兩方面提出了現代戲劇應該“恢復它的宗教性”、回歸原始神秘的巫術思維,其首要途徑便是放棄傳統戲劇的情節、劇本、臺詞等,超越劇本中心、邏各斯中心,讓戲劇回到人自身的在場,回到表演本身。
1936年3月15日,俄國導演梅耶荷德在談到中國戲曲藝術的特點時,曾經預言:“再過二十五到五十年,將出現某種西歐戲劇藝術和中國戲劇藝術相結合的局面。”④ 果然,西方戲劇藝術家逐漸致力于研究東方戲劇,并將東西方戲劇藝術相結合。現代西方戲劇中的東方影響不局限于藝術形式與技巧方面,而是廣泛地存在于哲學、宗教、文學等其他方面。從阿爾托、格洛托夫斯基、謝克納、巴爾巴等人的戲劇理論與實踐中,都可以看到明顯的來自東方的影響。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西方戲劇中存在著一股強勁的“東方化”“人類學化”的趨勢。
另外,在學科建設上,近幾十年來,西方劇壇中很多帶有人類學性質的戲劇研究、表演研究逐漸走向學科化。1979年紐約大學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人類表演學系”,隨后在美國一些大學相繼開設了類似的專業或課程。在歐洲和澳洲的一些大學也開設了相關課程,如英國威爾士大學成立“人類表演學研究中心”、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建立了“人類表演學系”,很快地,歐美上千所大學都開設了這些課程。在這股戲劇研究學科轉向的浪潮中,與戲劇人類學相關的課程在傳播系、文學系設立,有的在政治系、心理學系、人類學系也可以找到,戲劇人類學化傾向逐步彰顯。在這樣一種跨學科研究的背景中,戲劇人類學作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學科概念,意義非常重大。
西方戲劇人類學者在這場與古老的、原始的、東方的戲劇藝術相遇過程中,關注演員的表演行為,探究戲劇表演的深層革新問題:將人的表演作為本體來觀照——戲劇是一種如何做人及如何看人的藝術。從這一背景出發,西方戲劇人類學,是西方先鋒實驗戲劇對“表演本體論”的重視,著重于“向表演突破”,是西方劇壇在“走向東方”乃至“走向中國”以尋求打破西方僵化的敘事為目的的舞臺戲劇的中西對話的結果。
第二,中國本土戲劇的人類學研究。中國戲劇人類學發展的另一個背景,是中國戲劇研究者們開始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對中國本土戲劇進行研究。
我國現代戲劇研究進程中,較早提出具有文化人類學傾向的戲劇觀念的是王國維,他指出:“后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⑤,然而“戲劇自巫、優出”實際上是他審視“人間”這一根本問題閃現的一顆思想火花。根據王國維有關戲劇的研究來看,“戲劇自巫、優出”僅是一種觀念的表達,王國維更注重的是對戲曲的文學價值、美學意境的考量。王國維之后,中國的戲劇人類學研究者們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戲劇文學、戲劇的發生(例如戲劇與“巫”的關系)、民間戲劇(比如儀式戲劇、“非遺戲劇”)等歷史文化語境中的本土戲劇進行田野考察,涌現出一批帶有戲劇人類學研究性質的戲劇研究成果,戲劇人類學由此在中國開始萌芽、逐步發展。
在我國,戲劇人類學正式獲得命名的一個顯著標志,應是1993年馬也《戲劇人類學論稿》的出版,這是首次對“戲劇人類學”進行關注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將戲劇定義為“戲劇是演員(為觀者或聽者)演故事的一種藝術”,簡言之是“演員演故事”⑥。這本著作圍繞這一定義,開展了關于戲劇發生論、功能論、發展論的理論闡釋,是一部典型的基于發生學意義的戲劇人類學著作。馬也引用泰勒、弗雷澤、列維-布留爾等人類學家的學術觀點,對史前的“演”與“摹仿”進行研究,以證明“扮”和“演”是戲劇的靈魂,并在早期巫術啞劇中已經存在。盡管《戲劇人類學論稿》主要是將文化人類學作為一種論證戲劇起源的研究視野引入其中,并未使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使用的仍然是傳統的戲劇美學范疇的研究方法,但馬也已經開始談及戲劇人類學的本體論問題,他明確認為:“文化或藝術的存在是人類存在的‘影子;離開人類學本體論的文化或藝術的本體論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人類學本體論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談文化或藝術的本體論問題。文化或藝術本體論是人類學本體論的一部分。”⑦ 顯然,馬也把戲劇人類學看作文化人類學的分支,戲劇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都人類學的一部分,這里實際上非常接近戲劇人類學的學科構建,可惜沒有詳細闡釋。
進入21世紀,戲劇人類學在中國有了新的進展。2003年容世誠的《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正式出版,這是一本以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為基本方法,對民間宗教儀式劇進行研究的論文集。正如序言所說:“本書取名‘戲曲人類學初探,是廣義地泛指一種從人類文化行為,特別是儀式行為探索中國戲劇的研究思路。同時,筆者是站在一個戲曲研究者的立場,尋求與人類學、表演學和其他學科的專家進行對話交流,以達到中國戲曲的跨學科研究的目的。”⑧ 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民間戲劇研究提供了跨學科方法,戲劇研究者回到藝術現場,以一個戲曲研究者的立場,尋求跨學科對話、研究的方法。
傅謹的《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是中國戲劇民族志的代表性成果,“該書以一個戲劇理論家的獨特視角,詳盡而細致地描述了臺州戲班的歷史與現狀、戲班的內部構成、戲班內演職員的生活方式、戲班的經濟運作方式,以及民間戲班特有的演出劇目與演出形式;客觀地剖析民間戲班的存在方式與內在構成,由此揭示了民間戲班擁有的頑強生命力的文化淵源”。⑨ 傅謹充分運用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長達8年深入跟蹤調查浙江臺州地區的民間戲班,其調查之深入、觀察之細致、思考之敏銳、探討之全面,令人拍案稱絕,可謂戲劇人類學著作的范本。其他運用田野調查方法關注民間戲劇、少數民族戲劇的重要成果,還有曲六乙的《儺戲·少數民族戲劇及其他》、蕭兵的《儺蠟之風——長江流域宗教戲劇文化》等。
二、中國學者關于戲劇人類學的學科建構
戲劇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一直糾纏在西方語境下的戲劇表演人類學與中國本土戲劇文化人類學的雙重背景之中。因學理背景、學術視角不同而有所區別,當下中國戲劇人類學,基本上分為以戲劇學為視角借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探究戲劇本質的“戲劇(表演)人類學”以及以文化人類學視角研究戲劇文化現象的“戲劇(文化)人類學”。
戲劇人類學作為戲劇學的研究方向就戲劇理論而言其理論和方法對傳統的戲劇學具有拓展和深化戲劇的某些問題的價值意義。而戲劇人類學若作為人類學的一個分支,戲劇作為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個文本、一種文化現象,實際上是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領域,更注重對戲劇背后文化大背景的深描,以探究人所創造的戲劇與人所創造的社會之間的關系為指歸。正因為如此,戲劇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仍然充滿爭議,而爭議主要體現在戲劇人類學的定義和學科定位上。
第一,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定義。1979年巴爾巴建立國際戲劇人類學學校,戲劇人類學首次獲得學科命名。此后有關戲劇人類學的學科建構都與他密不可分,基本上都是在他的基礎上的深化或批判,其中也包括中國學者的貢獻。有三位戲劇學者各自在其著作中專門論述戲劇人類學,這三本著作分別是:尤金尼奧·巴爾巴的《紙舟:戲劇人類學導引》、王勝華的《戲劇人類學》、陳世雄的《戲劇人類學》。
巴爾巴對戲劇人類學作出定義:“戲劇人類學研究的是不同類型(流派)、風格,以不同角色和個人或集體的傳統為基礎的舞臺行為的前表現性。在戲劇人類學的語境中,‘表演者一詞是指‘演員或者舞者,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戲劇指‘戲劇和舞蹈。”⑩ 巴爾巴對戲劇人類學的定義,其實是對戲劇人類學所研究的對象的闡述,即巴爾巴關注的人類在(有組織的)表演情境或戲劇活動中超日常的相關“舞臺行為”的前表現性。通過對演員的“前表現性”行為的研究,他揭示演員的表演中蘊藏著“技巧的技巧”,即前表現性的諸多原理(包括對立、平衡、一致的不一致、省略的效果等),這些“技巧的技巧”是所有演員所共同擁有的。演員在表演情境中擁有超越種族、性別、文化背景的共同技巧就存在于演員表演的“前表現性”行為當中。
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實踐與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不同的是,他不僅帶領劇團到世界各地實地觀察、研究當地人和戲劇有關的表演活動,還將劇團的戲劇表演作為“田野調查”交換的對象,進行“表演交易”,即劇團表演一個節目給當地人看,作為交換,當地人們也要表演一個他們本土的節目。這種“表演交易”是文化人類學家所未曾嘗試的交往活動,它是雙向輸出、雙向接收的一次既有獲得表演的田野調查結果又有文化輸出的交流活動,而用于交易的“通貨”是“表演”。他帶領劇團到其他國家的一些地方以戲劇表演作為交易,將戲劇現場鋪開在所到之處,與當地人進行“表演交易”,甚至與委內瑞拉一個充滿原始風情的印第安部落的亞諾瑪米人有過類似狩獵儀式的互動。
巴爾巴的另一個研究人類學的內容是跨文化戲劇研究。跨文化戲劇是他提出的“歐亞戲劇”、“第三戲劇”觀念的實踐,也是他關于戲劇人類學的實踐。巴爾巴在他創立的奧丁劇團之外專門成立了跨文化劇團MUNDI,主要負責演出多元文化項目的作品,包括《游行》、《哈姆雷特》、《美狄亞的婚禮》等作品。實際上,到了后期巴爾巴的工作包括工作示范、演員訓練以及奧丁劇團的創作,從內容與方式上看基本上都是跨文化戲劇的實踐,通過跨文化戲劇的實踐,巴爾巴試圖尋找的是一個所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個性特質的演員通過表演形成的“戲劇的烏托邦”。
第二,中國學者的貢獻。我國學者曾靜從當代戲劇人類學田野作業與民族志書寫的角度,認為巴爾巴的戲劇理論與實踐在使用了田野方法的同時,在民族志書寫上具有創新和實驗意義,可以被視為“戲劇實驗民族志的嘗試者”。其理由是:通過“表演交易”多點式的田野調查,采集個案探索戲劇的共同規律;不僅研究對象,且把對對象的研究當作研究對象,展現他介入到中國、日本、印度、巴厘島等異文化戲劇研究的主體感知過程;巴爾巴對跨文化戲劇——戲劇人類學的一種特殊修辭的研究;巴爾巴個人多文體的民族志式的書寫,包括游記、小說、表演筆記等。{11}
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僅是一個開端,在學界雖頗具爭議,但是開啟了戲劇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陳世雄就對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有過深入的分析和批評。陳世雄在《戲劇人類學》中對戲劇人類學的定義是:“戲劇人類學是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戲劇,同時又透過戲劇研究人類文化的一門交叉學科。”陳世雄戲劇人類學的核心觀念是:戲劇是人的自我實驗。他認為,戲劇是對規定性情境中的不同人群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直觀的觀察,戲劇給人們提供了自我演練、實驗的場景,正如人類學對人的行為的觀察、研究一樣。他指出了巴爾巴等人關于戲劇人類學研究中所存在的片面性,并針對這些片面性,表明了自己對于戲劇人類學的基本立場。筆者認為,他提出的戲劇人類學的建設,是與以巴爾巴等人為代表的西方戲劇人類學的一場深刻的學術對話,同時,也是對中國戲劇人類學學科建構的表達。他細致區分了表演與扮演的區別{12},他所認為的被西方戲劇人類學所忽略和呼吁戲劇人類學學者應該注意的問題,恰好正是巴爾巴等提倡的西方戲劇人類學的主要特點。陳世雄從中國民間目連戲到宮廷目連戲的發展探究戲劇的起源,論述中西戲劇與儀式之間的關系;研究演員的身體、面具、傀儡與戲劇的關系,等等,通過西方戲劇人類學反推中國戲劇人類學的學科定義。基于西方戲劇人類學對“表演”特別關注的傾向,陳世雄在中西對話的語境中,指出戲劇人類學研究應該注意如下幾個問題:第一,戲劇人類學應當劃清“表演”和“扮演”的界線。而西方戲劇家們如謝克納、巴爾巴所關注的表演已經變得越來越寬泛,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以及舞蹈、其他舞臺藝術中存在的表演。而對于戲劇中的表演,重點在于角色的扮演。第二,應當重視演員形體動作與心理過程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相比之下,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關于演員表演的“前表現性”原理的研究,表演“技巧的技巧”更多的是一種實用性的關于表演的生理過程的形體訓練。這無疑引起了陳世雄提出戲劇人類學應該對演員角色扮演的“形體動作”與“心理過程”二者關系的重新審視的命題。第三,對表演者的研究應包括對角色的研究。第四,在人類學視野下運用比較的方法,把東方戲劇,特別是中國戲曲納入研究范圍,通過東西方的對比,探索戲劇特別是戲曲的藝術規律,以利于戲曲藝術的繁榮發展。因此,陳世雄的戲劇人類學是與西方戲劇人類學的對話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建構,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比較法對中西戲劇的問題進行研究,不僅包含了西方戲劇人類學的表演人類學研究也包含了本土戲劇文化人類學的內容,這是對戲劇人類學研究的客觀審視,因為巴爾巴戲劇人類學的確代表了戲劇人類學重要的研究方向,但是它不應該是戲劇人類學的全部,尤其應該通過對于中國戲劇,特別是中國戲曲等本土戲劇研究,以探索本土戲劇理論的建構。
與巴爾巴、陳世雄兩位不同的,但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學科歸屬辨析的,是王勝華在其著作《戲劇人類學》中對戲劇人類學的定義:“戲劇人類學是依據戲劇資料,運用戲劇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研究人類社會、人類發展規律的學科。”{13} 在著作中王勝華非常明晰地指出戲劇人類學屬于文化人類學的分支學科,且屬于文化人類學下藝術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戲劇人類學》以時間與空間為線索,從時間維度研究中國戲劇的發生、發展,從戲劇發生學視角關注中國戲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空間維度研究戲劇空間(物理空間、文化空間)與城鄉差異,最后探索戲劇與人類心理的人類學之根本問題。尤為重要的是,這些研究都有詳實的田野調查為支撐,運用了文化人類學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基本方法,對中國戲劇及戲劇背后的文化大背景進行深描,在深入解釋戲劇的基本規律的同時,探究人所創造的戲劇與人所創造的社會之間的關系。
關于戲劇人類學的概念與學科定位,以及戲劇人類學應該怎樣處理戲劇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關系,譚霈生在《有關戲劇學學科建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由于戲劇人類學的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特性,要求研究者們兼備戲劇與相對應的學科知識結構和理論能力。其中,對戲劇本體的認識應該是前提條件”,“所謂‘戲劇學雖然也被定位為一種科學,但是,它的研究對象卻是一種藝術,從宏觀上講,這就涉及科學與藝術的關系。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學、人類學等都是科學,它們與藝術的本性是對立的。……無論我們可以從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學科中獲得多少理性的認識,從而擴展、深化對戲劇中某些問題的理解,但是,以‘戲劇為對象的研究主體,卻不應遺忘對象的特殊性”。{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