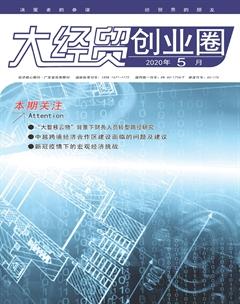論我國醫療決定代理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尹曉慶
【摘 要】 當患者缺乏自主決定能力或者不宜對醫療行為作出自主決定時,需要由他人代為決定,此時的代理具有強烈的人身性,我國《民法典》在《侵權責任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可適用代理的情形,但尚未能構建起完善的醫療決定代理制度,應當從維護患者自主決定權的角度出發,明確代理的理論依據、適用前提、代理人范圍以及代理規則等問題,真正實現醫療決定代理保障患者權益的作用。
【關鍵詞】 自主決定權 知情同意 醫療決定代理
一、問題的提出
醫療決定代理是在患者無法自主作出醫療決定時,由有權代理人代為決定的行為,我國《民法典》規定了“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情形。醫療決定與患者的人身權益密切關聯,應當考慮允許醫療決定代理適用的情況,探究患者自主決定能力的判斷標準問題。此外,醫療決定代理人應當以患者自主意愿和人身權利為基準,遵循代理規則作出代理決定,就我國現行法規定而言,對于代理人的具體范圍、代理規則等問題仍存在可細化和完善的空間。
二、患者自主決定權與知情同意規則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上訴法院在Salgo案中首次使用“知情同意”原則。在知情同意規則下,患者有權對病情狀況、診療措施以及相應的醫療風險等信息知情,并在此前提下根據各自情況作出符合其自主意愿的決定。
知情同意規則與患者的自主決定權不可分離。關于二者關系,有學者從人格權角度出發,認為知情同意與自主決定權存在相當的差別,指出“同意”強調被動接受而“決定”則是權利人自主決定;[1]有學者從醫療權利的角度出發,認為知情同意權和自主決定權同屬于醫療過程中的患者權利,內容有所不同卻密不可分;[2]還有學者針對知情同意權的權利宿主提出不同見解,認為其應當屬于隱私權而非自主決定權。[3]盡管觀點各異,但幾乎達成普遍共識的是,患者的自主決定權通過知情同意規則得以實現,知情同意規則為患者實現自主決定權提供具體的制度保障。[4]
我國《民法典》第1002條將生命權概括為“生命安全”與“生命尊嚴”,彰顯出民法對于生命尊嚴的注重。[5]患者作為獨立的個體,享有對相關醫療信息的知情權和作出自主決定的自由,因此,貫穿于醫療過程中的知情同意規則,不僅關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權,更核心是在于保護患者的自主決定權、維護其生命尊嚴。
三、醫療決定代理制度的具體規則
(一)適用前提。患者自主決定權是其自身人格權利的體現,在作出醫療決定時首先應當考察患者的自主意愿,謹慎處理代理的前提條件問題,遵循保護患者自主決定權和人格尊嚴的基本原則。
關于患者自主決定能力的判斷問題,《病歷書寫基本規范》第10條將民事行為能力適用于與自主決定能力的判斷,民事行為能力是否可直接運用于醫療決定中自主決定能力的判斷?答案是否定的,行為能力是為維護交易安全而生,但自主決定權所涉及到的同意權是權利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因此兩者盡管存在交叉的部分,但由于性質不同,不能完全等同視之。[6]
發達國家基本形成了以患者有無識別能力為判斷標準的表意能力說,[7]患者的識別能力是理解所同意的內容、意義和效果的能力,此種能力應以個案認定的方式加以判別,即醫務人員在長期的診療過程中,通過與患者交流以及對患者身體狀況、精神狀況的了解,能較為客觀地判斷患者是否能夠理解醫療行為所涉及到的信息以及是否有作出決定的能力。醫療事務因其特殊性而不能直接適用民事行為能力的判斷標準,且醫療決定關涉個人人格尊嚴,適用統一的判斷標準極易導致患者的人格權利遭受侵犯,因此,區分個體差異,以個案認定的方式判斷識別能力具有正當性。同時,應當考慮到,由于個案認定的難度較大,可以引用醫學領域的相應標準,由相關的醫務人員參與認定,形成科學合理的認定機制,全面判斷患者識別能力。
“不宜向患者說明”作為前提條件之一,相較于以自主決定能力為基礎的“不能”而言,顯然更具有導致判斷任意性的風險。不宜說明的情形實質上指向實施保護性醫療措施涉及到的信息,即可能挫傷患者求生意志、損害身心健康等不利于患者治療的信息。但正如前文所論述,知情同意權是不可剝奪的患者本人的權利,由第三人來判斷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判斷醫療信息是否對患者的意志有挫傷效果,這本身就是一種剝奪,且在實踐中存在過度援引的風險,以致不適當地擴大代為決定的范圍。因此,應當秉承保護患者自主權的精神,原則上只將患者不具有自主決定能力作為他人代理的例外情形,若有切實證據證明患者情緒將對治療帶來嚴重不利影響,不得不向其隱瞞真實情況的,可以轉變告知和獲取同意的方式,及時安撫患者情緒、和患者家屬溝通,共同將不利影響控制到最低,比如我國臺灣地區所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第5條的規定,“病人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方式,將病人之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后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人”。
(二)代理人范圍。患者作為獨立自主的主體,應有提前以意定方式選擇代理人的權利,即便在沒有預先處理的情況下,代理人的范圍也需要以具體的規則加以明確。
預立醫療指示制度能促進患者醫療決定自主權的實現。預立醫療指示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為防止將來無法表達醫療決定意愿的狀況,在個人尚有識別能力時,預先作出的關于處理醫療事務的書面表達,即“預立醫囑”,二是在個人意識清楚時將醫療行為的代理權授予給值得信賴之人,由該代理人在其缺乏自主決定能力時行使代理,即“醫療持續性代理”。在預立醫療指示制度中,患者自主決定權的實現實質上只是在時空上進行了推移,其核心同樣是為維護個人的自主權利和人格尊嚴,也符合我國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社會現狀,且雖然我國意定監護制度將被監護人的意愿置于法定之前,但現有的法律制度并未將醫療決定代理作為監護制度下的特殊規定,意定監護制度尚不能直接適用于醫療決定代理問題,因此,在我國確立預立醫療指示制度是有必要的。
醫療決定的高度人身性,決定了要以最切合患者主觀意愿的意定代理人為首選,只有在沒有委托意定代理人時,才考慮法定的醫療決定代理人人選。關于法定醫療決定代理人,發達國家的法律對此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制,比如《瑞士民法典》第378條規定醫療法定代理人以“與無判斷能力人共同生活”或者“經常親自照管無判斷能力人”為條件,《美國馬里蘭州醫療決定法》對患者的非近親屬及朋友提出了類似要求,《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則對醫療決定代理人的選擇規定了排除條款。可見,醫療決定是關乎患者人身的重大事項,即便沒有意定代理人也需審慎確定法定的代理人,我國法律僅粗略規定由“患者的近親屬”代理,而在實際運用中,還應從患者利益出發,根據與患者的利益關系、親疏關系、是否尊重患者意愿等背景來確定代理人。
(三)代理規則。根據醫事法和生命倫理學學界通說,醫療代理決定應當按照以下順序執行:一為自主簽署的預囑,二為替代判斷,三為最佳利益。自主簽署的預囑是患者自主意愿的直接表達,是代理決定所能依據的最優選項,在明確表達患者意思的自主預囑不存在的情況下,取而代之的是替代判斷的標準,即假設此時患者在有自主決定能力的情況下會做出什么醫療決定,替代判斷標準和自主預囑都屬于探求患者真實意愿的方式。在不存在自主預囑又難以探求患者意愿時,第三順位的最佳利益則成為代理的最后一順位標準,最佳利益標準是在考量所有可能的情形之后確定的最有利于患者身體健康權利的標準。
關于替代判斷,即假設患者有能力的情況下會做出何種決定,通過既往的信息判斷患者可得推知的意愿,其核心仍然是遵循個人自主權利的原則。替代標準并不是患者真實的意思表達,而是通過一系列證據推定的最接近于患者真實意思的處理,那么問題就在于如何推斷患者可能的意愿,一方面可以患者對此類相似情況作出的意思表示為參照,另一方面,代理人的選擇尤為重要,比如與患者共同生活或者關系密切的代理人,通過對患者的生活習慣以及道德信仰、價值觀念等思想層面的了解,可以找到支撐代理決定的依據。
替代判斷著眼于患者自主權利的實現,能接近患者真實意愿固然是最終目的,但究其根本也只是一種主觀推斷,能否反映患者意思尚不可保證,況且現實狀況紛繁復雜,判斷難度較大,且無法通過現有線索推斷得知患者意思的也屬常見,此時應當根據最佳利益標準進行,以尊重患者自主意愿為基本原則,也要兼顧患者生命健康權利的保護。最佳利益標準是在無法考察和推斷出患者真實意愿時,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為患者利益而作出的處理,客觀上有利于患者生命健康權利,是醫療決定代理應當遵循的規則之一,但因其并未以患者本人意愿為出發點,在醫療決定代理中類似于兜底性的規則。
四、結語
醫療決定代理制度關乎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和人格尊嚴,在實施過程中首要考慮的應當是患者的自主意愿,此觀念應貫穿制度建設的始終。在醫療決定代理的適用前提方面,以患者識別能力為判斷依據,診療信息可能對患者產生不利影響時可轉變告知方式,通過個案具體判定是否適用醫療決定代理。代理人的選擇應以患者意定為原則,法定次之,在考慮代理人時應參考其與患者的親近關系等因素。代理規則要遵循最大程度尊重患者自主的原則,按照自主簽署的預囑、替代判斷、最佳利益的順序執行。
【參考文獻】
[1] 楊立新,劉召成.論作為抽象人格權的自我決定權[J].學海,2010,(5):189.
[2] 趙西巨.醫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61.
[3] 郭明龍.論患者隱私權保護——兼論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請求權基礎[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3,(3):87.
[4] 葉欣.患者知情同意權的價值目標與法理思辨[J].學習與實踐,2019,(4):77.
[5] 張紅.民法典之生命權、身體權與健康權立法論[J].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0(2):71.
[6] 程嘯.論侵權行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4):112.
[7] 黃丁全.醫事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