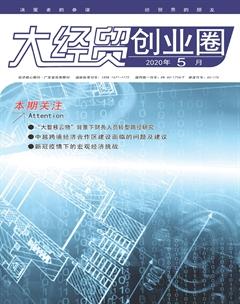重大誤解制度之重大性要件研究
【摘 要】 在重大誤解制度的構(gòu)成要件中,誤解是否重大被認(rèn)為是最關(guān)鍵的要素。但我國立法卻未對此予以明確,學(xué)界也是眾說紛紜。通過對學(xué)界觀點(diǎn)、司法實(shí)踐以及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梳理,在重大性要件的認(rèn)定上宜采納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主觀上考慮表意人心理狀態(tài),客觀上從第三人角度展開客觀分析,在客觀重大性上,引入一般理性人與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考察一個(gè)誠信守信的理性人在基于一般的交易目的時(shí)的內(nèi)心意思。
【關(guān)鍵詞】 重大誤解 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 一般理性人
一、問題提出
(一)重大誤解制度的內(nèi)涵。重大誤解并不是一個(gè)國際通用的概念,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及國際統(tǒng)一法在立法與實(shí)踐中使用的均為“錯(cuò)誤”概念。追根溯源,我國民法上所稱的重大誤解制度源自蘇聯(lián)[1],目前,仍有許多學(xué)者主張應(yīng)當(dāng)跟隨國際步伐,修改“重大誤解”制度為國際上更為普遍的“錯(cuò)誤”制度。
重大誤解制度主要適用領(lǐng)域在合同法,與合同未成立、合同解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存在本質(zhì)不同。首先,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dāng)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jī)構(gòu)予以撤銷,撤銷的前提在于合同已實(shí)際成立,與未成立的合同存在著本質(zhì)差別[2]。其次,因合同未成立產(chǎn)生的賠償問題適用的為三年的訴訟時(shí)效,而可撤銷的重大誤解合同適用的為一年的除斥期間。其次,重大誤解賦予了當(dāng)事人對合同整體進(jìn)行撤銷的權(quán)利;合同解釋則是在保留合同效力的前提下,對合同中有爭議的條款通過文義、體系、歷史解釋等解釋方法進(jìn)行重新詮釋,確定合同內(nèi)容。
(二)重大誤解制度的法律規(guī)定。即將生效的《民法典》第147條規(guī)定,基于重大誤解實(shí)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行為人有權(quán)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jī)構(gòu)予以撤銷。當(dāng)下現(xiàn)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民通意見》)第71條對認(rèn)定重大誤解做了簡要規(guī)定:“行為人因?qū)π袨榈男再|(zhì)、對方當(dāng)事人、標(biāo)的物的品種、質(zhì)量、規(guī)格和數(shù)量等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的,可以認(rèn)定為重大誤解。”該條規(guī)定列舉了重要的錯(cuò)誤類型,并要求應(yīng)造成較大損失,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如在實(shí)踐中出現(xiàn)列舉內(nèi)容之外的錯(cuò)誤,是否可認(rèn)定為重大誤解?重大誤解之重大性如何認(rèn)定?這些問題都需要學(xué)界不斷分析、探討、解決。
(三)重大誤解制度的構(gòu)成要件。在明確構(gòu)成要件之前,我們有必要回應(yīng)錯(cuò)誤一元論與錯(cuò)誤二元論的學(xué)理爭議[3]。錯(cuò)誤二元論是指將錯(cuò)誤區(qū)分為表示錯(cuò)誤與動(dòng)機(jī)錯(cuò)誤[4],表示錯(cuò)誤是指因錯(cuò)誤導(dǎo)致其內(nèi)心意思與外在表示不一致,動(dòng)機(jī)錯(cuò)誤是指當(dāng)事人的意思本身就存在錯(cuò)誤。錯(cuò)誤二元論的觀點(diǎn)將動(dòng)機(jī)錯(cuò)誤原則上予以排斥,即重大誤解一般僅指表示錯(cuò)誤。錯(cuò)誤一元論則未作此區(qū)分,此時(shí)錯(cuò)誤不僅包括動(dòng)機(jī)錯(cuò)誤,還包括表示錯(cuò)誤。本文基于錯(cuò)誤一元論展開論述。在錯(cuò)誤一元論的前提下,學(xué)界認(rèn)為,重大誤解制度的構(gòu)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幾個(gè):
1.民事法律行為已成立。如前所述,重大誤解制度雖與合同未成立有密切聯(lián)系,但二者存在本質(zhì)的不同。撤銷的前提在于民事法律行為已依法成立,只有業(yè)已成立的民事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才可以基于發(fā)生了重大誤解而請求法院撤銷。
2.誤解須是重大的。只有產(chǎn)生了重大的誤解,當(dāng)事人才可以基于重大誤解制度請求撤銷。一方面,重大誤解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救濟(jì)途徑,可以幫助在行為中因動(dòng)機(jī)錯(cuò)誤、表示錯(cuò)誤而陷入不利境地的當(dāng)事人從法律行為中解脫出來,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實(shí)質(zhì)正義;另一方面,為了維護(hù)交易安全、保護(hù)相對人信賴?yán)妫刹粦?yīng)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做過多的干涉。因此,應(yīng)當(dāng)對誤解設(shè)定條件進(jìn)行限制,即誤解只有在滿足“重大”要件時(shí),才可產(chǎn)生撤銷民事法律行為的效果。后文筆者將重點(diǎn)論述重大性要件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
3.因重大誤解而為民事法律行為。這是因果關(guān)系要件,即當(dāng)事人是基于錯(cuò)誤認(rèn)識(shí)才作出的民事法律行為,如果沒有誤解,則不會(huì)為此行為。
4.不具備消極要件。在滿足上述三個(gè)積極要件后,只有民事法律行為不存在消極要件時(shí),才可基于重大誤解請求撤銷[5]。消極要件是指,當(dāng)事人的撤銷權(quán)未消滅。具體來說,撤銷權(quán)的消滅事由主要有:重大誤解的當(dāng)事人自知道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gè)月內(nèi)沒有行使撤銷權(quán);當(dāng)事人知道撤銷事由后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放棄撤銷權(quán);當(dāng)事人自民事法律行為發(fā)生之日起五年內(nèi)沒有行使撤銷權(quán)的,撤銷權(quán)消滅。
(四)認(rèn)定重大性要件的必要性。一旦認(rèn)定重大誤解,業(yè)已成立的合同即可能被撤銷,最終歸于無效,交易安全將受到嚴(yán)重沖擊,相對人的信賴?yán)嬉矊⑹艿角趾ΑR虼耍卮笳`解的認(rèn)定必須有其合理限度,若適用范圍過小,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將無法實(shí)現(xiàn),若過大,交易安全又難以保障。“重大性”作為重大誤解制度最重要的構(gòu)成要件之一,可用以規(guī)范重大誤解的輻射范圍。但重大性本身較為抽象,立法也未予以明確,如果不加以認(rèn)定,重大誤解的范圍將難以確定。其次,認(rèn)定重大性要件有利于法院判決的證成,充實(shí)法理分析部分,便于解決實(shí)際問題,使判決既合情又合法。
二、我國重大性要件之認(rèn)定及司法適用
重大誤解制度并不是新興的一項(xiàng)制度,我國學(xué)界對此已有長久的討論過程。有關(guān)重大性要件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主要存在三類學(xué)說:錯(cuò)誤對象與重大不利后果結(jié)合說;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
(一)錯(cuò)誤對象與重大不利后果結(jié)合說。該種學(xué)說的主要支持者為隋彭生、崔建遠(yuǎn)、張小勇、樊林等學(xué)者1,強(qiáng)調(diào)在認(rèn)定重大誤解之重大性要件時(shí),應(yīng)重點(diǎn)考慮兩方面的因素:錯(cuò)誤對象、不利后果。
錯(cuò)誤對象即對什么產(chǎn)生錯(cuò)誤會(huì)導(dǎo)致重大誤解。該學(xué)說認(rèn)為,只有對標(biāo)的物的本質(zhì)、行為性質(zhì)的錯(cuò)誤,才能視為構(gòu)成重大誤解的錯(cuò)誤。如果發(fā)生錯(cuò)誤的事項(xiàng)是不涉及合同主要內(nèi)容的細(xì)節(jié)錯(cuò)誤,因其本身無關(guān)緊要,不可歸為重大誤解的錯(cuò)誤對象。
不利后果是基于《民通意見》第71條作出的闡釋。該學(xué)說認(rèn)為,判斷重大誤解是否成立,應(yīng)考量錯(cuò)誤是否給當(dāng)事人帶來了較大損失,如果錯(cuò)誤并不產(chǎn)生使當(dāng)事人接受重大的損失,其不應(yīng)視為重大誤解。這種不利后果可從兩個(gè)方面予以考量:一是所支付的合同對價(jià)是否合理;二是當(dāng)事人是否因誤解訂立了與本意相反的合同,由此遭受了較大損失。
(二)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主張認(rèn)定重大誤解時(shí)應(yīng)兼顧主觀標(biāo)準(zhǔn)與客觀標(biāo)準(zhǔn),只有在二者同時(shí)具備時(shí)方可認(rèn)定構(gòu)成重大誤解。主觀標(biāo)準(zhǔn)是指具體民事法律行為中的表意人在締結(jié)合同時(shí)若知曉事情便不會(huì)為此意思表示,將不會(huì)締結(jié)合同或以不同的條款締結(jié)合同[6]。客觀標(biāo)準(zhǔn)引入了一般理性人,要求在判斷是否構(gòu)成重大誤解時(shí),設(shè)想一位誠實(shí)信用的理性人,在面對表意人所處情境時(shí)是否會(huì)為相同的意思表示。
(三)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與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的關(guān)鍵區(qū)別在于,是否承認(rèn)獨(dú)立的因果關(guān)系要件。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認(rèn)為“重大”包括主觀的與客觀的,不承認(rèn)存在獨(dú)立的因果關(guān)系要件;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則認(rèn)為,“錯(cuò)誤在交易上認(rèn)為重要”與“錯(cuò)誤與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guān)系”是兩項(xiàng)要件,也即承認(rèn)獨(dú)立的因果關(guān)系要件。兩種學(xué)說均各有利弊,只要邏輯上能夠自圓其說,均無不可。
對于客觀方面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又可細(xì)分為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是在具體行為中,裁判者引入一個(gè)誠實(shí)信用的理性人作為標(biāo)準(zhǔn),衡量其如無此錯(cuò)誤,是否會(huì)與表意人為相同的意思表示。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是以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的相對人作為判斷主體,從其角度出發(fā),保護(hù)相對人合理的信賴?yán)妗=灰咨现匾獦?biāo)準(zhǔn)是從純粹客觀的角度出發(fā),根據(jù)法律行為所追求的典型經(jīng)濟(jì)目的判斷該錯(cuò)誤的發(fā)生是否重大到需要被撤銷,以最大程度地保護(hù)交易安全。
三、重大性要件之域外立法
作為一項(xiàng)重要的撤銷事由,域外同樣對重大誤解做了明確規(guī)定。意大利、瑞士、德國、日本等國,以及國際統(tǒng)一法均對此有所規(guī)定,并對重大性要件提出了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等要求。
(一)意大利。意大利有關(guān)錯(cuò)誤制度的規(guī)定主要體現(xiàn)于《意大利民法典》第1429條、第1431條中。意大利將錯(cuò)誤限制為“顯著性錯(cuò)誤”,或可表述為“實(shí)質(zhì)性錯(cuò)誤”,認(rèn)為只有實(shí)質(zhì)性的錯(cuò)誤才可影響合同效力。意大利第1429條列舉了顯著性錯(cuò)誤的類型,并在第1431條中規(guī)定了可識(shí)別性錯(cuò)誤的概念,其中引入了善良家父作為判斷主體。可以認(rèn)為,意大利民法典中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結(jié)合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客觀方面,更傾向于一個(gè)善良、誠實(shí)的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
(二)瑞士。瑞士對錯(cuò)誤制度主要規(guī)定于《瑞士債法典》第 23-25條[7]中,瑞士采用的是主觀、客觀標(biāo)準(zhǔn)相結(jié)合的立法原意,在客觀標(biāo)準(zhǔn)上更強(qiáng)調(diào)相對人可識(shí)別性。不難理解,在雙方民事法律行為中,既有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也有接受表示的相對人,只有引起錯(cuò)誤的事實(shí)可能為相對人所認(rèn)識(shí)為錯(cuò)誤的構(gòu)成要件,才會(huì)實(shí)際損害相對人的利益。該種觀點(diǎn)注重保護(hù)相對人的信賴?yán)妫彩亲非髮?shí)質(zhì)公正的體現(xiàn)。
(三)德國。《德國民法典》第 119 條規(guī)定:(1)在做出意思表示時(shí),就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發(fā)生錯(cuò)誤或者根本無意做出包含這一內(nèi)容的意思表示的人,如須認(rèn)為表意人在知道事情的狀況或合理地評價(jià)情況時(shí)就不會(huì)做出該意思表示,則可以撤銷該意思表示。(2)關(guān)于交易上認(rèn)為重要的人的資格或物的特性的錯(cuò)誤,也視為關(guān)于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的錯(cuò)誤[8]。從第1款可以看出,德國仍然采用了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主張裁判時(shí)應(yīng)考慮表意人的心理狀態(tài)。第2款中所述“交易上認(rèn)為重要的人的資格或物的特性的錯(cuò)誤”,表示其適用的是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是從經(jīng)濟(jì)目的出發(fā),在具體的法律行為中判斷錯(cuò)誤是否導(dǎo)致當(dāng)事人所欲追求的經(jīng)濟(jì)目的無法實(shí)現(xiàn),以此來認(rèn)定客觀重大。
(四)日本。2017年,《日本民法修正案》通過,第 95條對錯(cuò)誤進(jìn)行了規(guī)定——意思欠缺型錯(cuò)誤與法律行為基礎(chǔ)錯(cuò)誤都要滿足“依照法律行為的目的及社會(huì)通行的交易觀念為重要”的要件[9]。不難得出,日本在立法中也十分注重“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在客觀層面,應(yīng)當(dāng)依照法律行為目的與一般大眾的交易理念來判斷錯(cuò)誤是否系重要的。
(五)當(dāng)代國際統(tǒng)一私法中的規(guī)定。為了重大誤解制度的全球適用,現(xiàn)行有效的國際統(tǒng)一私法也對錯(cuò)誤制度做了規(guī)定。《國際商事通則》(PICC)采用了一般理性人的標(biāo)準(zhǔn),假想一個(gè)符合社會(huì)通行理念的理性人,將其置于表意人情形下,判斷其會(huì)如何反應(yīng),以此來認(rèn)定合同效力。《歐洲合同法原則》(PECL)引入了對方當(dāng)事人,認(rèn)為在對方當(dāng)事人的信賴?yán)娌恢档帽Wo(hù)時(shí),發(fā)生錯(cuò)誤的表意人可以請求救濟(jì),即客觀上適用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歐洲私法的原則、定義和示范規(guī)則》(DCFR)與PECL的規(guī)定比較類似,均提出了相對人可識(shí)別的標(biāo)準(zhǔn),僅有表述上的細(xì)微差別。
四、重大性要件認(rèn)定的可能路徑
重大誤解是“無意中為非真意之表示”,因此,基于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保護(hù),追求實(shí)質(zhì)公正,我國法律規(guī)定了可撤銷的救濟(jì)方式;但作為業(yè)已成立的民事法律行為,如動(dòng)輒即被法律宣告無效,交易安全將受到嚴(yán)重威脅,相對人利益也可能受到損害。由此,重大誤解制度的實(shí)施必須有合理范圍限制,重大性要件作為重大誤解的限定條件之一,有必要對此進(jìn)行明確,為司法適用提供法理依據(jù)。
(一)應(yīng)采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錯(cuò)誤對象與重大不利后果說與現(xiàn)行有效的立法較為接近,甚至可以說是《民通意見》第71條的解釋論,也具有較強(qiáng)的操作性。但該學(xué)說尚有不足之處:首先,在體例上,該學(xué)說將對象的認(rèn)定至于重大性要件中,不太妥當(dāng)。錯(cuò)誤對象應(yīng)歸屬于“誤解”的范疇調(diào)整。其次,重大不利后果的考量仍然不夠明確,該標(biāo)準(zhǔn)仍然較為抽象。最重要的是,將重大不利后果作為重大性要件的考量因素不當(dāng)限縮了重大誤解的適用范圍。對于未發(fā)生較大損失,但行為人間的確發(fā)生了影響合同主要內(nèi)容的重大誤解,此時(shí)出于對當(dāng)事人內(nèi)心真意的尊重,保護(hù)意思自治原則,也應(yīng)撤銷法律行為。而重大不利后果要件的存在便將這類案件排除在外,使其無法獲得實(shí)質(zhì)救濟(jì),無疑限縮了重大誤解的適用范圍。
相比之下,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對重大誤解的考慮更為周全。該學(xué)說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從表意人角度、第三人角度出發(fā)判斷,既考慮了表意人主觀上的意思表示,又從客觀上予以考查,較為全面。單一適用主觀標(biāo)準(zhǔn)或客觀標(biāo)準(zhǔn)裁判的案件說服力不強(qiáng),也許結(jié)果符合社會(huì)通行觀念,但法律證成過程一般不夠使人信服。主觀上,考慮表意人在作出行為時(shí)的情境下,如得知實(shí)際情況,是否將不會(huì)行為,或以實(shí)質(zhì)上不同的方式、內(nèi)容作出行為;客觀上,引入第三人,從非表意人的角度,客觀地看待。
(二)客觀考量因素。在客觀重大性上,仍然存在不同的觀點(diǎn),有的認(rèn)為應(yīng)采取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引入一個(gè)誠實(shí)守信的第三人判斷,有的認(rèn)為應(yīng)考查相對人是否可識(shí)別,有的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行為的經(jīng)濟(jì)目的,從交易上純粹客觀地判斷重大與否。本文認(rèn)為,應(yīng)綜合考慮一般理性人與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
首先,無需也不宜采用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無需采用的理由在于,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很大程度上可以為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所囊括,一個(gè)誠實(shí)信用的一般理性人自然會(huì)在作出決定時(shí)考慮到相對人的利益。在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中,我們所引入的第三人是符合社會(huì)通行理念的、誠實(shí)信用的、具備一般人所有的認(rèn)知力判斷力的理性人,如此之人,其在為民事法律行為時(shí)必然會(huì)兼顧相對人的合理信賴。如果相對人的利益無法通過誠實(shí)信用之人的考量,可能其本身就不值得法律保護(hù)。因此,在適用一般理性人的基礎(chǔ)上再行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或許是多余的。不宜采用的理由在于,相對人可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仍然只是針對具體的當(dāng)事人在考量,而基于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所做的考量是在同類交易中做的考量,更具普遍性,更能符合社會(huì)通行的觀念。
其次,應(yīng)當(dāng)綜合考慮一般人標(biāo)準(zhǔn)與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即考慮一個(gè)誠信守信的理性人在基于一般的交易目的時(shí)會(huì)作何行為。其一,作為民商事法律行為的重要制度,認(rèn)定重大誤解時(shí)不應(yīng)忽視商事方面的考慮。為了保護(hù)交易安全,商事上需要對重大誤解的適用進(jìn)行合理的限縮[10]。因此需要引入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分析法律行為的經(jīng)濟(jì)目的,避免重大誤解的擴(kuò)大適用;其二,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與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一般理性人的思維也是在具體的案件中基于對交易重要的判斷,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的考慮主體也是一般人,因而二者應(yīng)當(dāng)綜合把握,缺一不可。
五、結(jié)語
本文列舉了國內(nèi)、域外多位學(xué)者、多項(xiàng)立法中關(guān)于重大誤解制度的觀點(diǎn),不可否認(rèn),上述觀點(diǎn)均有其合理之處,并可為司法實(shí)踐解決重大誤解問題提供法理上的緣由,但同時(shí),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文認(rèn)為,就重大誤解制度之重大性要件,應(yīng)當(dāng)采用主客觀標(biāo)準(zhǔn)說,在客觀標(biāo)準(zhǔn)的認(rèn)定上,應(yīng)結(jié)合一般理性人標(biāo)準(zhǔn)與交易上重要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斟酌考量。
【注 釋】
[1] 詳見隋彭生.關(guān)于合同法中“重大誤解”的探討[J].中國法學(xué),1999(03):104-110.、崔建遠(yuǎn):《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頁、張小勇,樊林.論可撤銷合同——兼評《合同法》第54條之規(guī)定[J].政法論叢,2000(02):54-57.
【參考文獻(xiàn)】
[1] 陳耀東,沈明焱.重大誤解制度“重大”之認(rèn)定[J].學(xué)術(shù)論壇,2018,41(04):143-152.
[2] 隋彭生.關(guān)于合同法中“重大誤解”的探討[J].中國法學(xué),1999(03):104-110.
[3] 武騰.民法典編纂背景下重大誤解的規(guī)范構(gòu)造[J].當(dāng)代法學(xué),2019,33(01):16-27.
[4] 冉克平.民法典總則視野下意思表示錯(cuò)誤制度的構(gòu)建[J].法學(xué),2016(02):114-128.
[5] 韓世遠(yuǎn).重大誤解解釋論綱[J].中外法學(xué),2017,29(03):667-684.
[6] 孟晉. 重大誤解民事行為認(rèn)定研究[D].南京大學(xué),2012.
[7] 周紅高. 重大誤解制度的重構(gòu)[D].西南政法大學(xué),2016.
[8] 童蕾. 合同法中的錯(cuò)誤制度研究[D].復(fù)旦大學(xué),2013.
[9] 陳耀東,沈明焱.重大誤解制度“重大”之認(rèn)定[J].學(xué)術(shù)論壇,2018,41(04):143-152.
[10] 陳彥晶.重大誤解規(guī)則商事適用的限制[J].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22(01):144-157.
作者簡介:陳鍶鍶 ,女,1995年出生,出生于湖南省邵陽市新寧縣,湖南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槊裆谭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