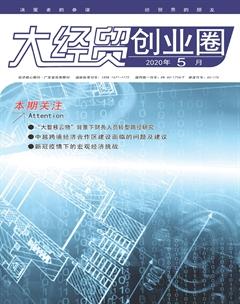論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素性質
【摘 要】 在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召開后,反腐倡廉的態勢持續高壓,職務犯罪的討論也一度成為熱點。“為他人謀取利益”要素在受賄罪中的性質定位問題學界一直有不同的爭論意見,主要形成了三種學說(實質上是兩張學說):客觀說、主觀說、新客觀說,而新客觀說筆者認為從實質上來說就是主觀說。三個學說在處理受賄罪中都存在缺陷,歸根結底,問題在于“是客觀要件還是主觀要件”這種形式化的提問方式,相比較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他人謀取利益”對受賄罪的法益侵害是否產生影響。在不同的受賄罪具體情形下,“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既可以屬于主觀違法要素,也可以屬于客觀違法要素,兩者之間是擇一的選擇關系。這就是混合違法要素說的理論依據。混合要素說不是憑空出世的,這種“混合”理論在刑法學界上具有理論先例,在立法上也可找到相關的法律規定佐證支持。
【關鍵詞】 客觀說 主觀說 承諾 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 混合要素說
一、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素性質的理論爭議
( 一) 客觀說及其問題
197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 185 條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并沒有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的表述方式正式出現在法律規定中是在《刑法》出現之后,是在 1988 年出臺的 《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 以下簡稱 《補充規定》)中出現的 。《補充規定》第 4 條第 1 款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補充規定》通過之后,學界就有了不同的觀點爭論。客觀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要素,所謂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受賄人為行賄人謀取某種非法的或者合法的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但是,如果公務人員收受了財物而實際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則不構成受賄罪。
在上述觀點看來,所謂 “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客觀上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而不要求具有為他人實際謀取了利益的結果。在1997 年《刑法》施行之后,為更好地適用《刑法》,就出臺了《刑法》“條文說明” ,在該《條文說明》中表述:“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受賄人利用職權為行賄人辦事,即進行 “權錢交易”,至于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條文中的 “利用職權為行賄人辦事”,要求至少已經開始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學界也有不少人堅持這樣的立場。這就是客觀說的觀點。
但是,客觀說存在諸多問題。( 1) 存在明顯的處罰漏洞,縮小受賄罪的范圍。比如,在行為人存在為他人謀利的意圖但并未開始謀利行為時,按此說難以入罪。( 2) 會造成處罰不均衡,難以接受。實務中可能存在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國家工作人員履行了法定義務和正當工作職責,從而在為他人謀取的是正當利益的情況下,認為是犯罪,而另一種情況是承諾為他人謀取該正當利益,卻并未實施謀利行為的,也就是并未履行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法定義務的場合,卻因欠缺 該“謀利行為”這一客觀要素而無法認定為受賄罪,顯然令人難以接受。( 3) 與犯罪既遂的刑法原理不符。在實務中,通常會有這種情況,國家工作人員在收受賄賂后,尚未實施或者不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行為的情況下,根據客觀說,犯罪已經既遂,但因沒有實施謀利行為還沒有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也就是出現了沒有完全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構成了犯罪,而且成立了犯罪既遂,這顯然違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論。
( 二) 主觀說及其缺陷
主觀要件說觀點認為: “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貨幣與權力互相交換達成的一種默契。就行賄人來說,是對受賄人的一種要求; 就受賄人來說,是對行賄人的一種許諾或答應。因此,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受賄人的一種心理狀態,屬于主觀要件的范疇。”主觀說主要存在如下問題:(1)在事后受賄的場合,難以入罪。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履行完畢某職務行為 ,而該職務行為正好為行賄人謀取了正當或不正當利益 ,他人事后為表示感謝贈送財物而國家工作人員予以收受的,應當可認定為受賄罪。可是,不管是在實施職務行為之后收受他人財物時,還是在收受財物之前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實施的職務行為之時,該國家工作人員具有 “為他人謀取利益” 的 “主觀意圖”都難以論證。同時,特別是在正當履行職務行為而客觀上正好為他人謀取到了利益的情況下,該國家工作人員更加不會預見到受益方將會贈送財物給自己。所以事后受賄的場合,主觀意圖不明顯,按該說難以入罪。(2)在虛假承諾的場合可能會造成處罰漏洞和不均衡。該說認為 “為他人謀取利益”體現為一種主觀上的謀利意圖即可。可是,“意圖”的字面意思是 “希望達到某種目的的打算”,行為人是有主觀上的“希望”存在的,但是在虛假地承諾為他人謀利的場合,由于并不存在行為人主觀上的“希望”也就是所謂的 “意圖”,也就會否定“為他人謀取利益”,按該說就不能構成受賄罪。但是,存在真實謀利意圖的場合認為是存在“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情節而在虛假承諾的場合卻否定這一點進而不構成犯罪,顯然這既是處罰的漏洞,也是一種處罰的不均衡。
二、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素性質之我見
( 一) 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稱為 “主觀要素”僅是底線宣示
學說上認為 “為他人謀取利益”是被動型受賄罪的主觀要件這僅僅是一個最低要求而已,這種理解側重點在于 “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至少需要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主觀心理活動,也就是只要達到了“同意”為他人謀取利益之程度就夠了,這只是一種底線要求,那么這種“同意”謀利的主觀心理是完全可以體現為其外化的外部行為的。不過,這與綁架罪中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這一主觀要素是有區別的,因為綁架罪中這一要素被法條明確規定為主觀要素,而受賄罪中的 “為他人謀取利益”要素并未規定為是主觀要素,而在實務上,這一要素既可能表現為客觀行為也可能體現為主觀心理。在國家工作人員已經開始為他人謀取利益甚至已經謀取到利益時, “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為客觀要件; 而不論是行為人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明示承諾)還是在對他人的謀利請求不予拒絕(默示承諾)等情況,都應當認定為 “同意”為他人謀取利益,從而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的主觀要素。
特別是在事后受賄的場合,“為他人謀取利益”更是一種純粹的客觀要素,完全脫離了主觀要素,這明顯已經不僅僅只是主觀說所理解的心理活動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因此,主觀要素層面上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一個最基本的“底線要求”,這種 “底線宣示”只具有形式化意義。
另外,在主觀說的用詞上筆者認為應再斟酌。由于收受行賄人財物后 “虛假承諾”為他人謀利者也應納入受賄罪處罰范圍,而主觀說即 “意圖謀利說”在此問題上存在會導致處罰漏洞的缺陷,所以,當 “為他人謀取利益”體現為主觀要件時,不應描述為 “意圖”,而應定義為 “同意”為他人謀取利益,才能更好的將虛假承諾 ( 虛假同意) 場合納入進受賄罪的處罰范圍之內。因為“意圖”有“想要達到某種目的的意思”,從其字面的意義來說,“意圖”的目的性強于 “同意”,而“同意”內涵而較為中性,從而,虛假的內容更容易可以涵蓋進 “同意” 。因此,筆者認為放棄常用的 “意圖”用法而改稱 “同意”更為可取。
( 二) 混合要素說理論
被動收受型受賄罪中的 “為他人謀取利益”,根據受賄罪中的具體情形,這一要件既可以表現為客觀要素也可以表現為主觀要素,這兩者之間是擇一的選擇性關系,所以合稱為 “混合要素”。主觀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不過是主觀意圖之外部體現。可是,這一觀點值得商榷: 客觀上的謀利行為與主觀上的謀利意愿畢竟不同,某物的 “體現”也并不等于就是某物本身。而且,更典型的是,在事后受賄中,完全可能存在著客觀上實施了為他人謀利的行為,但主觀上卻欠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同意或意圖,此時認為該謀利行為是謀利意圖的外部體現是顯然不恰當的。
“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實踐中一般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1) 典型受賄的情況,也就是國家工作人員既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意思,也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客觀行為。這是客觀說所討論的場合。(2) 默契型受賄的場合,主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 ( 真實或虛假的) 同意而客觀上欠缺具體的謀利行為,這是主觀說討論的場合。雖然在實務上,對這種情況不一定會進入法律程序進行處理,但這種行為確實對法益造成了侵害,那么確實具有處理的必要。但是客觀說在對這種情況進行處理時會遇到困難,但是混合要素說就可以和主觀說一樣,對這種情況的處罰進行順利論證。(3) 事后受賄的場合,客觀上雖然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但主觀上卻并不一定有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內心意思。如果認為 “為他人謀取利益”是主觀要素,那么在這種事后受賄的場合要說明國家工作人員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心態是較為困難的; 但是如果認為該要素屬于 “混合”要素,那么在這種事后受賄的情況下體現為純粹客觀要素,那么就比較好解決這種困擾了。
筆者所說的 “混合”,并不是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在同一受賄犯罪中既是主觀要件又是客觀要件,這兩者之間是擇一的選擇關系。也就是在不同受賄情形下(比如:默契受賄、被動型受賄、事后受賄等)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情況分別認定為主觀要素或客觀要素其中一種。本文的主張類似于所謂 “主客觀擇一說”,但是,“主客觀擇一說”的表述有一定的風險,也就是在被動受賄的場合,會被誤認為不必區分受賄罪的具體情形,謀利行為或者謀利心態具備其一即可的,所以該名稱不是很合適,還是將此種主張命名為 “混合要素說”較為妥帖。
(三)混合要素說的先例和立法佐證
混合要素說在理論主張上存在先例可循。比如,對于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刑法學界認為這既可以由故意構成,也可以由過失構成,為了更好的理解這一情形就提出了“復合罪過”的概念。這里的 “復合罪過”,與本文提出的 “混合要素”有相似之處,或者也可以說,“混合要素說”的提出,受 到了“復合罪過說”的影響和啟發。
混合要素說可以從我國的刑法規定中找到證明。在刑法總則中,我國刑法第 15 條所規定的過失,應該理解為 是一種“混合的要件”:一分為二的來看,在有過于自信的過失的情形下,這個過失屬于主觀要件,需受到責難的是 “ 輕信能夠避免的主觀心態”; 而在疏忽大意的過失的情形下,需受到責難的,是“沒有預見”,而這個沒有預見應當理解為是一種體現為客觀要素的客觀事實。因此,在兩種不同的過失下,“犯罪過失”既可能是主觀性質的,也可能是客觀性質的,這也就可以理解為 是一種“混合”的罪過形式。
混合要素說還可從刑法對其他犯罪的規定中找到支持依據。比如,我國刑法第389 條對行賄罪的規定。在此條文中,“為謀取不正當禮儀”應當認為是主觀違法要素。但是,在事前行為人并未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形成不法約定,國家工作人員違背職務為行為人謀取到不正當利益之后,行為人為表示感謝而給予對方財物時,即所謂的事后行賄的場合,為了避免處罰漏洞和處罰不均衡,仍應承認此時屬于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實際上,對行賄罪法律規定的此種理解與受賄罪理解中的“混合要素說”的觀點是很相類似的。
以上是在對與賄賂類有關的犯罪中為混合要素說找到的解釋依據,其實即使在與受賄類犯罪沒有關系的其他犯罪中,也有“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擇一選擇的混合”的情形。比如,刑法第 111 條規定的 “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該要素對于竊取、刺探、收買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行為來說,屬于主觀要素; 而對于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行為來說,則屬于客觀要素。這些法律規定的存在也為混合要素說的理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四、混合要素說能在法條主義的前提下為嚴密受賄罪入口作出實質性貢獻
在目前學界討論中,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持應該取消受賄罪中 “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的規定的觀點。不過,筆者認為,這是沒有對該要件進行深入認識的結果,沒有建立在嚴謹思考的基礎之上所得出的結論,是過于草率的。在被動型受賄等場合,“為他人謀取利益”體現為主觀違法要素; 在事后受賄的場合,該要素則體現為客觀違法要素。這就是本文所主張的混合違法要素說的“混合”的意義。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結論,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對于連接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職務行為與其所收受的財物之間的對價關系、說明受賄罪須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法益造成實際侵害的角度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這一要件還具有重要的政策價值,區分黨紀和國法的調整范圍,以黨紀、政紀等處理那些單純受賄等情形,而在 “權錢交易”的情況下再動用刑法。在這樣的總體情勢下,尤其是我國十八大、十九大以來持續高壓的反腐態勢下,要充分考量高壓反腐的趨勢和大局,在適用解釋上對 “為他人謀取利益”采取相對寬松的態度,有助于盡可能嚴密受賄罪的刑事法網。
【參考文獻】
[1] 付立慶.《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體系地位:混合違法要素說的提倡》[J].《法學家》.2017.1(3):113-130
[2] 吳杰.《受賄罪司法認定與立法完善若干問題探討》.廈門大學.2002年
[3] 蘇汶琪.《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探析》.《湖北警官學院》.2012(8):80-82
[4] 李邦友,黃悅.《受賄罪法益新論——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切入點》.《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6(2):274-279
[5] 薛國駿.《腐敗及其對策研究》.蘇州大學.2002年
[6] 張明楷.《論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J].《政法論壇》.2004(05)
[7] 張明楷.《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中國紀檢監察報》2009.10 .9第004 版
[8] 趙煜.《受賄認定疑難問題及立法完善》.《法治研究》.2014(12):12-17
[9] 孫鶴鳴.《海峽兩岸賄賂犯罪比較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
[10] 賈茜.《關于賄賂犯罪中利益要件的思考》.《法制與社會》.2009(30):381-382
[11] 胡敏.《論受賄罪的主觀超過要素》.《河北法學》.2009.27(1):192-196
作者簡介:蘭浪(1998-),男,漢族,湖南益陽。碩士研究生,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