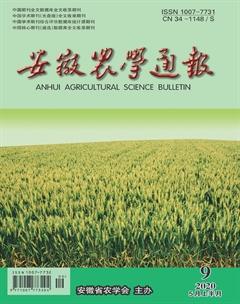典型草原牧區道路時空變化特征分析
張陽 賽西雅拉圖 其力木格



摘 要:以阿巴嘎旗那仁寶拉格蘇木為研究對象,通過查閱相關資料以及遙感圖像解譯等方法,研究典型草原牧區道路時空變化特征。結果表明:(1)2009—2017年,研究區內一、二級公路的變化趨勢不顯著,道路的增長主要體現在三級公路的增長上;(2)從2009—2017年間一級路與二級路、二級路與三級路的重心距離均呈縮小現象,說明下級道路的擴張以在上級道路附近為主;(3)研究區新增道路及人口數主要分布在東北部,并且相對集中,居民點的增加與擴張,對道路的位置和數量變化也有較大關系;(4)研究區草原道路的時空變化特征與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及牧戶的生產生活等人文因素息息相關,其中人文因素占據主要作用。
關鍵詞:牧區道路;時空變化特征;典型草原
中圖分類號 S8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7731(2020)09-0082-06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Roads in Typical Grassland Pastoral Areas
Zhang Yang et al.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tific,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e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Narenbaolage Sumu in Abaga Flag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typical grassland pastoral roads through the ways of consulting relevant notification materials and interprets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e conclusions showed that:(1)From 2009 to 2017,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roads in the study area wa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growth of roads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growth of third grade roads; (2)From 2009 to 2017,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roads,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roads, the distance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grade roads was decreasing, indicating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lower roads was mainly near the superior roads; (3) The newly added roads and population in the study area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and we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 increase and expans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the location and quantity of roads were also greatly related; (4)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road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altitude and slope, as well as human factors such as production and life of herders, among which human factors play a major role.
Key words: Pastoral Road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Typital Grassland
道路作為人類活動強烈的區域,道路沿線土壤及植被的退化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地受到學者們的關注[1-3]。然而,由于對道路引起草原直接和間接退化機理的系統研究不足,道路造成草原生態破壞的恢復機制尚不明確,加之道路對生態環境的各種影響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滯后性[4],往往容易被人們所忽視,近年來牧區道路的發展引起的草原退化有加速發展之勢。中科院研究表明10%的草場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道路侵蝕破壞,朱震達等的研究指出,機動車輛任意行駛引起的草原沙漠化可達各種人為因素沙漠化總面積的10%~20%[5]。內蒙古自治區土地面積1.183×107km2,在廣闊的草原牧區,遍地是草原道路(約4×105km)[6],既影響了牧區交通發展建設,又破壞了草原生態環境。
阿巴嘎旗隸屬于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是我國典型的草原牧區旗,是歐亞草原區蒙古高原地帶性典型草原的組成部分,半個世紀前曾被公認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保持典型草原原生植被最完好的草原地帶之一。然而,近年來阿巴嘎旗草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退化現象[7-9]。2017年6月,研究團隊在阿巴嘎旗那仁寶拉格蘇木野外調研時發現在草原上除主干道外,很多地方都看到大量的小路、便道存在,而且四通八達,少的有2~3車道并行,多的6~7車道并行,甚至超過20條車道并行,寬度窄的3~5m,寬的能達到40~50m,很少有1條行車道的。車輛隨意行駛、變道,在廣大牧區形成眾多自然路,甚至引起草地資源荒漠化,景象令人觸目驚心。
為此,筆者以那仁寶拉格蘇木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對蘇木內道路的時空特征演變及成因機制,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那仁寶拉格蘇木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西北部,是我國典型的草原蘇木,是蒙古高原地帶性典型草原的組成部分。蘇木人民政府駐查干敖包,距新浩特117km,那仁寶拉格蘇木位于東經113°28′~114°06′,北緯44°10′~44°47′(圖1)。蘇木人口密度為牧戶4.4戶/km2。該區域的交通道路包括各等級公路和車輛長期碾軋形成的便道。由于各牧戶間相互往來,在蘇木與嘎查之間、嘎查與嘎查間,甚至是牧戶與牧戶之間逐漸地形成一條條草原自然路,這些土路除少數被利用整修為公路外,其余遍布蘇木境內,形成四通八達的不規范土路網絡,極大地破壞了沿線草地資源。
為便于分析研究那仁寶拉格蘇木道路發展變化,在野外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結合研究區道路本身特點,本文將研究區道路劃分為3個等級:一級路,指路面寬度達到6m,通行所有機動車輛的柏油路;二級路,指除一級路外其他所有硬質路,路面寬度在3.5~6.0m之間;三級路,指人、畜、車輛長期碾軋、踐踏形成的自然路,包括各種土路小道、便道,牧道,路面寬度常在0.5~3.5m之間,個別路段寬度可達近10m。
研究區內一級路主要由縣道和那仁蘇木主街構成,縣道X920,由那仁蘇木人民政府駐地查干敖包向東南方向延伸,出蘇木轄區后在別力古臺鎮與省道S101匯合,匯合后借助省道S101向東可達阿巴嘎旗、錫林浩特市,向西可達蘇尼特左旗。另一條是縣道X923,由那仁蘇木人民政府駐地查干敖包向東北方向延伸到巴彥圖嘎蘇木。縣道X920、X923是那仁寶拉格蘇木與外界溝通交流的主要通道,承擔著保障那仁蘇木農畜產品等生產生活物資運輸暢通的責任。研究區內二級路路面寬度在3.5~6.0m之間,路面材質以碎石、水泥為主,是蘇木與嘎查之間、嘎查與嘎查之間連接的主要通道。二級路的形成主要是政府在原自然路基礎上,裁彎取直、填低削高建設而成的。研究區三級路眾多,其路面寬度多數在0.5~3.5m之間,具有點多、線長、面廣的特點。
2 數據來源與方法
2.1 道路影像 2009年道路影像下載于91衛圖(www.91weitu.com)。首先設定影像下載區域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那仁寶拉格蘇木,其次切換地圖選擇Arc gis軟件在線—影像(無偏移),最后設定影像級別第17級。2017年道路影像取自于阿巴嘎旗政府相關部門。
2.2 TM影像 本文在研究分析那仁寶拉格蘇木草原道路變化的過程中,所用NDVI數據為2009年9月23日和2017年9月7日2期Landsat TM衛星數據產品(帶號125/29和126/29)。每年兩景影像,為最大程度地排除影響因素,文中主要選取7—9月的植被。數據下載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http://www.gscloud.cn)。
2.3 研究方法 通過對內蒙古阿巴嘎旗那仁寶拉格蘇木2009年、2017年2期衛星遙感數據進行處理,首先獲取到研究區那仁寶拉格蘇木2009年和2017年的遙感影像數據;其次通過Arc gis軟件對衛星遙感數據進行解譯,得到研究區道路分布圖、居民點分布圖、水系分布圖、NDVI圖等相關數據信息;最后將影像疊加那仁寶拉格蘇木高程圖,得到那仁寶拉格蘇木2期綜合影像。
研究區那仁寶拉格蘇木是我國典型的草原區,較東部平原地區相比,具有人口稀少、居民點分散的特點,且草原地區建筑物較少干擾因素少,交通道路、居民點、河流、湖泊在影像上清晰易于識別。因此,本研究直接采用在遙感影像上目視解譯的方法,賦予道路線的特征,運用GIS軟件統計分析相關道路數據信息并標注那仁寶拉格蘇木交通道路、居民點、河流、湖泊的空間位置。
3 牧區道路時空變化特征
3.1 2009—2017年草原道路長度及密度變化特征 道路的形成與發展受眾多要素的綜合影響,為此,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中道路會呈現不同的形態。對牧區道路時間的縱向研究有利于道路變化趨勢的掌握。
3.1.1 長度 通過相關權威統計資料,了解到研究區(那仁寶拉格蘇木)2009年內共有交通道路4449.16km,其中一級路79.62km,占道路總長度1.79%;二級路315.53km,占道路總長度7.09%;三級路4054.01km,占道路總長度91.12%。2017年研究區共有道路4694.53km,其中一級路79.62km,占道路總長1.7%;二級路349.12km,占道路總長7.44%;三級路4265.79km,占道路總長90.87%。2017年較2009年相比,道路總長增加245.37km,增長5.51%,其中一級路長度未發生變化,增長為0,表明2009—2017年,研究區域內一級路沒有發生變化,保持穩定狀態;二級路長度增加33.59km,增長10.64%,變化主要表現在那仁寶拉格至都新高畢嘎查段公路,該段道路于2012年經錫林郭勒盟交通運輸局批準立項,同年7月開工并于當年完成,該段道路主要是在原自然路基礎上,經過裁彎取直、填低削高修建而成,路面采用水泥混凝土材質,路面寬度為3.5m;三級路長度增加211.78km,增長5.22%,三級路的變化主要是指自然路、牧道變化,且三級路廣散分布于研究區內,道路短小、零散(圖2)。
3.1.2 密度 2009—2017年蘇木轄區面積未發生變化,均為5032.65km2。通過計算得知2009年蘇木內道路綜合密度為0.88km/km2,其中一級路密度為0.016km/km2、二級路密度為0.063km/km2、三級路密度為0.806km/km2。2017年蘇木道路綜合密度為0.93km/km2,具體占比:一級路密度為0.016km/km2、二級路密度為0.069km/km2、三級路密度為0.848km/km2。近年來一、二級公路的變化較為穩定,增加趨勢不顯著(增長率趨近于0),道路密度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三級公路的數量上,其中三級公路道路增長了0.042km/km2,增長比率為5.21%(圖3)。
3.1.3 道路總體狀況 研究區域是典型草原地區,地勢平緩,行車障礙少,無論是嘎查還是牧戶居民點都具有分布廣、居住散的特點。同時嘎查內牧戶草場面積較大,戶均人口數量較少,在管理利用草場時,為節約時間,提升效率,因拉水照看羊群等因素導致牧戶對車輛的使用需求逐步上升。而車輛長時間在草原上行駛碾壓形成了大量的自然路(即三級路),此外,那仁寶拉格蘇木大部分的嘎查間、牧戶點之間道路連接由三級路承擔。部分自然路經過車輛長期碾壓后,形成10~15cm的車轍,影響車輛通過被廢棄使用,此時意味著新的自然路即將形成,過往車輛在廢棄路旁邊繼續行駛通過,碾壓形成新的自然路,這也是造成三級路眾多、廣泛分散的一大因素。同時三級道路還受到相關政策的影響,2017年內蒙古自治區“十個全覆蓋”項目對道路要“村村通”、“戶戶通”的要求,也是研究區內三級道路增加的一個影響因素。而一、二級公路的變化多數受政府的相關政策影響,蘇木內的主要公路都已經硬化到位,交通網絡體系也較為成熟,為此一、二級道路的增加趨勢不太明顯。
3.2 那仁蘇木道路空間變化特征 道路的空間變化受到地形、地勢、人為改造利用等多因素影響。對道路的空間變化研究有利于其空間演變特征及驅動因素的了解。
3.2.1 道路分布方位變化 利用ArcGIS 10.2下的標準差橢圓工具,分別測定研究區兩期道路分布的方向性,根據橢圓長短軸指向性分析道路、居民點密集區,并依此進一步分析。2009—2017年間,道路方位中心向東移動0.14km,向北移動1.08km,并且橢圓的長軸和短軸均有縮小,旋轉角度放大1.71°,說明研究區新增道路主要分布在東北部,并且相對集中(表1)。
根據實際考察,研究區道路增加主要分布在那仁寶拉格蘇木至原青格勒寶拉格蘇木政府駐地(2006年該蘇木并入那仁寶拉格蘇木)、原青格勒寶拉格蘇木政府駐地至阿日寶拉格嘎查、買仁圖音呼都嘎、哈布其勒郭等區域,增加的道路主要以三級路為主即自然路、土路居多(圖4)。
3.2.2 上下級間道路空間分布變化 通過獲取3種不同級別道路的重心,分析2009—2017年上下級道路重心的距離變化。2009年一級路與二級路重心距離為140880m,二級路與三級路重心距離為12622m;2017年一級路與二級路重心距離為105440m,二級路與三級路重心距離為10596m(圖5)。研究表明從2009—2017年間一級路與二級路、二級路與三級路的重心距離均呈縮小現象,說明下級道路的擴張以在上級道路附近為主,這一點與野外實地考察結果一致,當高等級道路在修建或因其他因素無法通行使用時,附近往往會形成與主路平行的數條低等級道路。
3.2.3 道路與居民點位置變化 通過對2009年和2017年2年的居民點密度與道路密度進行分析,發現居民點核密度變化較明顯的區域位于研究區圖6中的I和II 2個區域。從圖6可以看出,I和II 2個區域的居民點核密度從2009—2017年有明顯增加現象,與此同時,道路密度在這2個區域也同樣有增加現象。牧戶點數量的增加、牧戶間的交流聯系、牧戶外出至嘎查或蘇木(牧戶至主路間的新路形成)、牧戶家至草場的道路(均為三級)均有需求,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下導致三級道路的數量會有大幅度上升趨勢。這與之前的牧戶2009—2017年間三級道路增加明顯的研究結論相一致。綜上可見,居民點的增加與擴張,對道路的位置和數量變化也有較大關系。
4 影響道路的因素
4.1 海拔 對各海拔帶內2009年和2017年交通道路密度均值進行計算和統計,分析結果如下。2009年交通道路密度與海拔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和線性關系(圖7),其線性回歸方程為:[Y=0.0000009X-0.0103(R2=0.2827)],式中,Y為交通道路密度參數,X為海拔高度參數。而2017年交通道路密度與海拔有很好的相關性和線性關系(圖8),其線性回歸方程為:[Y=0.00001X-0.0129(R2=0.6669)],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式中,Y為交通道路密度,X為海拔高度。
經過對交通道路密度變化與海拔的相關分析,不難看出,此種變化趨勢與居民點密度變化很相似,同樣都是向高海拔地區發展(圖9)。隨著海拔升高,道路密度增長比重加大,海拔越高的區域道路密度增長越快。于是,可以推斷交通道路的發展方向也是由低海拔地區向高海拔地區擴展,且增長迅速,同樣具有打破海拔因子限制的趨勢。
此種結果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該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由于該區域低海拔地區便于放牧且地表水資源豐富利于定居,所以低海拔平坦地區屬于干擾強烈的地區,由此造成的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和草場退化導致產草量降低而不適宜畜牧業發展,人為活動的區域向生態環境和草地質量較好的高海拔地區轉移以利于牲畜采食。但是此種轉移必然會將干擾延伸,從而導致高海拔地區生態環境的破壞。
4.2 坡度 在對坡度因子與交通道路分布的相關分析中,2個年度的數據分析結果均顯示交通道路密度在各坡度水平上分布均具有隨坡度增加道路密度遞增的特點,主要是因為三級道路較多地分布在坡度較大地區,但坡度范圍很小,主要分布在7°~8°之間,說明該地區地勢相對平坦,坡度對道路影響相對較小。但二者的相關性較弱(R2=0.1324),且在顯著性檢驗上未通過(圖10、11)。
此外,通過相關性分析,2009—2017年間交通道路密度的變化與坡度因子基本呈現出不相關關系(R2=0.0002),回歸方程為:[Y=0.00001X+0.0003(R2=0.0002)],式中,Y為交通道路密度,X為坡度(圖12)。
4.3 人文影響因素 通過對蘇木內阿拉坦陶高圖嘎查的牧戶訪談得知,嘎查內道路硬化主要從2015年開始,之前的道路都是以零星分散,各戶之間的來往交通極為不便。在道路硬化后,牧戶前往主道路間的常年規范小道開始形成,這在無形中增加了三級公路的長度。同時在道路路況變好的條件下,嘎查內牧戶同年開始買入小轎車等先進現代化交通工具用于牧戶間的溝通交流及往返旗縣。再加上家里用于放牧的摩托車、托草料及拉水的小卡車,甚至部分牧戶購置了打草機等大型農用車,家中機械在草地上行走的頻度和強度也在與日增加。同時政府的相關決策建議也會促進草原路的修建。綜上可見,人文因素是草原道路形成及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
5 結論
通過分析,研究最終得出如下結論:(1)2009—2017年,研究區內一、二級公路的變化趨勢不顯著,道路的增長主要體現在三級公路的增長上;(2)2009—2017年間,一級路與二級路、二級路與三級路的重心距離均呈縮小現象,說明下級道路的擴張以在上級道路附近為主;(3)研究區新增道路及人口數主要分布在東北部,并且相對集中,居民點的增加與擴張,對道路的位置和數量變化也有較大關系;(4)研究區草原道路的時空變化特征與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及牧戶的生產生活等人文因素息息相關,其中人文因素占據主要作用。
參考文獻
[1]胡晉茹,楊建英,趙強,等.公路建設的生態影響與生態公路建設[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6(12):144-147.
[2]溫瑀.生態脆弱區公路路域生態環境評價與綠化模式設計研究[D].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2013.
[3]關振寰.草地開墾及公路交通對青藏高原草地土壤退化的影響[D].蘭州:蘭州大學,2018.
[4]任誠.道路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研究[J].綠色科技,2013(12):180-181.
[5]朱震達,劉恕,邸醒民.中國的沙漠化及其治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33.
[6]王彥志,余秀峰,相東.牧區道路路面結構分析[J].公路交通科技,2006(03):48-50,56.
[7]羅培,賽西雅拉圖.基于草場生存評估模型的阿巴嘎旗北部牧戶草場退化現狀及原因分析[J].草原與草業,2019,31(03):27-32.
[8]羅培,敖敦格日樂,賽西雅拉圖,等.不同放牧方式對草場放牧壓力的影響研究——以綿羊群日活動軌跡為視角[J].安徽農學通報,2018,24(23):102-105.
[9]白麗艷.近十年來阿巴嘎旗北部克氏針茅草原群落動態分析[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2011.
(責編:王慧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