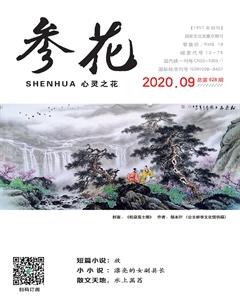從《流浪者之歌》中感悟“靜”
摘要:現(xiàn)代社會(huì),人們都忙碌于快節(jié)奏的工作、生活,很難靜心沉氣,找時(shí)間去讀一本書(shū)、看一部電影,或欣賞一部舞劇。舞劇《流浪者之歌》改編自赫曼·赫塞的同名小說(shuō),編導(dǎo)林懷民使用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手法,將觀眾帶入一個(gè)萬(wàn)籟俱寂的冥想世界,正如林懷民說(shuō)的那樣“在喧囂的時(shí)代里帶給觀眾安慰與寧?kù)o,那穿過(guò)菩提葉隙,斜陽(yáng)照射的陽(yáng)光”。
關(guān)鍵詞:《流浪者之歌》 林懷民 靜
林懷民曾說(shuō),如果這一生,能留下一部作品,他希望是《流浪者之歌》。起初,筆者并不理解與贊同,但這句話最終在多次欣賞這個(gè)作品之后得到了認(rèn)同。在《流浪者之歌》中,沒(méi)有激烈高昂的音樂(lè),也沒(méi)有緊張熱烈的情緒,甚至沒(méi)有極具戲劇性的劇情。林懷民選用了佐治亞民謠作為背景,刻畫(huà)了求道者、擺渡者、修行者安靜的內(nèi)心境況,與三者無(wú)聲相對(duì)應(yīng)的是稻米從天而降的“唦唦聲”,使得舞臺(tái)上有了“蟬噪林愈靜,鳥(niǎo)鳴山更幽”的境界。《流浪者之歌》被稱為是“云門(mén)舞集”中最安靜的舞蹈,它不再過(guò)度地強(qiáng)調(diào)編導(dǎo)技法的展現(xiàn),而是更加重視作品的思想內(nèi)核,與完成了從“外”到“內(nèi)”的轉(zhuǎn)變,表達(dá)了飽經(jīng)風(fēng)霜最終回歸平靜的一種態(tài)度。
一、《流浪者之歌》中的“靜”
《流浪者之歌》是一部考驗(yàn)觀眾心性的作品,在全場(chǎng)90分鐘的演出之中,沒(méi)有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沒(méi)有激昂的配樂(lè),沒(méi)有高超的動(dòng)作技巧。整部舞劇的氣氛莊嚴(yán)肅穆,像極了一場(chǎng)神圣的祭祀儀式,觀眾不由自主地安靜下來(lái),去聆聽(tīng)舞臺(tái)上的一切聲音,金色的稻米掉落地面唰唰的聲音,舞者喘息的聲音,一切在舞臺(tái)上真實(shí)存在的聲音。舞劇帶給了觀眾真正的“靜”,讓他們?cè)谛蕾p的過(guò)程中有時(shí)間去思考、去感悟。
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源于林懷民菩提樹(shù)下的頓悟,在他的眼中印度是個(gè)真實(shí)的地方,一切的生老病死都發(fā)生在身邊。恒河是印度人眼中神圣的象征,作為印度的母親河,每天承載著印度人的生死輪回。當(dāng)林懷民煎熬于對(duì)自我的懷疑否定時(shí),他去了佛祖得道的菩提樹(shù)下靜坐思考,突然一切變得安靜了。他將這種領(lǐng)悟帶回了臺(tái)灣,與云門(mén)舞集舞者的靜坐結(jié)合,創(chuàng)作出這份獨(dú)一無(wú)二的安靜。
二、《流浪者之歌》中的“鏡”
《流浪者之歌》成功之處在于它猶如鏡子一般,幻化萬(wàn)千又包羅萬(wàn)象。“一千個(gè)人眼中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觀眾所體會(huì)到的《流浪者之歌》中展現(xiàn)出的一切含義都源于自我感官賦予。作品中最大的道具是三噸的金色稻米,在舞劇之中稻米表現(xiàn)出猶如谷泉、谷河、谷丘、谷瀑、谷水及谷輪的自然化形態(tài),以及千溝萬(wàn)壑的地理環(huán)境,呈現(xiàn)出了壯觀而真實(shí)的畫(huà)面感。求道者在稻米中舉步維艱,他們緩慢前行,沒(méi)有高超的技巧,沒(méi)有優(yōu)美的動(dòng)作,似抽搐般的怪異舞姿,加上沉重的呼吸,這都是求道途中無(wú)盡苦難的表達(dá)。最后當(dāng)金黃色的稻米在舞臺(tái)后方如傾盆大雨般一瀉千里時(shí),求道者們以米洗身祈求得到光明,從而在痛苦之中得以解脫。稻米是萬(wàn)物的化身,又化身于世間萬(wàn)物,它作為道具渲染了環(huán)境背景,營(yíng)造了自然景象,仿佛帶有一種莊嚴(yán)的宗教氣息,塑造了獨(dú)特的人物形象,幫助情感關(guān)系更好傳達(dá)。雙手合十的僧人,自始至終任由清泉似的稻米從天而降卻一動(dòng)不動(dòng),他像是來(lái)自彼岸的觀察者,目睹眾生生命的起伏。在筆者眼中,他更似一種信仰,靜立在前方,任由你經(jīng)歷挫折艱難,但永遠(yuǎn)給你指引方向。看似所有形象出現(xiàn)在觀眾的眼前,實(shí)則所有意象都存在于觀眾的內(nèi)心。
舞劇的點(diǎn)睛之筆在于最后一部分《終結(jié)或起始》中的擺渡人,長(zhǎng)達(dá)15分鐘的表演,給予了觀眾無(wú)限的思考與遐想。但據(jù)說(shuō)這個(gè)精彩的部分最初并不是在編導(dǎo)的計(jì)劃之中,而是在演出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給觀眾留有反思的空間。擺渡人手拿犁耙,在專心致志一圈一圈地推擺著稻米,像是豐收之后晾曬果實(shí),又像是在講述世間萬(wàn)物的輪回,所有觀眾屏息凝氣,內(nèi)心明了卻又期待著奇跡的發(fā)生,似乎一眼萬(wàn)年,親眼見(jiàn)證著生命的輪回。
三、《流浪者之歌》中的“境”
赫曼·赫塞在小說(shuō)中寫(xiě)道:“什么是沉思冥想?什么是軀體舍棄?什么是持戒奉齋?什么是屏息呼吸?那是從‘自我中一種短暫的飛離、從生命的苦痛中一種臨時(shí)的逃避;那是對(duì)生命痛苦的一種緩和、對(duì)生命愚行的減輕。”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敘事性舞劇相比,《流浪者之歌》更像是一場(chǎng)心靈的洗禮。它向觀眾傳達(dá)了一種境界,傳達(dá)了對(duì)生命中痛苦的一種解脫,舞者們利用肢體動(dòng)作為觀眾呈現(xiàn)了一場(chǎng)求道之旅。流浪者的終點(diǎn)是什么——是忘我,是解脫,是擺脫苦難,是走向光明。我們不要像那群衣衫襤褸的男女一般在世俗的物質(zhì)洪流中徘徊,而是如那個(gè)修行者一般心如止水,去除浮躁,像那個(gè)耕耘者一樣通過(guò)踏實(shí)勞作,自我苦行,這才是我們得道的途徑,才能走向光明。正如林懷民在菩提樹(shù)下的感悟:“佛陀不是神,而是凡人,為了利益眾生,苦思出讓世人安身立命的生命哲學(xué)。”林懷民將西方現(xiàn)代舞與禪結(jié)合,用現(xiàn)代舞來(lái)表達(dá)禪,用禪訓(xùn)練舞者、引導(dǎo)觀眾,在日常訓(xùn)練中使用靜坐、冥想等方法,使禪可以真正地融入身體之中,又通過(guò)身體反映給觀眾,引導(dǎo)觀眾融入其中,最終達(dá)到一種身心合一、物我兩忘的境地。
四、結(jié)語(yǔ)
《流浪者之歌》帶領(lǐng)觀眾“由靜入鏡”,最終到達(dá)“境”。林懷民給觀眾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看似樸實(shí)無(wú)華,卻有著無(wú)限可能的空間。他善于將中西方文化進(jìn)行融合、創(chuàng)造,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被世界各地的觀眾接納、喜愛(ài),在舞蹈中尋找到自己的靈魂歸宿。走進(jìn)劇場(chǎng),放下陳念,用心去聆聽(tīng)屬于《流浪者之歌》的安靜,用心去感受舞蹈帶來(lái)的純粹。
參考文獻(xiàn):
[1]李沁憶.舞蹈中的觀“象”生“意”——以林懷民《流浪者之歌》為例[J].大眾文藝,2018(19):155.
[2]朱一峰.從呼吸出發(fā)——品《流浪者之歌》[J].戲劇之家,2018(06):113.
[3]趙海潮.賞析《流浪者之歌》——從身體語(yǔ)言和多模態(tài)話語(yǔ)媒介角度[J].海南廣播電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18(04):48-51.
[4]李洪墨,胡博.淺析現(xiàn)代舞《流浪者之歌》的表現(xiàn)內(nèi)容與藝術(shù)特征[J].戲劇之家,2015(21):121.
[5]陳依雯.欲望、生命與信仰——淺析現(xiàn)代舞《流浪者之歌》中的人文情懷[J].音樂(lè)時(shí)空,2015(19):32.
[6]歐建平,林懷民.關(guān)于《流浪者之歌》——?dú)W建平對(duì)話林懷民[J].藝術(shù)評(píng)論,2011(05):68-71.
[7]莊點(diǎn).談《流浪者之歌》中的禪意[J].成都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02):81-82.
(作者簡(jiǎn)介:趙宏文,女,碩士研究生在讀,青島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2018級(jí),研究方向:中國(guó)民族民間歌舞表演及教學(xué))(責(zé)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