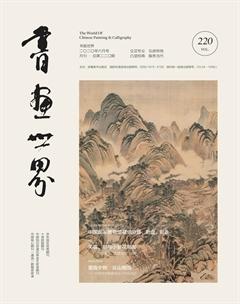由內(nèi)而外



就中國(guó)花烏畫(huà)的筆墨而言,當(dāng)今美術(shù)界存在著兩種帶有普遍性的偏頗認(rèn)識(shí):一種類(lèi)型是把筆墨僅僅視為寫(xiě)意畫(huà)的入門(mén)功夫,把筆墨錘煉和風(fēng)格創(chuàng)造截然分開(kāi),認(rèn)為一旦“學(xué)會(huì)”筆墨就不能再計(jì)較筆墨,否則必成“畫(huà)匠”無(wú)疑。另一種類(lèi)型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紀(jì)80年代引進(jìn)的西方美術(shù)思潮所引發(fā)的,認(rèn)為既然筆墨應(yīng)以表情達(dá)意為歸旨,既然寫(xiě)意畫(huà)作為一種藝術(shù)樣式須突出其創(chuàng)造性,既然寫(xiě)意要走向世界,與西方文化接軌,那么,傳統(tǒng)是必須打破甚至放棄的桎梏。在他們看來(lái),表現(xiàn)傳統(tǒng)審美理想的主要手段——筆墨,已不再是當(dāng)今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
筆者認(rèn)為,上述兩類(lèi)看法盡管有種種相左之處,但在根本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筆墨的內(nèi)涵以及筆墨在花烏畫(huà)藝術(shù)中的本體價(jià)值。前者因?yàn)檎J(rèn)識(shí)不到筆墨傳統(tǒng)的本體特征,不可能實(shí)現(xiàn)有價(jià)值的繼承;后者是由于背離了中國(guó)寫(xiě)意畫(huà)的歷史傳統(tǒng),無(wú)法進(jìn)行真正寫(xiě)意意義上的新探索和新突破。因此,花烏畫(huà)作為一門(mén)獨(dú)立的藝術(shù),其載體是筆墨,其手段是技法,這種技法的核心就是筆墨。它不是孤立于寫(xiě)意畫(huà)各種要素之外的一般性技法,而是貫穿于寫(xiě)意畫(huà)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之中的核心要素,是衡量花烏畫(huà)作品藝術(shù)水準(zhǔn)高下的重要尺度。除卻形象之外,筆墨自有獨(dú)立的審美價(jià)值。筆法研究在國(guó)畫(huà)理論研究范疇內(nèi)有其特殊的地位,特別是對(duì)基礎(chǔ)理論薄弱的當(dāng)代國(guó)畫(huà)界來(lái)說(shuō),這項(xiàng)課題顯得尤為重要。
分析古今筆墨研究的得失,是從事該課題的首要工作。
筆墨的闡述是古代畫(huà)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筆墨不但是古人繪畫(huà)實(shí)踐中主要的傳承對(duì)象,也是理論研究的首要內(nèi)容。古人對(duì)筆墨的研究言簡(jiǎn)意賅,舉其要,則有以下幾種:
一、對(duì)筆墨技法內(nèi)容的論述。這體現(xiàn)在對(duì)執(zhí)筆、運(yùn)筆的研究和書(shū)法緊密相連上。這在繪畫(huà)進(jìn)入自覺(jué)階段后即引起了畫(huà)家關(guān)注。關(guān)注執(zhí)筆法,歷來(lái)眾說(shuō)紛紜,各不相下,但都是圍繞如何更好地運(yùn)用毛筆而展開(kāi)研究討論的。古人對(duì)運(yùn)筆的要求大同小異。至于用筆法,它是筆墨的核心內(nèi)容,也是寫(xiě)意畫(huà)技法的關(guān)鍵。對(duì)此,古人在實(shí)踐上有精深的研究,在理論上有或詳或略種種不同形式的表述,而表述形式的非系統(tǒng)性是其基本特點(diǎn)。
二、對(duì)畫(huà)法、墨法、水法、色法審美內(nèi)涵的研究。這既有理論的闡述,也有感覺(jué)的描述。這方面研究在魏、晉南北朝即已達(dá)到很高程度,代表性著述有謝赫“六法論”,反映出古人在筆法運(yùn)用中對(duì)陰陽(yáng)宇宙意識(shí)和生命意識(shí)的體認(rèn)與追求。以后的研究基本在此范圍內(nèi)做不同角度的闡發(fā)與充實(shí),但很少有對(duì)其“所以然”的探討。
三、對(duì)筆法墨法源流的討論。古人通過(guò)長(zhǎng)期的繪畫(huà)實(shí)踐,經(jīng)過(guò)總結(jié)、充實(shí)、再總結(jié)的代代傳承,逐步獲得筆墨的技法內(nèi)容和審美意識(shí)的積淀,繪畫(huà)本體也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隨之完善、確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是筆墨傳承并銜接了歷史。歷代畫(huà)家因而常常做些推本溯源的討論工作,但因文獻(xiàn)資料的嚴(yán)重散失和實(shí)物材料的過(guò)于欠缺,論述中難免有主觀臆測(cè)之弊,往往帶有神秘化傾向。這在主觀上是由重感覺(jué)、輕實(shí)證的思維方式造成的。
四、對(duì)筆墨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對(duì)筆墨的審美價(jià)值和本體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在古代,常常隨古人對(duì)筆墨技法內(nèi)容認(rèn)識(shí)的不同而不同。有兩種基本看法:一種認(rèn)為筆墨是第一位的,形象居次要地位,這在寫(xiě)意花烏畫(huà)中占主流地位;另一種認(rèn)為形象是第一位的,筆墨居于從屬地位,持此見(jiàn)解者亦代不乏人,但影響遠(yuǎn)不及前者,雙方各有偏頗。
古人研究筆墨在方法論上采取的普遍方式,是對(duì)感覺(jué)的簡(jiǎn)潔描述和對(duì)比喻的巧妙運(yùn)用。其優(yōu)點(diǎn)是可以避免筆墨討論陷入機(jī)械化境地,有利于筆墨內(nèi)涵的深刻表達(dá);其不利處是接受者如果沒(méi)有達(dá)到能與論述者實(shí)踐、理論相溝通的水平,經(jīng)常會(huì)產(chǎn)生歧義。這兩種結(jié)果都不利于筆墨的有效傳承和進(jìn)一步充實(shí)。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藝術(shù)的豐富內(nèi)涵難以言盡。但傳統(tǒng)的感悟式點(diǎn)評(píng)研究方式,除了適用于相當(dāng)水平的畫(huà)家“對(duì)話”外,也不可避免地誘發(fā)出一些弊端:(一)實(shí)踐水平不到一定程度者,根本無(wú)法領(lǐng)會(huì)這些筆墨的真實(shí)內(nèi)容;
(二)忽視在筆墨理論上做宏觀的、歷史的把握。
清以后,隨著中西文化的兩次交匯、沖撞,筆墨研究相應(yīng)地呈現(xiàn)出一些不同于往日的特點(diǎn)——體現(xiàn)在畫(huà)家、理論家開(kāi)始對(duì)歷代所傳筆墨之“所以然”的追尋上。理論家們多借用西方美學(xué)成果甚至自然科學(xué)理論成果來(lái)剖析筆法的內(nèi)內(nèi)外外,確實(sh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jī)。但是,實(shí)踐專家雖然“知其然”,卻缺乏系統(tǒng)的方法論,筆墨研究在他們手中仍大體停留在明、清現(xiàn)代的理論水平上;理論家們又常不“知其然”,以致求其“所以然”時(shí)往往捉襟見(jiàn)肘,為有造詣的畫(huà)家所不屑一顧。實(shí)踐與理論的嚴(yán)重脫節(jié),是近代尤其是近些年來(lái)筆墨研究不能真正深入的根本原因。
為了準(zhǔn)確深入地認(rèn)識(shí)筆墨,對(duì)元明清乃至民國(guó)以來(lái)的筆墨研究成果做一梳理無(wú)疑是必要的。有突出性成就的筆墨與構(gòu)圖的,如潘天壽,構(gòu)圖善于造險(xiǎn)破險(xiǎn),李苦禪也是個(gè)構(gòu)圖好手;墨法與水法,如黃賓虹,詳細(xì)地歸納了墨法與水法,提出“平、留、圓、重、變”的筆法和漬墨法和水法;筆墨的轉(zhuǎn)換反映筆墨意象,如李苦禪、潘天壽等。
正是由于對(duì)筆墨在認(rèn)識(shí)上的不全面、在理論上的無(wú)系統(tǒng),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國(guó)畫(huà)理論界很不自信,時(shí)而糾纏于“具象”“抽象”等西方美學(xué)概念,時(shí)而糾纏于“傳統(tǒng)”“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問(wèn)題;沒(méi)有對(duì)筆墨進(jìn)行全面深入的理解,必然導(dǎo)致寫(xiě)意畫(huà)的沒(méi)落。
近代以來(lái),筆墨不斷變化,寫(xiě)意畫(huà)本體的生命力日漸孱弱。搬用西方美術(shù)觀念的種類(lèi)“繪畫(huà)”流派針對(duì)變種“病癥”,拿筆墨開(kāi)刀,確實(shí)事出有因,但因此而摒棄筆墨,則無(wú)異于將寫(xiě)意畫(huà)“斬草除根”了,因?yàn)檫@樣同樣違背了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所以,重新認(rèn)識(shí)筆墨,建立筆墨論,并以此為基礎(chǔ)重建寫(xiě)意畫(huà)本體,是當(dāng)代美術(shù)界最為迫切、最為重要的課題,關(guān)系著寫(xiě)意畫(huà)未來(lái)的命運(yùn)。如果能正確、全面地認(rèn)識(shí)筆墨,還它一個(gè)本來(lái)面目,那么,我們就為寫(xiě)意畫(huà)在將來(lái)的健康發(fā)展去掉了一個(gè)隱患;否則,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藝術(shù)品種,寫(xiě)意花烏畫(huà)完全有可能在今天中西文化激烈沖撞的大旋渦中,因我們這一代的不努力而出現(xiàn)異化,進(jìn)而走向消亡。
鑒于古今筆墨研究方法上的利弊,我認(rèn)為尤其要注重以下幾點(diǎn):
(一)在重視古今筆墨理論歸納整理的同時(shí),將這些理論與古今名作結(jié)合起來(lái)相互印證,由此推出結(jié)論。
(二)力求整體性、系統(tǒng)性、宏觀性,剖析筆墨,以利于深入把握筆墨的文化內(nèi)涵,而不把它僅僅視作一種低層次的技藝。
(三)綜合論證,重新確立筆墨在寫(xiě)意畫(huà)中的價(jià)值。
(四)論證筆墨應(yīng)與造化、心靈統(tǒng)一,提倡寫(xiě)生的重要性。
簡(jiǎn)言之,就是既要繼承傳統(tǒng)思維方式之長(zhǎng)處,又要吸收西方形式邏輯和實(shí)證主義研究思路的優(yōu)點(diǎn),盡量做到既有認(rèn)識(shí)的深度,又有論證的系統(tǒng)性。
約稿、責(zé)編:徐琳祺
喬妍芳 Qiao Yanfang
喬妍芳,2017年畢業(yè)于湖北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2019年考入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美術(shù)學(xué)系,攻讀花烏畫(huà)創(chuàng)作方向碩士學(xué)位,導(dǎo)師為劉波教授。現(xiàn)為邵陽(yáng)學(xué)院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