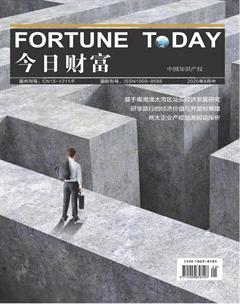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路徑研究
羅珈欣?常遠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對于推動灣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灣區的產業競爭力和整體經濟實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研究大灣區產業發展狀況的基礎上,探析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現實挑戰,從構建市場一體化和產業分工合作角度,探索出實現灣區協同發展應從凝聚合作共識,創新合作體制機制;發揮政府的協調功能;培育利益共享產業鏈,深化產業分工合作;加強科技創新能力,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等路徑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的協同發展。
一、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有助于進一步提升灣區經濟實力,促進灣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目前三地的產業合作與發展仍處于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尚未形成真正的協同發展模式。在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探析灣區在實現跨境跨區域的產業協同發展中遇到的現實挑戰,探索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路徑。本研究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合作體制機制,加強科技創新等方面實現市場一體化提供有效的參考價值,為各地政府制定產業協同發展政策提供依據,對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發展分析
(一)粵港澳三地產業結構分析
灣區內部產業結構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香港和澳門擁有先進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占比分別達93.1%和95.8%,處于服務經濟發展階段。珠三角九市中,除廣州、深圳與東莞的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以“三二一”模式發展外,其他城市仍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尚處在工業經濟與服務經濟混合發展的階段。
(二)粵港澳三地產業結構存在趨同現象
在CEPA框架推動下,珠三角積極推動產業轉型,產業結構逐漸與港澳趨同,日益發達的服務業對港澳服務業構成了挑戰,三地間利益格局出現分化,經貿關系由互補性的垂直分工逐步轉向同質化的競爭。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間的三次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均大于0.65,產業結構趨同度高。在珠三角九市內部,制造業相似系數處于較高水平,產業發展呈現同質化競爭。深圳與東莞、惠州、中山與珠海、佛山與中山之間的制造業相似系數均超過0.88。
(三)粵港澳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升級
近年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珠三角在全球產業鏈的競爭能力下降,面臨資源能源約束與生態環境壓力雙重難題,產業發展處于高速換擋期,亟需新動能來不斷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實力雄厚的港澳也面臨著經濟增長后勁不足、服務業發展模式單一,工業空心化等壓力。
三、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現實挑戰
(一)粵港澳三地的體制系統不同
在“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三種法律體系”的框架下,粵港澳三地需要克服體制不同帶來的跨境協調難題。第一,港澳與珠三角在經濟制度、政府體系、財政體系、生活習慣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致使灣區內人才、資金、信息、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二,三地的司法體制不對接。三地法律體系間的差距制約跨境合作中出現法律問題的解決。粵港澳三地在體制系統的差異形成了“玻璃門”,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嚴重影響產業融合與協同發展。
(二)行政區經濟限制市場一體化
粵港澳三地的體制不同制約了要素的流動,珠三角的行政區經濟也制約了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各自為營的珠三角內部經濟發展存在利益藩籬,導致區域產業結構性矛盾凸顯:一是區域間進行資源爭搶,導致資源耗散、資源配置效率低;二是追逐相似的有利于己的產業,導致重復建設與產業結構趨同。區域間的競爭形成了市場和行政壁壘,限制區域產業的空間布局和產業價值鏈的延伸。
(三)區域協同和管理體制機制滯后
粵港澳三地的體制不同與行政性經濟對灣區的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形成了屏障和阻隔,嚴重影響灣區的產業協同發展。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主要以黨政聯席會議的形式存在,對于經濟合作缺乏約束力。在制度層面上,灣區跨境協作的體制機制尚不健全。基于CEPA的合作制度在應用中存在“大門開,小門不開”的問題,缺乏實質性作用。區域經濟協同機制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產業經濟利益分享與補償機制不健全,行政區的競爭激勵缺乏制度的硬約束,產業合作缺少制度的保障,區域的分工和產業價值鏈的延伸難以實現。
四、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路徑研究
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協同發展要以產業鏈分工協作和轉型升級作為目標,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功能,在政策引導和創新驅動下,促進要素的快速流動和資源的高效優化配置,實現區域經濟整體效益最大化。
(一)創新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創建市場一體化
一體化市場有利于灣區經濟協同發展,而實現一體化發展的前提保障是構建有效的協調機制。
第一,凝聚合作共識。凝聚合作共識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前提。粵港澳三地要改變各自為營的發展觀念,從灣區整體經濟利益出發,突破利益藩籬,以增強灣區整體實力為目標,凝聚協同發展的合作共識。
第二,構建市場一體化制度。在“一國兩制”原則下,追求不同經濟制度的“求同存異”,加強市場規則對接以減小市場體制差異對要素自由流動的制約;積極探索三地在物流、資金、人員出入及貿易等方面的便捷性措施,加快要素流動速度;通過法律層面的制度協調灣區合作的難題,為市場一體化提供法律保障,降低要素流動成本。
第三,創新協調發展機制。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重視求同存異,科學探索協調發展新機制;構建粵港澳三地政府正面的溝通聯絡機制和對話框架,協調解決大灣區發展中遇到的重大難題。健全多渠道多層次制度化的合作協調機制和利益共享長效機制,兼顧平衡各方的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產業分工和產業價值鏈延伸。
(二)發揮政府的協調功能,加強政策引導作用
政策引導是保障協調機制實施的重要工具。充分發揮政府對區域產業發展的頂層設計和指揮作用,以產業政策為引導工具,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灣區產業協同發展。
各城市政府在已有整體產業布局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產業發展與優勢,制定符合灣區全局戰略的產業發展規劃,在發揮產業比較優勢同時避免過渡競爭;積極協調區域間的營商規則,通過市場規則對接構建一體化市場;建立區域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地方企業融入灣區的整體建設中;制定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創新研發,激發創新活力,支持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培育利益共享產業鏈,促進產業分工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要在遵循城市間協作的客觀規律下,發揮比較優勢,培育利益共享產業鏈,以實現灣區產業鏈高度整合和區域經濟深度融合。
第一,培育利益共享產業鏈。港澳先進的現代服務業能夠助力珠三角制造業轉型升級,同時珠三角發達的制造業可以彌補港澳“工業空心化”缺陷。加強粵港澳產業鏈全面融合發展,整合港澳技術創新資源,利用廣州、深圳創新研發的優勢,結合珠三角其他城市完備的制造業體系,加強產業對接協作。
第二,發揮核心城市引領作用。發揮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作用,建設具有高端高增值服務業的國際大都會;推進建設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打造經濟、文化多元發展的經濟交流基地;發揮廣州國家中心引領作用,增強國際貿易和科技教育中心功能,建設綜合性國際大都市;釋放深圳科技創新能力,打造全球產業創新中心的創意都市。
第三,珠三角其他城市實現錯位發展。珠江東岸(包括東莞、深圳等)要以高科技和新興產業為主創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制造產業集群;珠江西岸(包括佛山、中山、珠海等)以裝備制造業為核心打造技術密集型產業帶;惠州、江門、珠海側重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
(四)加強科技創新驅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創新驅動是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主線和重要路徑。積極推動港澳兩地融入創新體系中,打造開放互通的科技創新共同體,創建科技創新要素共享平臺,利用互通開放的國際平臺集聚高端國際創新資源。發揮創新極輻射功能,加快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探索有利于推進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的政策措施,通過降低三地就業門檻等方式促進人才流動,拓展人才創新創業空間。優化灣區創新發展環境,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和運用,推動三地在知識產權和專業人才培養等領域的合作。(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