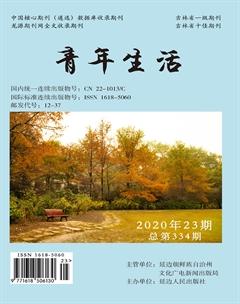淺析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判例制度
王健
摘要: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判例,是指在司法活動中產生,經過特殊程序認定,具有普遍約束力,能夠作為今后類似案件裁判的基礎的司法判決。但只要能夠滿足案件是在司法實踐中產生,并且對以后類似案件具有指導作用,即使該案例經過抽象化處理,也同樣可以認為是判例。判例作為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它植根于成文法、起著補充、修改、完善律文的作用,與成文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是審理案件、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是我國古代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章按照按照成文法和判例的關系變化以及判例制度的發展歷史梳理了我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判例制度。
關鍵詞:中國古代;判例;成文法
按照成文法和判例的關系變化以及判例制度的發展歷史,本文將中國古代判例制度分為了5個時期,即先秦時期、秦漢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和宋元明清時期。先秦時期沒有明確的判例法的記載,判例制度處于“萌芽期”;秦漢時期判例被大量應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判例的發展陷入停滯;隋唐時期,唐代官方明令禁止使用判例;宋元明清時期,判例制度再次發展,宋代官方認可判例,元代法典編纂中出現了判例,明清兩代形成了律例結合的立法模式。
一、先秦時期的判例制度
夏商兩代,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并未出現,也沒有明確的判例法的記載。此時的法律淵源主要是商王的命令和適合于奴隸主貴族統治的某些習慣。“禹刑”、“湯刑”即是夏商兩代在長期發展中逐步形成和不斷擴充的,其內容基本以習慣法為主。《尚書·盤庚》記載有“有咎比于罰”的字樣,說明當時司法實踐中已有類比先例的做法。西周初期沿用商朝的一些成事或習慣,史書載“陳時皋事,罰敝(比)殷彝”,“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此處的“殷彝”、“御事”指的就是判例。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的頒布和法家思想的崛起,成文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成文法的公布推動了法律的適用,也推動了判例的發展。荀子所說的:“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此處的“類”即司法審判中所遵守的判例和原則。《左傳》和《國語》中也多次記載了運用判例的事件。
二、秦漢時期的判例制度
在秦代,司法審判的成例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稱為“廷行事”。《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了秦代司法實踐中廣泛地實行援用“廷行事”或“行事”作為依據的制度。秦律中的《法律答問》也經常提到運用“廷行事”作為定罪量型的標準。這說明以例斷獄在秦代時已經為法律所肯定,司法判決的案例已經可以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文之外可資援引的審判依據了。
進入漢代,判例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漢代并未完全消失。如《漢書·翟方進傳》記載:“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另一方面,在漢代又出現了新的判例形式———決事比。所謂決事比,就是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取相同類似且已經判決的案例作為司法審判的依據。由于決事比可以補充法律規定之不足,為適用法律提供范例,因而被廣泛適用,《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武帝時“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東漢時比的數量又有發展并出現了根據司法實踐的經驗對決事比進行編纂刪定的判例集《辭訟比》。由于用比來審案既方便又靈活,為司法官廣泛采用。漢代判例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春秋決獄”。《春秋》是儒家經典,即根據《春秋》中的案例,來處理疑難案件,由漢代大儒董仲舒所開創,對漢代判例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后漢書·應劭傳》中載,膠東相董仲舒年老稱病還鄉,朝廷每當遇到疑難問題時,就派遣廷尉張湯親自去董仲舒家中征求意見。于是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在董仲舒之后,漢朝的司法官依然頻繁使用《春秋》之義來處理重大疑難案件。春秋決獄彌補了成文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規還不完善的情況下,依據儒家經義使案情得以妥善處理,同時儒家經義中的慎刑,德治和教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苛刑峻法的局面。但是,春秋決獄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經決獄中確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則,嚴重破壞了封建法制,甚至出現了“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的情況。其次,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對儒家經義的任意解釋使法律失去其應有的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再次,春秋決獄傳播了儒家思想中許多消極因素,進一步強化了對人們思想觀念的控制。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判例制度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判例發展陷入停滯期。一方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戰亂、動蕩的時期,長達近300年,朝代更替頻繁,戰爭不止,人們長期生活在流離和不安之中,無法過安定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法律很難真正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漢代以后,我國成文法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律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從“經學”中分離出來,法學理論及成文立法技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如《曹魏律》中的“八議”制度,《晉律》中的“準五服制罪”及《刑名》、《法例》篇的成型,禮法結合等等。儒家思想對法律的影響開始轉變,進一步抽象化,體現在思想指導上,而不是在具體案例中引用《春秋》。
四、隋唐時期的判例制度
隋唐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各項社會制度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和高度,也是古代法律成果最為輝煌的時期。隋朝的《開皇律》是一部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在篇章體例、基本內容各方面總結和發展了以往各個朝代的立法經驗,使封建法典趨于定型,確立了其后成文法律的范本。唐律繼承和總結了自秦漢以來尤其是隋朝封建法律的經驗和教訓,結合唐朝實際,進行了幾次規模宏大的立法活動,建立了形式多樣、內容完整的龐大的法律體系,達到了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顛峰。隋唐法律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非常完備,成文法的詳盡,使判例的適用空間減小,唐代不但嚴格規定了司法實踐中判例形成的規則,并且運用成文法規范判例的適用。《唐律·名例》“斷罪無正條”律文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唐代前期出現了《法例》,它是判例集合,在司法活動中用于指導案件審判。從唐高宗開始,唐代廢止了“例”,高宗從重視制定法的立場出發, 為防止判例對制定法造成沖擊禁止援用《法例》,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先是祥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為折衷。后高宗覽之,以為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制。并是武德之際,貞觀以來,或取定宸衷,參祥眾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為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但審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時有發生,所匯編的先例也是法學教育的重要內容。雖然唐高宗廢止了“例”,但在《唐律疏議》的“疏議”部分依然存在案例,這種案例與真實判例相差無幾,只不過內容語言經過提煉,形成了不同于判例本身的風格。這種“疏議”中的案例可以視為判例的“萌芽”。另外,《大中刑律統類》中的“敕 ”也可以視為典型判例。“敕”是古代皇帝針對具體案件進行的特別批示,一般只對個別案件有效,但附于律文之后,便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唐代還出現了判詞,一般是由官府出題,提出一個假設的案例,由應試者作判。這種判詞是虛構的,而且因為判斷它的優劣,主要是看詞章,所以判詞也主要是在運詞譴句、引經用典方面下工夫。因此,雖然也反映了當時士大夫對法律和社會問題的一些認識,但對當時社會的整體認識價值不是很高。
五、宋元明清時期的判例制度
宋代“編敕”是一項重要的立法活動,它是為了司法部門便于援用判例,每當經過一定時間,政府將皇帝對于案件批示及處理決定進行整理匯編。也就是定期對判例進行整理匯集,方便今后地方司法審判中進行援用。根據《宋史·刑法志》記載,“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可見“敕”是根據已發生的案例來為今后制定規范。同時又有,“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這說明宋代敕的地位得到明顯提升,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代替“律”。此外,宋代還存在另外一種重要的判例制度“斷例”,它也是對現有判例進行整理,經過朝廷篩選匯編形成判例集,來指導司法審判。“敕”和“斷例”作為宋代兩種判例,它們在司法過程中都發揮重要作用,但他們之間存在一定區別。首先,制定機關不同,“敕”由刑部負責整理皇帝發布的“敕書”,而“斷例”涉及范圍比較寬泛,不僅局限于刑事案件,因此一部分由大理寺整理,一部分有其他部門整理。再者,“敕”的來源單一,只能是由皇帝針對某一案件的批復和判決而產生,而“斷例”的來源可以由皇帝詔書產生,也可以由司法機關產生。宋代另一種類似判例性質的法律形式是“指揮”,經過整理的指揮正式與敕令并行。宋代例的泛濫造成了很多弊端,以至有些官吏“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唐代出現的判詞在宋代取得了進一步發展,一些士大夫將前代明敏斷獄、平反冤案的記載匯編成書,或將自己的判詞收集保存起來,甚至編入自己的文集,傳之后世,例如:《疑獄集》、《堂陰比事》、《折獄龜鑒》和《名公書判清明集》。這些文集收集分析了大量的破案故事,而不是判決書。另外,這些案例都是實案,大都從當時的筆記小說中采集而來,或者以歷史上或現實生活中的實案為原型而予以夸張添附,因而與唐代的純粹擬制的書判完全不同。在這些判例法作品中,經驗總結的成分居多,主要是向官吏提供偵察和審理案件的指導思想、方法和經驗,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先例,既有對破案經驗的總結,由判例所體現的法理和法律術語的解釋,還有對各個相關案例匯編后的分析比較,以及這些案例所反映出來的原理和學說的概括總結等等。
受宋代立法影響,元代司法實踐中也使用判例,《大元通制》的編纂體例中就有詔制、條格、斷例三類,在其中,條格、斷例占有絕對優勢,它將大量的唐、宋律文以“斷例”的形式為其所用。在元朝的法典中,判例的地位非常高,元代的《至正條格》計有3359條,其中“斷例”就有1059條。此外,元朝的各級官吏收集和編例的風氣也很盛行,以至出現了“有例可援,無法可守” 的狀況。
明清時期,律與例進行合編,共同適用,使中國古代判例法漸趨完善,日益發達。明朝的例源于判案依據的判例,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例不斷增加并且成為正文律的附注。明代的例有《充軍條例》、《贖罪事例》等,比較典型的是明孝宗十三年頒行的《問刑條例》,它與大明律并行,從此條例不再是權宜之法,而成了永久性法律。萬歷十三年《問刑條例》附于大明律后,形成了《大明律集解附》的體例,至此,例與律幾乎處于同等的地位。《明大誥》是明太祖朱元璋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件進行整理匯編而成的御制判例集,司法官吏斷案必須參照援引大誥中采編的判例為依據,其效力往往在律之上,被優先適用。
清繼承了明朝的律例。在律例關系上,明清經歷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過程,即律例各行到律例合編。清朝順治三年頒行的《大清律集附例》后附條例321條,雍正五年頒布的《大清律例》附條例1042條。清代的例分為條例、則例、事例等形式。條例是刑事單行法規,附于相關律條之后,如大清律中的條例。則例指某一政府部門或某項政務方面的單行法規匯編,由成例和事例構成,如《刑部現行則例》、《戶部則例》、《工部則例》。事例則指皇帝就某項事務發布“上諭”后經皇帝批準的政府部門提出的建議,它具有行政法規的性質,附于會典之后。在清代,判例的地位更加重要,發展更加成熟,顯示了中國判例制度的完善。主要體現為:第一,清代確立了因案生例制度,即針對具體的案件的審判而在判詞中附請定例。定例通過具體案例而產生,使判例的適用達到了規范化。第二,成案制度出現。成案是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形式,由各部或各省對某些典型案例的判決匯集而成。大清律對其適用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者為定例,一概嚴禁,勿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 但對那些具有長期適用性的成案可以由刑部詳加查核,上奏皇帝批準,著為定例后才可適用。第三,就律例而言,在法律適用中,例優先適用以“有例則不用律” 為原則。但這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律既多成虛文,而例遂俞滋繁碎”。第四,清代出臺了相應的立法來規范例的形成和適用。
結語
中國古代判例在總體上對律起輔助作用,效力低于成文法。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成文法的傳統。成文法的完備使判例生存的空間受到擠壓。戰國時期,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強調一切“皆有法式”。秦代的廷行事只能在律令無規定情況下適用。漢初仍主要沿用秦之舊制,定九章律,作為主要的律法;漢中期以后的決事比,春秋決獄也只能限于疑難案件而律無相應規定時。東漢、魏晉時期的“故事”亦是如此。唐代嚴格適用例,即“斷罪不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例只有經過中央批準以后,才可引用,并且在唐高宗時廢止了“例”。宋朝初年,太祖命令“凡斷獄本于律,律所不該,以敕、令、格、式定之。”神宗以后的以例破律到了明清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明清時律例合編,律與例并行,做到了以例輔律,此時的例已從判例上升為單行的成文法規。正式意義的成案(判例)適用必須是定例并且由刑部批準以后。總之,中國古代法制史是以國家制定法為主干的,判例法一直處于附屬性、輔助性的地位。
參考文獻
[1]蒲娜娜.判例法及中國“判例法”歷史考察[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04.
[2]陳堅綱.中國古代判例法研究[N].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4,3(51)
[3]余曉磊.唐宋時期判例研究[D].北京:青年政治學院,2015
[4]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及相關概念考論[N].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12
[5]楊思斌.中國古代判例制度的演變與基本特征[J].法學雜志,2008,2
[6]陳歡.中國古代判例制度的演變研究[J].法學之窗,2011,5:19
[7]葉林.判例制度簡論[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04.
[8]朱敏玲.中國古代判例法研究[J].法制與社會,2014,9(下):9-10
[9]蔣嘯.判例法研究[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