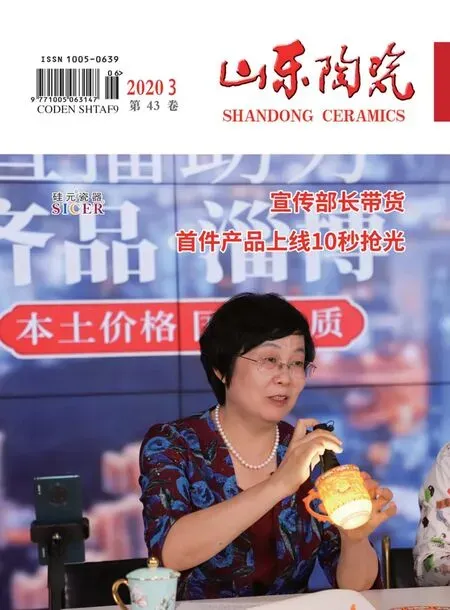“梅樁壺”的意境
王俊琴

圖1 梅樁壺
梅花在民間是傳春報喜的象征,歷代文人對梅花青睞有加,詠梅的詩詞文章數不勝數,紫砂梅樁壺借用了這種關于梅的象征,通過外形重塑,提供一種可以發自內心追逐的現實具象。對于梅樁壺的創作,不同的創作者心中有著不同的梅的形象,這種創造的實質其實是對內心的一次呈現,紫砂以自身優良的材質及可塑性,為制作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對內心的發掘造就了各種不同樣式的梅樁壺。
現代人便捷的生活得益于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僅有幾十年,上千年的文明歷程在短短的幾十年間驟然加速,當代的文藝創作領域也紛紛開啟了新時代的創新機制,紫砂壺藝由此迎來了又一個發展機遇。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乍一看跟慢節奏的古典飲茶文化格格不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驚訝的發現,長期的快節奏會使人疲憊,而文藝的生活環境能夠使人慢下來,獲得休憩。這種感受在紫砂藝術上表現的尤其明顯,紫砂壺與茶相伴,提供了一種近乎儀式性的飲茶生活,也為紫砂壺藝的創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圖1“梅樁壺”是一件傳統的紫砂花貨造型,臨摹自然生長的梅花樹,依據其形態塑其意境,將繁花與滄桑,歲月無情而又生生不息結合到一起,展現出梅花虬枝走揚、高貴冷艷、綿延存續、傲然挺立的形態。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在這把壺的主題制作方面,“梅花”確實是整體的裝飾核心,但卻并非這把壺最主要的表現方向,“梅花”是表象,是點綴而并非核心,制作這把壺要突出的在于“梅花”之“骨”,我們常說人有傲骨,仿若寒冬之梅,指的就是那種無畏的品質,所以花在外是為肉,身在內是為骨,整器的核心全在于對壺身的制作和塑造上。
從壺面來看,這把壺展現出的是一種生命的悠長氣息,將一種生的希望于枯榮滄桑的形體中膨脹開來,溝塹平滑,深淺有度,給人一種壺面仿佛是光滑的錯覺,而當實際觸摸上去就會發現,上下縱橫的溝壑,凸起的梅節,給人觸之生景的錯覺,仿佛眼前就浮現出樹表凹痕,梅枝斷裂的痕跡,在這里故意忽略掉梅樹本身的肌理,而用紫砂壺光滑的表面處理代替,但在壺面之上又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溝壑紋理以及樹節,不過分平滑,也不過分粗糙,處于兩者之間,通過傳統拍身筒與鏤捏相結合的方法,塑造出逼真立體的壺面效果,讓人觸景生情,感受到那種歷經歲月的無奈,但又宛若新生一般的振作。
壺面的處理讓人感受到梅花之骨所孕育的力度,所以在壺面之外、壺身之上,壺鈕、壺流、壺把就是包裹在骨骼之外的皮肉,擷取樹枝的不同造型特征,與壺身輝映,圍繞壺身這一主干生長衍化,將作品所孕育的情感基調整合了起來。壺鈕取一截梅花小枝,對于梅花的描述歷代文藝創作中都有所闡述,彎彎曲折的,嬌俏的呈一拱形立于壺蓋之上,且粗細分布符合自然生長的態勢,由粗變細,且于末梢處再延出新枝,新枝細小綴上梅花,這些就成為了點綴在壺蓋之上的梅花貼塑;壺把的塑造同樣也是如此,虬枝被形象地折成一個自然而然的彎把,恰到好處,便于提握,跟壺鈕所不同的是,壺把更為堅實有力,生長出來的梅花也就相應的更加豐盛。需要注意的是,壺鈕的枝干走向與壺把的走向要相互一致,因為在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長都有自身規律,通常一側的枝葉都會被動的追尋陽光呈現出統一的方向感,在這把壺上想要將梅花塑造的生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所以兩者的朝向是一致的。
對于壺流的處理,從壺身中部延伸出一根枝節,挺而向上跟壺鈕壺把的蜿蜒曲折不同,壺流的形體氣質延續了壺面的光潤和有力,幾乎可以將其視作壺身于一體,按接的處理讓兩者的銜接幾無痕跡,如果說梅花展現了自身的韌性,那么壺身與壺流所表現的就是內質的堅硬了,同時壺流的走向亦呈現出一種向上的姿態,這其中的表達相當容易讓人理解,那就是鼓勵人面對困難的時候樂觀向上。
紫砂形體的塑造需要扎實的工藝技巧以及合理的自然變化,紫砂梅樁壺的形體并非是憑空出現的,其各個部分都需要從大自然中的真實去提煉出來,這種提煉是一種有限的重復,即臨摹出外在的神韻,而將所要表達的觀點孕育在形體自身的變化當中,這樣既可以有生動的自然表現,也適當的展示了創作者所要傳遞的精神訊息,不拘泥于實際,又超脫于一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