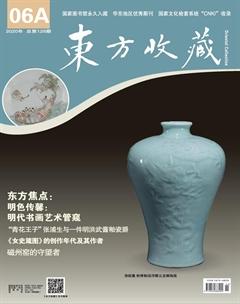盛唐光彩 海納百川
潘鈺


2007年,長沙博物館與寧鄉縣文管所進行了一次館際調撥,一件極其精美的國家一級文物——海獸葡萄紋銅鏡得以進入長沙博物館收藏。以此為契機,長沙博物館對該館藏所有銅鏡進行了第一次系統梳理,并編撰成書。本文作者因此對唐代葡萄鏡進行了初步的接觸和研究。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這面唐代孔雀葡萄紋銅鏡(圖1),出土于長沙寧鄉縣黃材鎮的唐墓,該面銅鏡直徑18、厚達1.6厘米,重708克。狻猊鈕,主題紋飾為以一飾細點紋之凸弦分割為內、外兩區。內區主題為圍繞狻猊之五只海馬,海馬造型生動活波,翹首張嘴、揚尾,以順時針方向排列,造型稍有不同,其間以葡萄紋填充。外區為鳥蝶,鳥雀形態多樣,計有八只,有作飛翔狀、有盤旋長尾如長綬鳥、有啄食葡萄狀,其間夾有蜂蝶五只,有作飛舞狀,亦有作停息草葉狀。蜂蝶間以葡萄、蔓枝、草葉填充。緣上翹,飾以連珠狀花朵。鏡面閃現著石黑色清冷的光澤,同時依然保持著唐代銅鏡特有的渾厚、精致、大氣、包容。這枚銅鏡體型厚重,紋飾為高浮雕形式,瑞獸、鸞鳥、飛雀以及蔓枝、卷草等各種動植物紋飾尤為精美;海獸、孔雀與葡萄,這三種完全異質的文明因素,搭配和諧,相得益彰。葡萄莖葉、海獸孔雀的毛發細節,都栩栩如生。這面銅鏡不僅是葡萄鏡中精品,在所有銅鏡中也屬于佼佼者。
“海獸葡萄鏡”這一定名時間較早,出自清代梁詩正等奉敕編修的《西清古鑒》。而此之前,這類銅鏡在宋代的《博古圖錄》上稱為海馬葡萄鏡,區別在于對這一外來獸類動物的不同稱呼。大部分銅鏡都是以海獸和葡萄為主題紋飾,長沙博物館所藏的這件加入了孔雀紋,區別于普通的鸞鳳雀鳥紋樣,因此更顯得厚重且精美。
海獸葡萄鏡是唐代葡萄紋銅鏡中最為流行的一類,出現于唐高宗時期,流行于武則天時期。這種說法按銅鏡鑄造與紋飾的演變發展史來說,是較為準確的。葡萄鏡的種類較多,從初唐到中唐均有不同的變化發展,徹底消失則是在晚唐時期。以長沙博物館館藏的葡萄鏡來分類,基本可以分為海獸葡萄鏡和純葡萄鏡(圖2)兩類。本文所介紹的海獸孔雀紋葡萄鏡,雖然紋飾精美,但是布局較為中規中矩,表現出特別的是另外一面葡萄鏡(圖3),明顯打破了六朝最為流行的分欄式布局——古鏡圖錄稱之為“過梁式”,同時葡萄紋飾的造型自由舒展,打破了圓形分割的束縛。六朝至隋唐早期的銅鏡,多半還有分區,仍然繼承漢代以來規矩紋銅鏡的傳統,然而過梁式葡萄鏡打破了這一傳統。這兩類葡萄鏡的年代先后仍待研究,以現在的資料來看,過梁式年代并未明顯晚于分欄式。
葡萄枝蔓從銅鏡內區蔓延到外區,與外區的葡萄枝蔓相交織呼應,因此這類葡萄紋又叫“過梁葡萄紋”。這時的葡萄紋已是圓形框架結構,由連續的波形作為骨架并將海獸圍在其內,看上去好像瑞獸正在葡萄藤蔓之間自由奔跑,使瑞獸和葡萄紋之間有了較為自然的組合,各種姿態的瑞獸以自由填充構圖方式穿梭奔跑于葡萄枝蔓之間,給人一種活潑靈動的視覺效果,整體風格豐富且和諧。同時布局還秉承了六朝以來的主流——紋飾圖案呈中心對稱式,從其鑄造風格、造型布局、紋飾細節都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唐鼎盛時期的工藝品,是生產力水平和藝術審美完美結合的見證,其年代可以準確斷定在唐代的武則天至玄宗時期。
海獸是唐代葡萄紋銅鏡中使用最為廣泛的一種紋飾。這些動植物都不是中原地區原生本地出產,而是由海外、西域絲綢之路流傳進來,所以通稱為“海獸”。魯迅先生就曾在《墳·看鏡有感》中說過:“古時,于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雖然名為“海獸”,但它卻不是真的海生動物,只是古人的一種地域概念罷了。藍孔雀分布于印度和斯里蘭卡,綠孔雀分布于東南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稱之為海獸,都是外來進貢動物,或者外來的動物寓意。
及至唐代,日常生活用品中裝飾采用葡萄紋的逐漸增多,最常在織錦、壁畫以及銅鏡等物品上使用的圖樣,尤其是葡萄紋的銅鏡,成為葡萄文化最重要的載體,葡萄紋也成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圖案紋樣之一。而石窟、墓葬壁畫上出現的葡萄紋,有的是作為主題之外的鑲邊紋飾,如敦煌唐代洞窟、云岡石窟等;部分是壁畫內容的一部分,如永泰公主墓,有一捧果盤的侍女,果盤中的數串葡萄及葉子清晰可見;甚至在墓室石槨上也出現了葡萄紋樣,最具代表性的是隋代虞弘墓,其石槨上有浮雕的三男子邊舞蹈邊釀酒圖。他們在六角臺上手拉著手,腳一邊踩踏葡萄,旁邊的兩個男子從左右兩側拉住垂下的葡萄藤蔓以保持平衡。
孔雀出現在銅鏡紋飾上的情況并不多見,而且一定是與葡萄鏡一起出現,單獨作為紋飾的情況并不存在。在這面銅鏡上,四只巨大的孔雀,纖毫畢現,神態栩栩如生,與周邊的葡萄紋與蔓枝紋一起,形成了賞心悅目的構圖。作為銅鏡紋飾,孔雀比不上鳳凰、鸞鳥甚至鳥雀之類的傳統吉祥鳥類,但是它與葡萄紋一起,“中西合璧”,這是唐代的旋律,也是盛唐的氣魄。
學術界對葡萄紋是本土還是外來的紋飾有過爭論。有日本學者認為海獸葡萄鏡紋飾是來自于古羅馬,也有人認為禽獸和葡萄紋的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國已流行的葡萄紋樣與四神十二辰鏡或四獸鏡、五獸鏡等紋樣結合。這說明葡萄紋的圖案確實最早來自于海外,西方傳統裝飾自拜占庭、古波斯等傳到中國后,才漸與唐初獸鏡和四神十二生肖鏡等紋飾融匯一起。現階段主流觀點是唐人從外域已有的葡萄與動物組合裝飾紋樣上得到啟發,以海納百川的心態,突破性地將葡萄這一外來植物紋樣與中國傳統紋樣結合、改造、融合,創造出的一種既新鮮又包含有中國自身紋樣傳統的新的紋樣形式,才使其成為中國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陳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中評論:“則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文化藝術上同理,隋鏡未能脫六朝之窠臼,分欄分區一應俱全,唐代銅鏡則吸收前代傳統,又引入外來文化符號,包容并蓄,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屬于唐代物質文化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