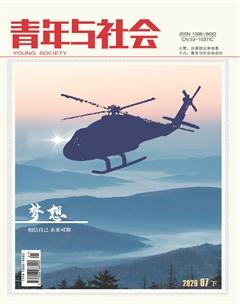儒家倫理思想中生死觀的現世啟迪
韓笑笑


摘 要:儒家倫理作為一種傳統的倫理思想資源,對于我們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傳統儒家倫理思想中,關于生死觀的探討也一直存在。生死問題不僅僅存在于書籍等資料的記載中,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儒家生死觀中蘊含著許多豐富的精神資源,其中儒家把生死貫通起來,提出了衡量生與死的價值標準,揭示了生命的意義,這些觀點對于當代人對待死亡和生命的意義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儒家倫理;生死觀;生命倫理
一、先秦儒家倫理思想中的重生思想
先秦儒家倫理思想中蘊含著關于生命觀、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死亡等問題的討論,儒家倫理思想中一直強調重生哀死的思想,也有的講到儒家是厭惡死亡的,但是從《論語》等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儒家也是提倡“死得其所”的。
儒家倫理思想中關于“重生”的看重有著兩層含義,第一點是對于人肉體生命的重視;第二點是對于人的精神生命的重視。在傳統儒家思想中,一個人的完整生命不僅僅是肉體的健康與整全;更關鍵的是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有機統一。而且儒家的生命觀中更加重視的是人的精神生命,在某些情況下,人的精神生命比肉體生命更加重要。這里就存在著兩種情況,當肉體生命和精神生命沒有沖突的時候,儒家首先是推崇肉體生命的寶貴,因為對于肉體的保護是一種孝的表現,也是“孝”的要求。由于人的生命之寶貴,所以孔子提倡對于生命的重視,同時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身亡,不惹是生非和冒險:“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這里講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做事沖動,不加思考的人,做出這樣的犧牲是沒有意義的,與儒家所提倡的成仁不相符。但是當肉體生命和精神生命相互沖突的時候,就會提倡“殺人成仁”、“舍生取義”等做法,因為在傳統儒家看來,在這種情況下要尊崇更高層次的社會價值,這個層面的精神生命就是指個人生命對于社會、對于國家的價值所在。
二、儒家倫理思想中的死亡觀
孟子講到,“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表明“重生哀死”是人的本性。荀子講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也是表明強調”生“是每個人值得去追求的,而輕易求死不僅僅是一種不孝,而且是每個人應當厭惡和拋棄的。
由古至今,在大多數人看來,只有生才是好的,死是最不好的,即使一個人高壽而亡,壽終正寢也被認為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一般都認為死亡時痛苦的,是一種完結,是有歸于無的。但是死亡的問題是每個人在人生中都不能避免的,儒家倫理思想中也包含一些關于死的看法。
對于儒家而言,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不是由自然生命決定的,人是有著主動性的,有著自我存在的意義,如果我們對于自然生命的結束是恐懼的,那就表明我們受到死亡的限制,從而不能超越死亡,從而和一些動植物是沒有區別的,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生命的可貴,同時也在于人類的自主特性。動植物受到死亡的限制,從而無法面對死亡,甚至從生到死的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的自主性的體現,但是人卻不一樣,我們可以去感受,去迎接死亡,甚至超越死亡。在儒家看來,如果我們能超越死亡,那么我們的生命就會一直延續下去,這種生命的延續不是指肉體生命的存在,而是一種精神生命的不斷留存與延續。超越死亡的關鍵就是明白“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道理,人在早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那么晚上如果去世也沒有什么遺憾了。人之為人的存在就是要明白一定的道理和規矩,如果不遵守倫理道德,那么人就枉為人,但是如果用自己的一生去踐行道德知識,那么就能夠領悟道德的深層含義,也會坦然面對死亡。
三、儒家倫理思想“生死觀”的當代意義
由于生死問題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特別是關于“死亡”的思考,有著更為復雜的看法,恐懼和懼怕死亡的到來,認為死亡時一種不幸的事情,這種觀點似乎是更常見的,但是也應該明白死亡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它不代表著終結,不代表著生命本體的消失,“死”是可以有價值的,這種價值可以通過由“生”到“死”的一系列過程中體現出來,這種有價值的死亡也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所提倡的。
(一)實現生命價值的途徑
儒家十分重視人在死亡之后對于后世的影響,這不僅可以使自己的名聲和功績流芳百世,而且可以使子孫后代得到庇護,從而達到家族的繁榮和長生。儒家認為,雖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那么死亡就是值得的,或者說是不朽的,這種不朽有著三種層次。儒家認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這三個不同的人生價值的層次中,第一個層次是立德,也就是要求人成為一個道德的楷模;第二個是立功,為國家建立功勛,特別是在國家民族面臨為難時,為國家做出貢獻,第三個層次時著書立說,為中華民族做出貢獻留下一些寶貴的文獻資料,對后世帶來影響。宋代哲學家張載講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對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價值觀的說明。
儒家認為實現個人生命價值的方式就是“內圣外王”。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孔子認為,只有做到知命、知禮、知言,才能成為君子。其實儒家修身的重點,就在于塑造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的人,培養一個有著君子品質的人。成為一個具有君子品行的人,關鍵做法就是“內圣外王”。所謂的“內圣”指的就是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使自己進入圣賢的境界,“外王”就是積極投身于一些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人,也就是達到“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二)順應死亡的到來,理性對待死亡
儒家倫理思想中認為生死是必然的一種現象,是我們活在世上的人都無法避免的,這種必然的東西我們或許沒有辦法改變,但是也不是要消極的做事,去消磨時光,虛度一生。儒家倡導的是一種積極的、向上的人生態度,強調活著的人應該努力踐行儒家提倡的“仁“、“禮”、“人倫道德”、“成仁取義”等做人的道理,有所作為,那么當面對死亡時,就會不留任何遺憾,從而也就不畏懼死亡,宋代儒學家張載在《西銘》中指出:“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也就是講,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活著的時候,富貴貧窮都是上天給予的眷顧或考驗,活著的時候順應父母和事理,死的時候,便心安理得,安寧而逝去。也就是說在或者的時候要順勢而為之,這樣的話,當面對死亡的時候也是安寧的,順存沒寧,生死兩安。
在儒家看來,我們人的一生不可能都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進行,自己的生死和富貴,只能盡人事,聽天命。如果按照玄秘的角度看一般是一種消極的生命觀,但是剔除了其中“天命”的神秘色彩,把“天命”當作自然規律來看,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就有了另一種解釋,也就是說人在活著的時候順應自然的規律和遵守道德做人的道理,當面臨死亡時候,就可以理性的面對,不用恐懼,淡然迎接死亡的到來。
(三)“存心養性”,“樂知天命”
孟子告訴我們一個人要“善生”,同時也要“善死”。“善生”指的是要在活著的時候珍惜生命,存心養性;“善死”是要順應生死的規律,安靜坦然的面對死。
儒家把人的生命分為自然之命和道德之命,而這兩者相比較,道德之命是更為重要的,自然之命指的就是人的肉體生命和生死規律的必然性;道德之命指的是人通過不斷的努力所獲得的一種個人價值的彰顯,實現道德之命的途徑是“內圣外王”,正確對待自然之命的態度就是“樂知天命”。所謂“樂知天命”的人生態度包含著三種含義,第一種是以苦為樂,即“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第二種含義指的是“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的人生態度,第三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生態度。
在當代,很多人的生活壓力使得個人的幸福感下降,有些人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患了抑郁癥,甚至到最后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認為的“痛苦的一生”,這部分人所面臨的問題,其實都是人生中所不可避免的,如果一直深陷其中,不跳脫出來,則會陷入痛苦的漩渦中。而跳脫出漩渦的途徑,可以從儒家“樂知天命”的人生中得到借鑒,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盡人事”,傾其所有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履行好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做一個由德行的人,積極努力的去改變現狀,即使不能改變客觀的條件,那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狀態,順應“天命”的客觀規律,順勢而為之。
參考文獻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年.
[2]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4] 鄭曉江.“樂知天命”與“安之若命——儒家生死智慧之現代詮釋[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5] 張朝霞.中國傳統生死智慧及其現代意義[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