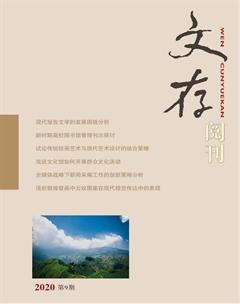基于酷兒理論對比分析酷兒電影
沈盼盼 謝苑苑
摘要:20世紀90年代興起新酷兒電影浪潮,中西方分別出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酷兒電影。本文基于酷兒理論擬對中國電影《阿莉芙》與智利電影《普通女人》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兩部電影的異同及原因。兩部電影都講述跨性別者的故事,本文從主題、人物、情景設置三方面分析了二者相同處,然后從影片結局、自我認同方式、壓力來源三方面比較其不同處,最后從宗教影響、家庭倫理觀念、價值取向、社會建構方面入手剖析原因。本文在酷兒理論指導下對兩部電影進行分析,展現了酷兒們通過自身相對傳統和主流文化的異質性,去獲得自由公平表達欲望和性別身份的權利,揭露了酷兒電影期望創造新的人際關系格局和理想化生活方式的本質。
關鍵詞:酷兒理論;酷兒電影;《阿莉芙》;《普通女人》
1.概述
20世紀90年代興起新酷兒電影浪潮,以格斯范桑特的《我私人的愛達荷》為代表,創作了一批以女同性戀群體為主題的電影。90年代的新酷兒電影主要表現同性戀的不羈、反叛,也反映了社會性問題,涉及性、毒品、艾滋病等。影片多以獵奇、窺探的視角進行。進入了21世紀新酷兒電影開始有所轉向,并且影響了亞洲及其他地區的酷兒電影創作。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認同性伴侶合法,酷兒電影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更多轉向了細膩化的同性間情感的描寫,常態化敘事開始成為主流,以平等視角進行描繪,通過歷史、現實等各種角度來盡可能真實的還原同性戀群體。遺憾的是,酷兒電影關于雙性戀、跨性別者、異裝者、虐戀描寫較少。
目前國內外學者就酷兒電影進行了多方面研究,有學者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剖析酷兒電影中的同性戀現象[1],也有學者從宏觀文化視域下分析中西酷兒電影差異[2],還有學者從同性戀的亞文化角度解讀酷兒電影的演變歷程[3],另外有國外的學者從文化焦慮入手分析了酷兒電影中犯罪概念與同性戀的融合[4]。然而,以酷兒理論著手分析酷兒電影的研究較少。酷兒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新的性理論,它質疑性別身份的中心主義論者,探討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年齡等的關系,以給人們對于欲望和身份的理解帶來更為廣大的影響。酷兒電影對酷兒理論有先天實踐的優越性。本文選擇《阿莉芙》與《普通女人》兩部跨性別者電影,在酷兒理論基礎上,進而總結二者處理酷兒電影上的不同策略和深層的價值差異,借以對酷兒電影研究有所補充。
2.酷兒理論
酷兒理論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史學、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為自己找位置。“酷兒”這一概念作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范或性規范不符的人。
2.1挑戰異性戀霸權
酷兒理論對異性戀制度和其話語霸權的社會常態發出挑戰。異性戀機制最強有力的基礎在于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欲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就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征和異性戀的欲望。三者一致性是被人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當作人類性行為的基礎,建立以異性戀為基礎的性別等級秩序。然而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它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復行為的真實基礎,并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人們的注意力應集中在性感的性活動上而非適當的性別表演,質疑以性欲為基礎的性身份的概念,挑戰二者之間關系。
2.2消解男女兩分結構
酷兒理論打破了男性與女性及對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劃分界限。酷兒并不是一個新型的固定的“性主體”的標簽,而是提供了一個本體論的類型。它拋開了單一的、永久的和連續性的“自我”,以這樣一種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變的、不連續的和過程性的,是由不斷的重復和不斷為它賦予新形式的行為建構而成的。在各種身份分類的挑戰中,超性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巴特勒認為,男女兩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每個人都是易性者,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標準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
2.3批判傳統同性戀文化
酷兒理論提供了一種表達欲望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份和性身份,質疑標準典型的“同性戀者”,重新定義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三者聯系。傳統的同性戀身份政治以“同性戀社群價值”的名義壓抑在酷兒性行為中大量存在的差異的偏向,創造出一套關于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規化的圖景。酷兒理論否認這種“偽裝神圣的道德主義”,提倡性多樣性,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
3.酷兒電影《阿莉芙》與《普通女人》的對比研究
3.1相同處
3.1.1擺脫異性戀性別制度
在傳統性和性別觀念中,一個人生理性別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征和異性戀的欲望[5]。而《阿莉芙》與《普通女人》兩部電影中的主角打破了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劃分。阿莉芙愛上了異裝癖同事阿哲,瑪利娜也擁有男性愛人的奧蘭多。巴勒特的“表演”理論中提出,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地重復的行為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正如阿莉芙與瑪利娜“她們”是男人,“她們”愛男人,但是作為一個女人來愛男人,“這種表現就意味著性和表征的不和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不和諧,以及社會性別和表征的不一致[6]。”但主角們對異性戀制度的“天生化”進行質疑,使性欲擺脫性別身份認同,將生理性別從自然化表象的束縛中解脫,把性建立在一個不斷改變的表演的系列之上,是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性欲三者鏈索關系的挑戰。
3.1.2揭露二元運作
在《阿莉芙》與《普通女人》兩部影片中,主角或多或少面臨外界的非議。阿莉芙父親面對異裝的兒子問出:“我的兒子阿利夫在哪里?”瑪利娜遭受諸多歧視,甚至秉公的警察都對其做出粗暴言行。這些現象建立于男女二分結構,性別的單義性將跨性別者直截打入“他者”行列。在其性別身份不符合傳統兩性認知時,人們自然而然將非規范化的性實踐視為社會禁忌,趕入其道德和律法合圍而成的領地進行壓制。而酷兒理論對固定的性身份提出質疑,認為其不過是重復的實踐,“某種表象被沉淀、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象”。自我不應是固定的性主體,而是通過不斷重復和新形式的行為進行建構。主角們挑戰性別等級制度,對抗傳統價值觀(如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婚戀觀)。
3.1.3打破“同性戀身份”局限性
兩部影片中的主角都為跨性別者,她們各自努力生活而非泥淖中獨行。用固有存在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定義二者顯然是單薄的。她們擁有男性生理性別,但其社會性別認同的確是女性,心理上是異性戀而在生理上是同性戀。酷兒理論強調性方面的多元流動性,用傳統“同性戀”或者“異性戀”的靜態身份觀念已然不能全部概括。Queer并不指某一種性類別,而是指這樣一種過程:性身份和對欲望的表達能夠擺脫這樣的結構框架。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身體屬性,而是多重、游移不定的,主角跨性別者的身份彰顯了分類界限逐漸模糊的趨勢,提供了表達欲望的新方式。
3.2不同處
3.2.1異性戀價值矩陣下的排他
傳統性和性別觀念認為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征和異性戀的欲望。然而這是為了繁衍需要將異性戀模式自然化、優等化的結果,三者的一致性使社會性別的層級結構得以建立。為了維持這種適宜的主體性,“非規范化”的性實踐必定被打入賤斥者的領域,大眾對其的排斥恐懼心理正是控制性別系統的工具。兩部影片中對此的體現緊密交織在家庭、階級、種族、文化的軸線中。
中片里固有成見主要來自于家庭。阿莉芙有傳承父親族長位的責任。影片初他一直向父親隱瞞跨性別者身份。得知要回部落商討相關事宜,他卸去了濃妝。盡管排斥,但其沒有拒絕強迫性的男性社會性別表演。沖突在父親意外拜訪時達到高峰,偽裝建構的男性特質轟然倒坍,在其陷入巨大驚慌外,對性規范越軌行為認識的自我矛盾也在家庭沖突中達到最高峰。盡管后期主角重著女裝但不可否認在邊緣化的危境下家庭使其趨同于異性戀價值矩陣。面對其中性別身份的話語霸權,阿莉芙從妥協到抗爭,停止文化規范對性的物質化,它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身體屬性,而是流動、多元的欲望。
智片中則全然相反,家庭給予主角唯一的溫暖與理解,偏見與排斥來自外界社會。愛人猝然離世打破了平靜的生活。愛人家庭以侮辱言語、粗暴行徑打碎她構筑的女性身份,視其欲望為怪異,禁止她參加葬禮。影片中警察命令主角脫下衣物,擺出姿勢,以大眾視角對其身份窺視與評判。相機后的獵奇是畸形欲望的滿足,更借此展露社會對該群體的不公與惡意。社會性別表演具有強迫性,即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范,就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然而這種性別規范化的表現只是文化管制下的產物,瑪利娜打破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天生化的連續性幻覺,沖破社會給予的壓迫,執起法律武器,在逆境中反抗異性戀的性統治。
3.2.2二元性主體裂變
巴勒特的性別操演理論認為性別不是一種存有(being)而是一種行為(doing),人們不可以通過自由控制和有意為之的行為形成性別,性別是在不斷重復性別規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性主體是流動的、過程中的范疇。先天某種的性別特質不過是社會規范與話語建構的結果。兩部影片中主角分別從不同角度瓦解支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欲望的規則,走出二元體系的囹圄,尋找到自身性別的符號。
中片里主角身為男身卻渴望女性軀體,模仿表演無法解決生理與欲望相斥,其選擇變性來打破兩性界限尋找真正自我。電影中多次應用鏡子揭示主角內心,暗喻其自我認知轉變。開幕為主角對鏡子整理妝容,畫面上移為一美人魚像鏡飾,隱喻其內心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女性外表是其創造的另一個身份,借衣著的護照通過禁口進入相反世界——以這種近乎成為另種性別的方式,但其靈魂仍然禁錮于肉身中。影末阿莉芙完成變性手術,穿衣鏡前照出女性獨有的曼妙曲線。主角得到父親認可繼承族中頭目,并能自如與顧客談論發型款式。彼時鏡中的女人已與內心自我真正融為一體,阿莉芙打破傳統性與性別觀念的枷鎖,從欲望本源尋找到自身。但以巴特勒理論所言,男扮女裝的表演不是對原初形態的模仿,而是“一個對模仿的模仿,是一個沒有原件的復制品”。當男孩想像女孩一樣生活他本不必傷害自己的肢體,但在異性戀霸權無形驅使中形成了諸多暴力規范。在傳統倫理土壤中,酷兒文化無法得到滋養與根本的認同,性主體的建立更趨于向傳統認知妥協,主角對女性身姿的渴求也十分了然。
與中片不同,瑪利娜更多著重于社會性別,舍棄單一的性別表演而為“女性氣質”不斷賦予新形式。片中同樣應用鏡子意象,每次出現都是對性別身份的逐步強化與建構,通過它將自我想象為他人,把他人指認為自我(他人即指女性形象與特質)。其一為主角與街道上一面修容鏡相對,鏡中身影扭曲是其被動陷入性別認同困境的痛苦。彼時對女性身份的質疑遭受以致辱罵、人身攻擊慘烈現境令其無法。其二,為了尋找愛人遺物主角轉換性別進入男性浴室。進入樓道后映射的多個破碎鏡像暗示她雙重性別身份。在穿越兩性浴室時,采用中景長鏡頭記錄這“越界”行為——包裹上身的浴巾下移至腰間,借由性別空間跨越在影像上完成了對主角身份的述說,她追求女性身份,但不逃避男性過往。其三為片末,主角躺在沙發上,一面鏡子遮擋代表生理性別的性器官,映射出她女性面容——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錯位,模糊了彼此自然化、天生化界限。她與自我達成和解,并構筑成獨立的性主體。在巴勒特看來根本不存在“恰當的”或“正確的”社會性別,所謂“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復行為的真實基礎。瑪利娜在尋求一個普通女人身份時,質疑并顛覆原有性別機制,解構單義性的“性別”,在男性身體與女性靈魂中尋找到自我平衡。
3.2.3解蔽原初同性戀認知
酷兒理論質疑標準“同性戀者”,粉碎了性別身份和性身份,否認其靜態性,提出身份是流動變化的。性別沒有對錯真假,也沒有原初和衍生,而是在不斷行動重復中越界、形成。
中片主角阿莉芙不斷嘗試作出個人性行為和情感的選擇,影片末原為男兒身的她以女性身份接受頭目繼承。與生理性別不符的欲望讓其痛苦過,她渴望女性身體去生活,去獲得他人的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血緣紐帶維系的宗法社會結構中,她直面邊緣化的危機,勇敢轉化性別,壓抑的性行為在身份流動變化中得以解放。影片為跨性別人群撕破一個裂口,讓更多人得以窺見他們的真實生活,讓社會對其多一分寬容與溫情。
智片中盡管瑪利娜仍為男兒身,但她最后如愿以女歌手的身份站在劇院舞臺中歌唱。欲望并非性別的化妝表演,瑪利娜以女性身份與奧蘭多相戀而非純粹同性戀,身為男身的她在一次次反抗中形成新的性表達,以女性身份努力追求歌手夢想實現個人價值。與中片不同的是智片并未將沖突弱處理,而是將瑪利娜遭遇的不公直陳,通過直接的酷兒表述向傳統性別機制發起挑戰,侮辱、暴行等沖擊性行為與中片的溫和相較產生極大張力,直擊社會的精神實質。
4.酷兒電影《阿莉芙》與《普通女人》的異同原因
4.1宗教影響
中國文化傳統多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響,人們受道德倫理約束卻少有宗教信仰。如傳統文化中道家思想的“陰陽”之說,陰指女性,陽指男性。男性陽剛、強大,女性陰柔、弱小。儒家文化提倡女性的美德在于順從的規范,女性應遵守“三從四德”。傳統文化中對兩性截然不同的禮教規范、行為規定和等級差別塑造了男女兩性完全不同的性別氣質。跨性別群體的性別表達不符合傳統社會觀念的對其的性別期待[7]。
在西方,許多人信仰基督教,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和文化體系幾乎貫穿所有領域。原罪是基督教重要的基本教義之一。據《圣經.創世紀》記載,神創天地,為掌管萬物按照自己形象創造男人,后取其肋骨造了女人。其中二者生理性別差異明了了創世說中暗含的男女二元分類標準。后受蛇的誘惑,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犯下原罪被上帝趕出伊甸園。從婚姻角度分析,其中隱藏了另一個信息即一男一女人類婚姻家庭模式的選擇,上帝讓男人與女人組建家庭、繁衍后代,并增加女人懷孕時的痛苦作為“原罪”的懲罰,人們應該遵其為典范。跨性別者顯然違背了這種選擇,其性別角色也難以在二元結構中得到依托,在基督教文化氛圍中自然被視為異類。
4.2家庭倫理觀念
中國家庭倫理觀念里以人倫為基礎,在以血緣關系為基本坐標中用情感情理為法則處理家庭人際關系,靠他人存在確立自我存在,重視個體與家庭其他成員的關系,離開了這種關系,自我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中國的家庭本位思想源遠流長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家庭作為人們情感和精神的支柱,個人價值及社會地位完全依托于家庭,這易造成人格的日漸萎縮,個性表現愈加無力。影片中阿莉芙處于一個氏族部落中,身上背負的血緣不允許其逃脫責任,放任自由,她被迫壓抑內心性別。為了追求靈魂自由,在面對抽調血脈后可能面對的理智與情感的失重,阿莉芙毅然選擇反抗,是否以男身接受頭目是其抗爭的主流。家庭成為其作為跨性別者成見的首要來源[8]。
中國傳統家庭中以父子關系為主軸。中國傳統社會對這種血緣父子關系的重視表現為對男性世系家名及后代的傳承,而一旦家庭中確立這種父子關系往往要求講求孝道。影片中阿莉芙同樣面對守孝與自我的矛盾,父親與其關系的沖突與緩和也是影片的重要感情線。
西方家庭倫理觀念推崇以個人為中心,以理性的基本原則對待家庭成員和家庭事務。在西方家庭中,個人是本位,個體具有較高價值,不依賴于他人存在,獨立于家庭關系之外,享受自由與平等,是“建立在自由、樂觀主義、世俗主義、理性主義的理想之上,尊重肉體,也尊重心靈,對個人的莊嚴和價值給予高度重視”的希臘精神實質的體現。
不同于中國社會家庭,西方家庭以夫妻倫為主軸[9]。夫妻之間“在經濟上的彼此獨立倒促進家庭成員的彼此依賴”。夫妻在權利上的平等使典型的西方家庭想更像一個民主政體。美國的父母與孩子之間,自由、平等,父母并非權威者,子女完全有作為家庭的一個部分,擁有的權利與父母一樣多。孝順非家庭中主調,相反有束縛自然意識和自我發展之嫌。父母讓孩子擁有選擇的自由,而不灌輸既定的規范進行行為塑造,他們往往靜然而予以理解。此外西方家庭是流動的,人們傾向從家中走出,發展獨立自主的個人。影片中瑪利娜沒有受到來自家庭的壓迫或是指責。反之父親與姐姐是是給予她溫暖的來源,他們正視瑪麗娜作為個體的選擇,并給予尊重。
4.3價值取向
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認為,個人不僅要對己負責,還要對別人和社會負責,價值的實現需通過社會貢獻。人的確立方式是在“二人”對應關系中生成的,“自我”概念與他人相伴而生,個人的價值只有在他人的關系中得以體現。但若這種思想走向極端易忽視個人的存在,以致壓抑了人的自主精神。阿莉芙特殊身份使其具有繼承的特殊責任,而她渴望變性的愿望也極有可能由此消解。而影片提供了另一個正解,阿莉芙成為了女頭目,緩和了集體與個人之間的沖突,二者相互協調、相互妥協,走向融合。
西方以個體主義為基本文化特征的國家,人們注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認為人應該為個人而生存。他們主張個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不喜歡受到外界的干預和限制。如拉里.A.薩姆瓦所言“在西方文化中,個人是至高無上的,個人主義是首要的和肯定的價值觀。”其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是個人中心主義,強調個人價值并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個人價值的最終實現[10]。瑪利娜在影片中不僅維護了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權利與尊嚴,而作為女歌手她最終站在劇院里進行表演,通過在事業上成功實現了自我價值。
4.4社會建構
社會主流對跨性別者的歧視來源于男女性別范式,其對男女的行為舉止有嚴格的規定,跨性別者作為男女性別二分范式的“他者”被這種固有模式禁錮。男女性別范式源于社會建構。
在古代中國,由男權社會建構起的一整套社會制度使男女之間存在截然不同的社會分工。對于男性與女性歸屬的領域劃分塑造了男性與女性截然不同的分工、社會角色,男權社會通過把公共領域劃歸為男性,社會要求男性擔當起養家糊口的責任,男性是家庭的“頂梁柱”;把私人領域劃歸為女性的方式,給女性施加了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地位上的限制。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持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
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西方國家中,并在英語的語法中有所體現,英文中根據女性的婚姻狀況分為Ms(小姐)、Mrs(夫人),到了現代才衍生出了Ms用來指代婚姻狀況不明的女性;而男性則無論其婚姻狀況,都被稱為Mr;由此可見,在英語的文化語境中,對于女性來講,婚姻是對其定位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