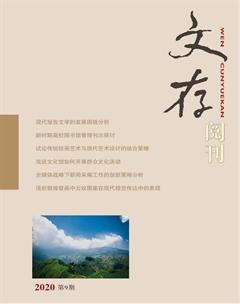T.S.艾略特《荒原》的東西方哲學思想探究
摘要: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T.S.艾略特是美國最偉大的現代詩人之一。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哲學家。其詩在展現現實面貌的同時也蘊含著深刻的哲思。作為現代詩派里程碑的《荒原》也毫不例外。本文旨在探討《荒原》中蘊含的東西方哲學思想。
關鍵詞:尼采哲學;二元對立;東西方哲學
著名長詩《荒原》被認為是現代派詩歌的里程碑,20世紀西方文學中的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杰作。一經出版,便備受關注。除了詩人深厚的文字功底,晦澀難懂的用典之外,詩歌中展現的荒原狀態即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恰好契合了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處的精神狀態。全詩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死者的葬禮》《一局棋戲》《火的說教》《水中的死亡》和《雷的說話》。在第一個部分詩人描繪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荒原;第二個部分描繪了貴婦的精神荒原;第三個部分描繪了下層人們的精神荒原;第四個部分是腓尼基水手的精神荒原;詩歌的最后一個部分,詩人提出了不同階層的人擺脫迷茫、走出精神荒原的途徑。筆者認為,五個部分各自成章,看似毫無聯系,但實際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前四個部分分別描繪了不同階層人的精神生活,突出表現了這樣一個思想:在西方世界,無論是貴族還是貧民,知識分子還是平民大眾,都深受精神危機的困擾。通讀全詩,筆者認為其蘊含著深厚的東西方哲思。
1.上帝已死、永劫同歸的尼采哲學
“上帝已死”是尼采重要的哲學論斷。對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而言,這一論斷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宛若“腐朽的糞便一樣的成分”(羅素,2010:394)。筆者認為尼采吶喊著“上帝之死”所反映出的哲學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與此詩相近。在《荒原》中,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們都深陷不同程度的精神空虛之中。這種心靈的迷失很大程度上源于信仰體系的崩塌。這清晰地傳達了尼采所信奉的“上帝已死”的哲學觀點。對于這種裹挾人們的精神迷失,詩人流露出了深深的憂慮。然而,詩人并沒有悲觀與絕望。詩人懂得盡管人們過去的精神支柱-上帝不復存在,但人們可以在生活中尋找新的信仰寄托,燃起新的希望。《荒原》除了體現尼采“上帝已死”的哲學觀點,也與后者宣揚的永劫同歸的思想相契合。尼采是一個矛盾式的人物。在他的哲學著作《善惡之外》中他慷慨陳詞,盛贊自由的精神和意志,不遺余力地鼓勵人們掙脫已有的一切道德束縛。然而,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個讓世人倍覺沉重的概念,即永劫同歸。他認為人生毫無新意,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一段又一段經歷的重演。我們人類不過是廣袤的宇宙中無足輕重的一粒塵埃。這種永劫同歸的哲學思想在《荒原》的第四部分有所體現。詩歌的第四個部分是全詩最短小精悍的部分,主要講述了一位曾經無比風流倜儻、英姿颯爽的腓尼基人水手,在他死后,一切都化為灰燼的故事。一切榮辱得失、曾經的光環與榮耀都隨著他的死去而當然無存。此處,詩人表達的一個哲思就是:無論一個人在世時多么光鮮亮麗,死后一切皆為過眼云煙,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個體的生命顯得十分渺小。此外,詩人提到腓尼基水手歷經青年和老年時期之后,最終進入“漩渦”,暗示生命不過是一段又一段經歷的反復循環。與尼采主張的永劫同歸不謀而合。
2.詩歌中二元對立的拆解
不同于笛卡爾的二元對立學說,現代哲學提倡解構——即二元對立的消解。作為一首現代詩,《荒原》亦主張二元對立的溶解。在詩歌的第一個部分《死者的葬禮》中,“生”“死”這一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體被拆解。詩歌中,敘述者反復強調一種“不生也不死”的狀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生與死的不是一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即生與死之間還有別的狀態。如此一來,生與死的這一兩元對立體被消解。有關生與死對立關系的消解在詩中的第五個部分也有體現。“我們曾活過而今卻垂死”。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消解更好地突出了處在精神荒原中的人們那種麻麻木不仁、醉生夢死、半死不活的狀態,從而極大地深化了詩歌的主旨。除了對“生”與“死”這個二元對立的拆解,詩人也對其它二元對立體進行了解構。詩歌中“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的對立關系顯得模糊不清。《死者的葬禮》中描繪的“不真實的城”卻真實地再現了倫敦城的景況。這種真實與不真實關系的破除使讀者游走在真實與虛幻之中,淋漓盡致地呈現了生活在荒原中的人們的精神狀態——麻木、混沌,引人深思。
3.詩歌中折射出的佛教思想
《荒原》中有好幾處地方折射出了佛教的睿思。眾所周知,基督教宣揚禁欲主義,而源自東方世界的佛教更是將禁欲主義發揚到了極致。詩歌中的整個第三部分就是一幅欲望世界的眾生圖。詩人形象細致地描繪并且抨擊了女辦事員、商販們縱欲的糜爛生活。縱觀全詩,讀者們不難發現盡管詩人內心沉重,但他并未徹底地絕望。而是在絕望中燃起了一絲新的希望。這絲希望便是來自宗教的救贖。《荒原》第五部分以四個梵語詞結尾,前三個意為“舍予”,“慈悲”,“克制”,充分體現了東方佛教思想對《荒原》創作主旨的影響。當欲望之火在整個西方世界如洪水猛獸般肆虐時,詩人是清醒的。他明白,人們的困境是信仰缺失和過度的物欲所致。于是,他向佛陀虔誠地祈禱,寄希望于借助佛教的智慧來撲滅這場欲望之火。最后一個梵語詞“shantih”出自佛教的經典之作《奧義書》,意為“平安”。在梵語中接連唱頌三遍“shantih”,意為內心平和,即能夠平和地接納“我”“你”“他”。在《荒原》的結尾處詩人將其重復了三遍,表達了其對人們走出精神荒原的美好希冀。在這里,艾略特向佛教發出了呼救之聲,寄希望于佛教宣揚的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克制、利他的精神能夠引領西方人慢慢走出荒蕪貧瘠的精神荒原,從而擁抱平和和安寧。
《荒原》中蘊含的東西方哲學思想對于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現代社會是多元的,看待生活的視角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不能再用過去那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想看待當今社會的各種現象,而應以一種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去對待萬事萬物,而不能做無腦的噴子。再者,生活在物欲橫流的現代商品經濟社會,我們隨時都有可能精神迷失。所以我們需要佛教所倡導的“舍予”“慈悲”“克制”的理念來警惕自我不被欲望所俘獲,從而擁有更加平和的心境。總而言之,東西方哲學思想滲透在《荒原》的字里行間,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挖掘。
參考文獻:
[1]Nietzsche,Friedrich.BeyondGoodandEvil[M].Edinburgh: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2]艾略特.荒原.趙蘿蕤譯.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1冊(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3]羅素.西方哲學史[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4]尼采.尼采談人生權力意識[M].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4.
[5]湯永寬.是瓶子還是籠子關于《荒原》題辭的譯文[J].外國文學評論,1998(01).
[6]張劍.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J].外國文學,2010(01):42.
[7]曽艷兵.“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論艾略特的《荒原》[J].東方論壇,2003(03):21.
[8]朱夢娜.《我們氣候的詩》的哲學主題[J].時代文學,2014(06):126.
作者簡介:
蔣玉霜,女,漢族,湖南永州人,碩士,邵陽學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