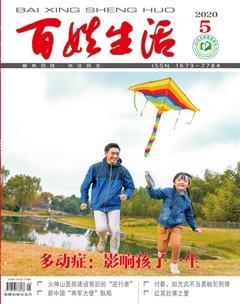北大“愛國怪人”陳漢章
魏豪
行走的國學寶庫
陳氏一族,在寧波象山德高望重。陳漢章自幼聰穎,4歲開始識字,10歲時便已賦詩100余首,少年時便考得本地童生第一名。到了25歲,陳漢章遠赴杭州參加鄉試,一舉中舉。當時朝廷先后多次聘他出仕,都被他一一婉拒。
從捧起書卷那一天起,陳漢章便將治學讀書作為人生追求,讀起書來簡直發癡。他每日天不亮,便捧起書誦讀。全村的雞還沒打鳴,陳家大院上空就響起他的瑯瑯書聲。且每篇都要誦讀10遍以上。陳漢章不僅僅是讀書,他還邊讀邊校。“考其優劣,校其佚漏,辨其真偽,評其得失。”被他讀過的書卷,旁人很難再插手。因為陳漢章記筆記有個習慣,要用6種色筆勾畫。每讀一遍,便勾描一次。從藤黃、淺藍,直到銀朱,一本書密密麻麻布滿心得。就這樣,陳漢章以最扎實的笨方法,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后來,陳漢章在北京時,教育部招待外國漢學家,必請他出席。無論對面的人問出什么刁鉆、晦澀的問題,陳漢章都能對答如流。一次,來訪的日本漢學家提出了困擾許久的迷思。在場的儒生皆不能答,唯陳漢章一字一句,引經據典地完美闡釋。這位漢學家激動萬分,直稱陳漢章為“兩腳書庫”。用現在的話來說,陳漢章簡直是行走的國學寶庫。

陳漢章畫像
但陳漢章不為名、不謀官,一心求取知識。等到軍閥混戰時,孫傳芳、吳佩孚多次親自邀請他做官。陳漢章照辭不誤。駐北京的六國使館,專門邀請他去講中國歷史,每周只用講2小時,每月報酬600塊銀圓。要知道,當時一個人每月花4塊銀元便綽綽有余了。使館還附加了專車接送服務。陳漢章還是拒絕了。這回,就連他兒子都坐不住了。跑去問父親,為何不接受如此優越的職務。陳漢章義正詞嚴:你們只知道酬金多,條件好,你們可知道,中國歷史豈能被外國所洞悉。
不當官愿意做學生
陳漢章一生最遺憾的是,未點翰林。清末時,京師大學堂聘請他當教授,陳漢章偏要做學生。彼時,綿延千年的科舉制已廢除,翰林無門。若在京師大學堂畢業,時人也稱“洋翰林”。為了做翰林,1909年,陳漢章竟然報名入學。4年后,陳漢章以中國史學第一名畢業,時年49歲。一畢業,他就被聘為北大國文、哲學、史學教授。據說,他在教授中國哲學史時,侃侃而談,從伏羲、黃帝講起,行云流水,如癡如醉。結果,兩年下來,這門課才講到商朝。
中華文化在陳漢章胸中,已幻化成無窮無盡的瑰寶。他探囊取物,用之不竭。而臺下坐著的馮友蘭、顧頡剛、傅斯年等,日后撐起中國近代哲學、文學、史學的半邊天。陳漢章“國學魁儒”的名號,不脛而走。
被稱作“愛國怪人”
陳漢章在北大前后20余年,桃李滿園。他從不避諱給學生灌輸愛國情懷。在上《中國歷史》一課時,他親自編寫講義。當時國家時局外憂內患,西方工業的車輪滾滾。陳漢章卻跟學生說, 歐洲發展的聲光化電,我國自古有之,而證據就在先秦諸子的著作里。他還特意搜羅了一批證據,給學生展示。譬如先秦時代,便有“飛車”一詞。這也被他解讀為,中國在那時就有了飛機構想。不料,一位學生起身提出反對:“陳先生,你考證出現代歐洲科學,在中國古已有之,為什么后來失傳了呢?”陳漢章正色解答:“這要在先秦時代以后的歷史講到。”在場另一位17歲少年,打斷了兩人的對話。少年說:“陳先生是發思古之幽情,光大漢之天聲。”陳漢章什么也沒說,當晚給了少年一張字條,邀他共談。少年忐忑前往,不知迎面而來的是斥責還是安撫。哪知陳漢章一見他,便說:“鴉片戰爭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養成一種崇拜外國的風氣,牢不可破。中國人見洋人奴顏婢膝,實在可恥。忘記我國是文明古國,比洋人強得多。我要打破這個風氣,所以編了那樣的講義,聊當針砭。中華民族同白種人并肩而無愧色。”這番話打動了少年,而后少年奮發圖強,成為我國一代文學大家。少年正是茅盾。這次意味深長的談話,讓茅盾了解到陳漢章一顆拳拳愛國心。只是這愛國的方式,與其他老師似乎不一樣。也因此, 他稱陳漢章“愛國怪人”
陳漢章雖然怪,卻治學認真。在北大,白天任教,晚上回家編寫講義。空閑時,給子女講解四書五經。哪怕生病發燒,學生跟到家里,他也從不回避。
1931年,68歲的陳漢章告老回鄉。在老家象山縣東陳村,繼續埋頭耕讀。這位在外游歷多年,當過北大教授的學者,回鄉也從不擺架子。逢春節,晚輩、學生去家中給他行跪拜禮,他也會以下跪還禮。起身時,還要對來者作揖。這樁奇聞,在東陳村傳開了。
德高望重的陳漢章對晚輩尚且禮節周全,對村中的孤寡老人,他也不吝施舍。逢年過節,送豬肉10斤,大米1斗。若有病災,抓藥治病,他也從不吝嗇救助。當時,家鄉有條石板路年久失修,一到雨天便泥濘難走。陳漢章以一己之力,出資修完了整條路。不僅如此,東陳村只有幾座私塾,村里適齡孩子求學困難。陳漢章牽頭捐資,興建學校,解決教育難題。與此同時,在他生命的彌留之際,還捐出1000塊銀圓,幫助縣里籌建公立醫院。不幸的是,當醫院落成時,陳漢章已溘然離世。
陳漢章衣錦還鄉,樂善好施。在象山東陳村的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陳漢章離世后,家中還留有800萬字手稿未出版。2006年,浙江省編纂《陳漢章全集》,集結了陳漢章一生心血累計21卷,近1000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