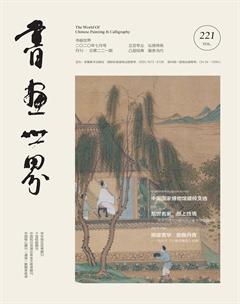誰探根九淵氣虛涵太清
呂永生

關鍵詞:蕭云從行草;筆法;結體;章法;墨法
蕭云從,安徽蕪湖人,明末清初著名書畫家,幼而好學,篤志書繪,寒暑不廢。其畫或人物或山水,遠近聞名。人物造型準確,形象栩栩;山水清疏秀潤,饒有逸趣;而書法傳世甚少,多流為畫作題跋。殊不知,其書篆、隸、真、行、草五體兼善。行草、小楷高雅古樸,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行草尤得王右軍藏骨含筋法而另辟蹊徑。蕭云從受晉唐書家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等所浸染后,漸漸形成不溫不火的書法風貌。篆書尚婉而通,隸書不乏精而密。59歲時,蕭云從為彭旦兮奮筆作山水長卷,以隸書題跋:“旦兮漢隸之學甲天下,將以易得數十幅,為晚年摹式。”其于《歸寓一元圖》中以篆書作標題,以隸書寫詩,一望而知,其書法功底不凡。在《太平山水圖》43幅畫作中,其亦以篆書為標題,以隸、真、行、草作詩文。其行草沉著而不乏飄逸,頗得“二王”神髓。概而論之,其畫作題跋,行書之中夾雜些草書,結體瘦長,用筆散朗;錯落有致,風調秀健。
其行草獨立書作為縱式行草條幅,詳覽筆觸,究其源流,饒有唐顏真卿《爭座位帖》《祭侄文稿》之遺風。蕭云從善書法,各體兼備,如梅磊所云:“世知蕭尺木以畫顯,而不知其六書、六律更精也。”[1]此作流動飄逸而沉著,或乃放手飛筆,若雨下風馳,亦見各體融于其中;有合有離,若隱若現;易退輕進,勇而非猛;無虛張夸耀之感。細而察之,或筆法,或結字,或章法與布白,天姿神縱,宕逸遒健,動合規儀,有若天成。
一、用筆寓靜于動
蕭云從用筆求“力古勢健”,隨意奔放;線條遒勁,清爽利索;重局部服從整體,亦常有主次之分,非均以發力;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用筆提按、頓挫及使轉、徐疾尤顯酣暢,承顏真卿行書《爭座位帖》之筆法。書寫毫無火氣,緊密而無懈可擊,蘊含著顏真卿活脫圓轉、駕輕就熟的大化境界,并呈現出顏真卿雍容大度、游刃有余的書寫意韻,又純以拙而重的筆意盡情揮翰,畫畫堅實,筆筆擒按,肉豐骨挺,如熔金瀉地、流光馳目。那筆筆圓渾線條的動感撲面而來,分明地表現出明朗而燦爛的心靈律動。只見神氣內斂,動作隱含于點畫之中,優游自然,出新入古。蕭云從擅用側臥之筆,顯飄逸而沉著。筆跡流澤,婉轉妍媚;思于精巧,翰無虛動。無論行書,或草以兼真,蓋起筆時藏時露,時方時圓。亦常有入鋒露紙而勢緩,起行相仿,不顯尖形,折筆較少。行筆以中鋒為總率,偶用側鋒取險,中部渾厚,動作稍慢,墨痕略見澀行,時有提按,少絞轉、多裹鋒;收筆或順勢,或勁健,毫不拖泥帶水。真所謂,筆到末處鼎力回,實到虛處勢不虛。總之,用筆微妙之變,集各家之長并將其融入自家之筆底。或篆籀,或漢隸,或魏晉風流,或顏氏情懷,用筆華麗而不乏骨力,瀟灑而不乏高雅,流美而未顯甜俗,可謂秀逸之間見清氣。
二、結體縱橫適宜
結體指每個字點畫與點畫之間的安排與布置,亦稱“結字”“間架”或“結構”。漢字尚形,故結體尤顯重要。元趙孟《蘭亭》跋曰:“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2]漢字的各種字體,皆以點畫連接、搭配而成形。筆畫或長或短,或粗或細,或俯或仰,或縮或伸,偏旁寬窄高低,或欹或正,從而構成漢字的千姿百態。要使字的筆畫搭配合理,研究書家結體必不可少。正如清馮班《鈍吟書要》云:“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跡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3]又云:“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4]由此可窺結字于書法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蕭云從此幅行草結體憑借飛動而痛快的筆法、嚴謹而不羈的結體以及通篇相互貫通的氣韻,撞擊著觀賞者的心靈,予以人美的享受;在篆、隸、楷、行、草等五種字體中既兼顧了靈動快捷而又承繼了漢字結體的嚴謹性,蘊含著別具一格的審美情趣。欣賞此作,我們不難發現,結體以修長為主,或大或小,或縱或橫,或欹或正。為了滿足謀篇布局以及書寫情感表達的需要,或意在筆前,或依循法度,無意于法亦無意于佳。
通篇結體雖然較平正,亦間或獨立,但獨立之中不乏上筆與下筆之間的微妙引帶與暗過,運動軌跡亦極其自然,且有一定的內在聯系。間或以欹側變化,而在細微處亦顯奇險之態。中宮緊收,外勢伸展,字形妍美而又顯篆籀之氣。幽緩舒和,正欹互參,力避楷書之刻板,加之線形粗細變化,尤顯儒雅、沖和,善變與巧思更展現得淋漓盡致。結體面貌亦出于顏真卿行書《爭座位帖》及《祭侄文稿》,但展促之勢,卻取自“二王”手札,抑或參以王羲之《圣教序》,然而更似《爭座位帖》《祭侄文稿》。如“是”字,結構中收,捺畫舒展,顯寬博之狀。如熔金出冶,隨流成形,有疏有密,有開有合,收放自如,不復以姿媚為念,亦無裝腔作態。雖然顏真卿之行書結構已隱含在字里行間,但結字顯然不如《爭座位帖》而顯平和穩定,明顯予以了大幅調整,多參碑意及“二王”行書筆意。
三、章法密而不塞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云:“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象跡,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5]可見,章法是書法作品的大局與統率,書寫時務必處理好字中之布白、字間之關系、行間之穿插,點畫之間要顧盼呼應,字與字之間或明連或暗連,行與行之間或遞相映帶,或神完氣暢,抑或精妙和諧,于是產生“字里金生,行間玉潤”的藝術效果,或顯“錯彩鏤金”之美,或具“芙蓉出水”之自然。
此作七行而下,單字間隨機應變,微微跌宕,于穩中搖擺,令人無窒息之感。上下之間,或筆斷意連,或縈帶牽絲,不雕不琢,由絢爛至平淡又復歸于樸素。不激不厲,若微波中見浪打;不溫不火,如夕陽中見風雨。字組破寧靜,筆勢定乾坤。以茂密取勝,翻側俯仰;大小疏密,于錯落起伏間相映成趣。從第一字至最后,起承轉合而行行富動態,不曲不直而又有跳躍之感。所謂“正極奇生,奇不反正”是也。
四、墨法燥潤相間
宋姜夔《續書譜·用墨》云:“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6]清包世臣《藝舟雙輯·述書下》云:“畫法、字法本于筆,成于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沉,筆飄則墨浮。”[7]用墨法往往因時或因人而異,如董其昌擅用淡墨,劉墉喜用濃墨;又常因書體風格、紙張性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此書作因字小,墨不易演繹,通篇而下,難以飛白;但燥潤相間而不失風神,以潤取妍,以燥造境,濃而不滯,帶燥方潤。筆蘸墨寫容易瘦,何況小字不易辨。此作翰動而墨淡,淡而生澀,崇尚自然,禪意逼出。
五、結語
一言以蔽之,蕭云從不僅繪事登峰造極,且書法亦能博涉多優。以行草為例,亦俯貫八分與篆籀。無論用筆與結字,還是章法與用墨,即使未能盡善盡美,亦不亞于明末專攻書翰者。畫家之中,亦可與弘仁之輩相抗行。弘仁書法瘦勁簡潔,線條爽利,轉折處或圓或露,棱角分明;筆勢峻峭方硬,布局精密,結構嚴謹,墨法滋潤。而蕭云從書法初看似覺平淡,細賞則其味無窮,全無俗氣,使人俗慮盡消,有山林野逸、軒爽清秀之氣質;筆筆有取法,字字有來歷;初看似顏真卿之風格,細觀又為“二王”法所囿;既取雄悍于北碑又浸淫于南帖,無跡可尋,似曾相識又陌生。正如其《題古木高賢圖》所云:“誰探根九淵,氣虛涵太清。”[8]此言可喻其人,兼喻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