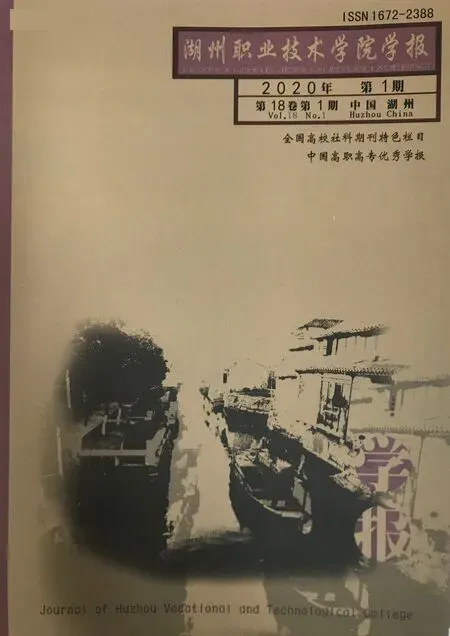龐德英譯本《華夏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 *
褚慧英 , 金美蘭
(湖州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年)是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是西方意象派詩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創作的詩歌,尤其是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品,在世界詩壇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成為西方現代詩人汲取創作靈感的重要源泉,更是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典詩歌和中國文化元素的跨文化傳播。本文嘗試以英譯作品《華夏集》(1)祝朝偉:《構建與反思:龐德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90頁。(Cathay) 為跨文化研究個案,從譯作對詩人自身創作的影響、對西方現代詩歌語言范式的轉變及詩歌抒情方式的轉變三個維度,探析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所做的創造性翻譯和創新性傳播,為推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融入世界文學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一、20世紀《華夏集》的跨文化傳播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種語言背后都有各自的文化支撐。翻譯作為一種語際轉換手段,實際上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行為,是一個實現東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所以,詩歌翻譯本質上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的跨文化傳播活動。龐德通過美籍東方文學學者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的手稿,邂逅東方文學和中國古典詩歌。他從150多首詩歌和注釋中精心挑選了19首詩歌進行“二次創作”,涉及李白、陶淵明、王維、郭璞等中國詩人的作品。1915年4月,英譯本《華夏集》問世,在西方讀者中獲得如潮好評。艾略特(T.S.Eliot)的評價是:“龐德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豐富了英語詩歌,是20世紀詩歌的杰出典范。”[1]xvi-xvii祁德爾(Mary Paterson Cheadle)認為:“龐德的漢英翻譯抓住了作品的神韻。”[2]30
“跨文化傳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間以及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活動,以及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流動、共享、滲透和遷移的過程。”[3]4這個概念中的要素,對應了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的傳播者、訊息、媒介、受眾和傳播效果[4]14,即傳播者發出訊息,通過一定的媒介渠道到達受眾,引起受眾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的變化。其中,傳播效果是傳播四要素里最終也是最關鍵的一環,直接反映了跨文化傳播活動或者說翻譯活動的最終成效,是跨文化傳播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傳播效果有短期的、直接的和微觀層面的,也有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和宏觀層面的。有的傳播能改變受眾的態度、觀念和思想等,甚至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進而推動社會變革和文化變遷。只有在正確的環境中使用正確的傳播策略,才能產生“強大的效果”,這種效果并不能普遍地或簡單地產生[5]308-309。
龐德的《華夏集》恰是在當時的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創造性的翻譯方式,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在西方深入人心,促使中國文化對英美文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1954年,由奧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編寫的一本廣為流傳的現代英美詩歌選集《袖珍本現代詩》(A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收入了《華夏集》中的《長干行》(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全球各大圖書館幾乎都收藏的大部頭美國文學集《諾頓美國文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的各個版本也收入了這首詩。可以說,《華夏集》使中國古典詩歌融入了西方主流文學圈,是跨文化傳播的成功案例,為中國古典元素的跨文化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華夏集》的翻譯特質
20世紀60年代,尤金·奈達(Eugene A.Nida)把通訊論和信息論的成果運用在翻譯研究中,認為語言的理解是開放的,翻譯的效果取決于兩種語言最大程度上的“功能對等”[6]120,其實質是構成了翻譯學和傳播學的互相結合。此后,許多西方學者把這種理論應用到翻譯與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龐德用中國古典詩歌簡潔明快的語言范式,客觀精準地向西方世界呈現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美景和壯闊情感,這恰好同奈達的解構主義的現代認知翻譯方法不謀而合。
(一)對自身創作產生的影響
龐德是意象派的領軍人物,其意象主義主張大多來自于中國古典詩歌和自身詩歌創作的結合。龐德雖不精通中文,《華夏集》也是其通過費諾羅薩的手稿翻譯而來,然而他熟知其他多國語言,對語言所承載的意義和文化有一定的把控能力。通過研究漢字與拼音文字的關系,他發現兩者有著很大的不同:漢字的象形、會意、指事功能,使它與其所代表的實物或現象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系,翻譯的過程是一個創造性的“二次創作”過程。對龐德的詩學與譯學的關系,謝明做過這樣的評述:“龐德的翻譯激勵并加強了他的詩歌創作,而詩歌創作又反過來引導和促進了他自己的翻譯。龐德的詩學基本上是翻譯詩學,他為20世紀詩歌翻譯的本質和理想重新下了定義。”[7]204《華夏集》作為龐德的代表譯作,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使他的許多詩歌創作都有中國古詩的影子。意象并置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技巧特征,在龐德的《詩章》中大量出現,如《詩章》第49頁:

Rain;empty river,a voyage,雨;空江;行旅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凍云火,暮色中大雨①①蔣洪新:《龐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4頁。
詩句中沒有出現一個動詞,雨、江、行旅、火、云和暮光等意象詞并置寫景,非常簡潔明快,這正是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模仿。作者采用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并置的手法,留給了讀者無限的解讀空間,從而激發了讀者的想象力,這成為龐德詩歌語言的一大亮點特色。
在翻譯模仿中國古典詩歌的過程中,句法等中國詩歌的其他要素也被龐德引入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例如,脫體句法(disembodiment)(有意模仿漢語原詩的無冠詞無系詞的句法)[8]232-233也出現在《詩章》第4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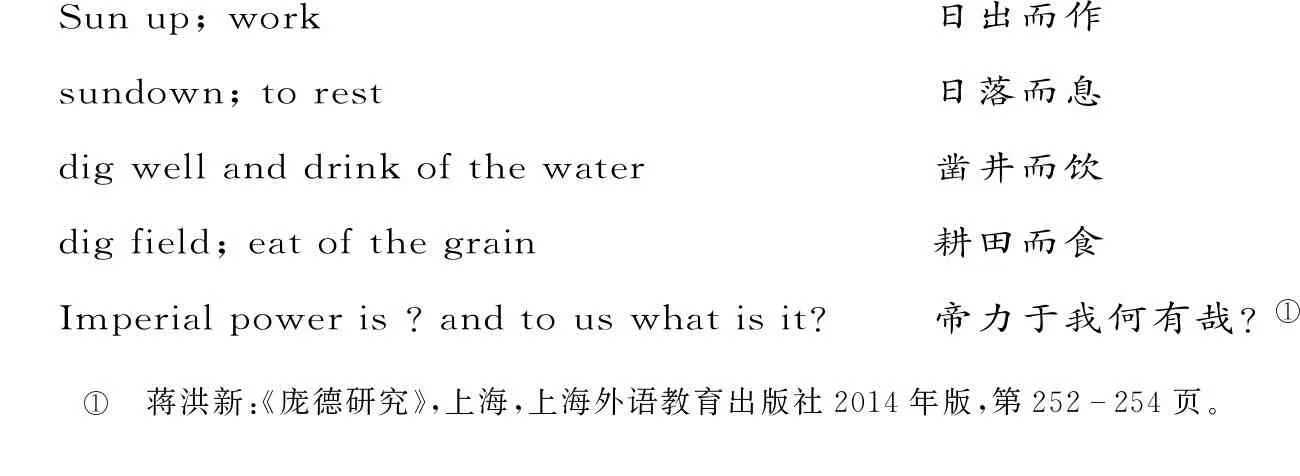
Sun up; work日出而作sundown; to rest日落而息dig well and drink of the water鑿井而飲dig field; eat of the grain耕田而食Imperial power is ? and to us what is it?帝力于我何有哉? ①①蔣洪新:《龐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4頁。
龐德此詩略去了一部分冠詞,不用指示代詞和主語,比如sun前面無冠詞,work前無主語等,人稱時態都不確定。在此詩中,中國古典詩歌的抽象、簡潔、模糊一覽無余。
(二)改變了西方現代詩歌的語言范式
跨文化傳播的有效性通常建立在譯者的立場和態度上,更取決于受眾民族對他族文化的強烈要求或內在需要。龐德把讀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因為翻譯所面對的讀者是同時代的讀者,所以譯者必須調整思路,改變策略,譯語必須符合現代人的思維方式、閱讀習慣和語言規范,表達應該是自然、流暢、凝練而具體的。如果用原來的語言規范約束譯語的表達,譯作不可能做到完全與原文“對等”。唯有將中國古典詩歌進行現代化轉型,將中國古典詩歌的特殊文本翻譯成通俗易懂的現代詩體,才能滿足西方讀者閱讀東方文學的需求,并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因此,“自由詩運動的方向之一,是以中國方式寫作,即使沒有費諾羅薩,沒有龐德,為當時流行的直覺審美所引導,這也是一個注定要探索的方向。”[9]196
基于這種有效性的策略,龐德的中國古典詩歌英譯在客觀上促進了20世紀初的英美詩歌的現代化轉型。20世紀初,美國的政治經濟飛速發展,引發了思想觀念﹑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嬗變,尤其是在狄金森和惠特曼逝世以后,美國詩人競相效仿英國維多利亞的詩風,過分“講究措辭謀篇”“矯揉造作,凄婉多情,有時甚至無病呻吟”[10]45。浪漫主義的不實文風以“自我”為中心,構建自我的浪漫世界,追求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唯美主義文學繼承了浪漫主義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但喪失了其積極的批判精神,企圖借助藝術的自足性和娛樂性來逃避現實。而龐德則以西方文化規則和話語方式,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本土化改造,實現了它的“重建”與“轉化”。以《華夏集》為主導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漸漸推動了英美詩歌語言的變化。中國詩“注重‘意象’‘神韻’‘簡潔’‘音樂’等”,恰好與龐德的“不要用多余的詞”“不要沾抽象的邊”“不要用裝飾或好的裝飾”的詩學觀不謀而合[11]4-5。龐德用樸素平實﹑親切自然的語言風格替代了辭藻華麗﹑奇特花哨的維多利亞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詩歌典型特點,打破了維多利亞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請看譯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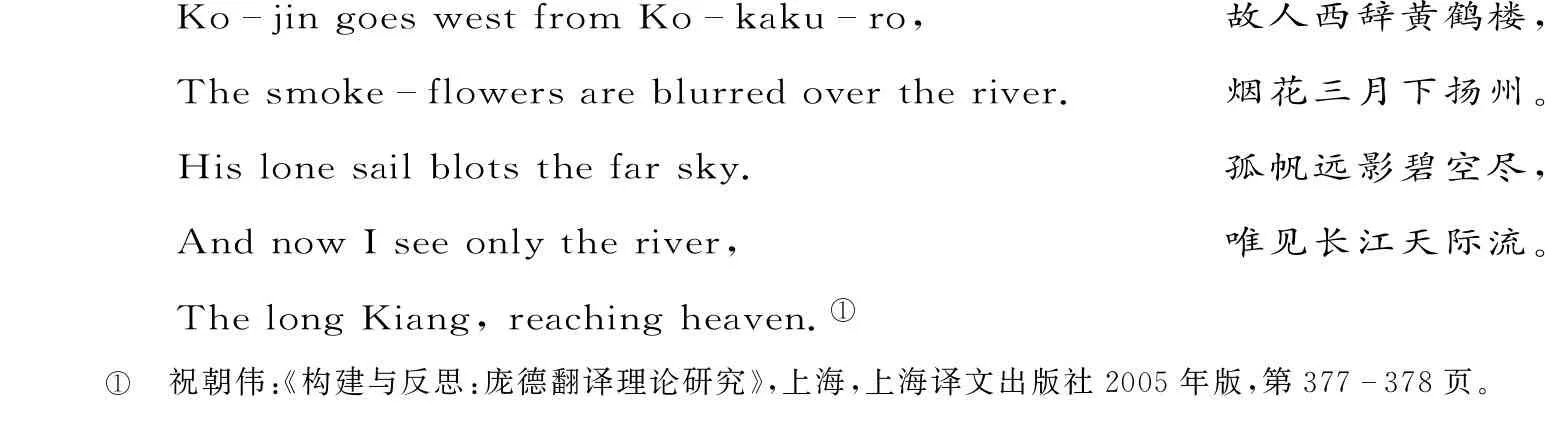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故人西辭黃鶴樓,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煙花三月下揚州。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孤帆遠影碧空盡,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唯見長江天際流。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①①祝朝偉:《構建與反思:龐德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378頁。
在此譯詩中,沒有多余的形容詞的堆砌,每一個詞都是為了客觀呈現。中國古典詩歌式的簡潔樸素﹑自然清新﹑用詞精確﹑準確表達詩人情感的特質,替代了當時英美詩壇流行的維多利亞詩歌式堆砌形容詞﹑充斥著多余的抽象詞的浮華之風。以《華夏集》為代表的詩集在英美詩歌現代文學轉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借中國古典詩歌的東風,自新詩運動起,英美現代詩逐漸變得明快簡潔,這與中國詩的影響分不開。
(三)改變了詩歌的抒情風格
在跨文化傳播活動中,傳播者對信息進行收集﹑選擇﹑加工和處理,都包含著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所以,跨文化傳播活動也是一種跨文化創造活動。當本土的某種文化勢力要顛覆既定的秩序時,往往會借用翻譯這種跨文化傳播工具進行創造,以他山之石攻玉。以色列學者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曾指出:當翻譯文學處于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的時候,翻譯文學就成為“革新力量的組成部分”,因而“常常跟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聯系在一起[12] 193。龐德也說:“偉大的文學時代也許總是偉大的翻譯時代;或者緊隨翻譯時代。”[13]3
一般認為,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導,尤其是儒家的倫理,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儒家敬天禮地,這個“天”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人頭上的天空,天地始終沒有擺脫其物質性與自然性。儒家文化對現世生活的執著,使得世俗性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特征。這種世俗性特征對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影響甚大,而且是唐詩、宋詞等各種文體的淵源。儒家敬重天地萬物,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超越生命的自然主義,使中國人與自然的關系非常親近,因而,中國的自然文學特別發達。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體現在中國文學中,人與自然、物與我是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學的物質性與自然性在中國古代意象概念的形成過程中都有所體現,如魏晉文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他們的作品中,自然與山水是交融的,詩人親近自然,寄情山水。意象主義與其如出一轍,不說教,而是通過客觀呈現意象和情景實現情感表達。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學有許多可與西方現代文學認同的處所,中國詩歌直接催生了現代西方的意象派詩歌。”[14]67
在20世紀初的歐洲詩歌界,從文學背景上看,長時間受制于舊的詩歌范式,本土性或本位性突出,保守懷舊,專注于緬懷失落的歷史光輝,渲染鋪陳傷感的情愫。這樣的狀態壓制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亟待顛覆。西方文學的發展借助于異域文學,批判本國文學,既而開辟了文學發展的新道路。以龐德為代表的詩人們,正是借助源于中國古典詩歌的客觀呈現意象和情景實現情感表達的方式,來代替不注重客觀呈現﹑為抒情而抒情的維多利亞浪漫主義詩人的作詩方式,從而實現了對維多利亞詩風和唯美主義的批判和反撥。
受龐德中詩英譯間接或直接的影響,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秋日》(Autumn)中,通過客觀精確地呈現意象和情景,如枝葉﹑墳墓﹑一大伙人﹑道路﹑老人﹑山羊﹑草等,獲得了詩歌美和情感的釋放。中國的文化遺產在域外的現代文學話語中流傳,有力地推動了跨文化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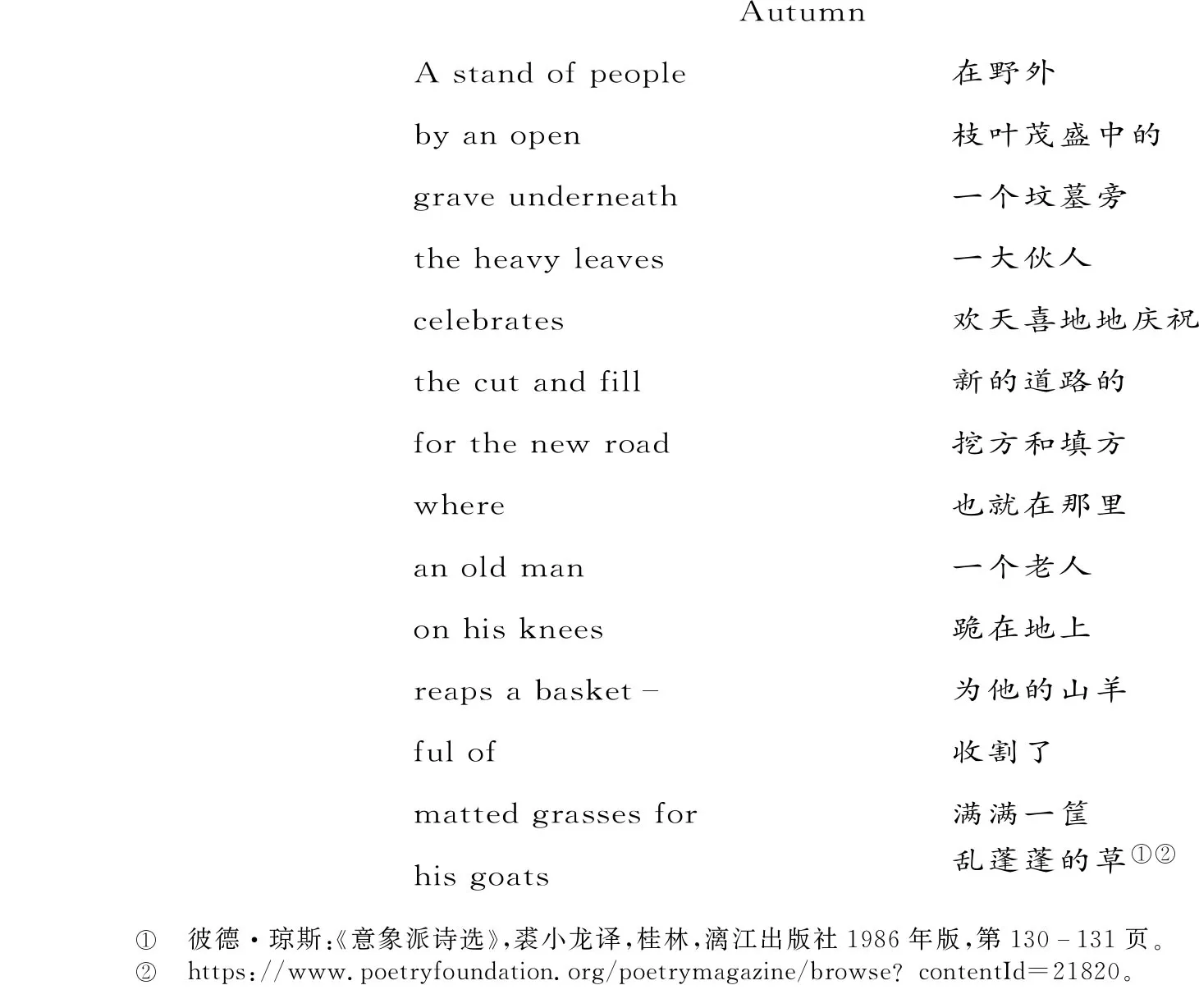
AutumnA stand of people 在野外by an open枝葉茂盛中的grave underneath一個墳墓旁the heavy leaves一大伙人celebrates歡天喜地地慶祝the cut and fill新的道路的for the new road挖方和填方where 也就在那里 an old man一個老人on his knees跪在地上reaps a basket為他的山羊ful of收割了matted grasses for 滿滿一筐his goats亂蓬蓬的草①②①②彼德·瓊斯:《意象派詩選》,裘小龍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頁。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browse?contentId=21820。
在洛厄爾(Amy Lowell)的詩歌《秋天》(Autumn)中,通過葡萄藤﹑葉子﹑水﹑月光和銀等意象的疊加,使得“詩中有畫”:

Autumn
總之,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傳播是一種軟性且又浸潤式的傳播。一種文化的跨國傳播不可避免地要學習、借鑒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長,并在相互影響中得到發展、豐富并提升。龐德以其獨特的思維、創新的方式,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人文知識、審美方式和價值取向,創新性地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為經典化了的中國古典詩歌轉化為英語詩歌并融入世界文學,做出了無可替代的開拓性貢獻。《華夏集》的譯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使得中西文化碰撞并相互影響;同時,中國古典詩歌意象主義的創作手法和漢字形象表意的特點,賦予了龐德意象主義的詩學主張,對西方現代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為后人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和翻譯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