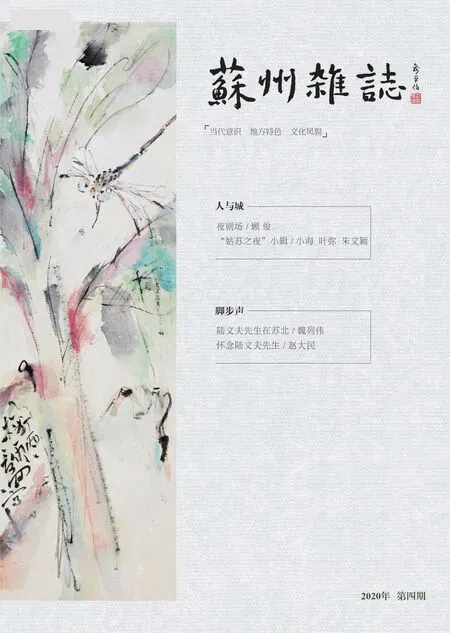水之靈
凌子

☉ 龍蝦
龍 蝦
我曾與一只龍蝦對峙過,彼此狠狠地對視。
那時十九歲,在一所鄉村師范學校讀書。學校周圍是田,校門正對京滬鐵路。雖然來回要坐火車,但家鄉事實上并不遙遠。
青春與鄉愁總愛把事實夸大,夸大到最后,就是呆呆地看亂云飛渡,想象千萬里外與千萬年后,心事浩蕩。那只龍蝦仿佛就在這時刻出現,出現在那條淺水渠中。
水清淺而渠深邃。渠底鋪排著落葉,那種鐵道旁常見的水杉針葉,很纖麗。龍蝦的窩就安在渠一側,光滑而碩大。我看云時,它可能在抬頭看我;我低下頭時,則看見它不慌不忙一退縮,洞口的靜水由此畫出一水圈,如詩人激情揮灑后那么一吐煙圈。這一定是只久經歷練的小龍蝦,由此當尊稱它為“老龍蝦”,它在揣摩我?
龍蝦的須挺長,恰如京戲武生帽上抖動的花翎,威風。龍蝦的螯更威武,擺動著,像要撕裂敢擋眼前的一切。但那是未經世面的小龍蝦相,多為龍蝦中的“楞頭青”。與我對視的老龍蝦,沉靜得很。它蹲守洞口,身子三分之二藏洞中,穩穩當當,如老相公端坐太師椅。長須垂拂,任由飄落的杉針擦拭。重頭戲來了,老龍蝦的雙眼猛地彈出;剎那又緊急定格,如兩根裝有探頭的天線直挺挺豎著。好吧,對峙開始!我想說,這般倨傲的注視不可笑嗎?但龍蝦不會笑,很認真地堅持著。我想問,你想看見什么?但龍蝦懶得作答,也許它只是想看到它想看到的,并在可能的范圍內把看到的看穿、看透、看破。
那時我發著文學燒,好做白日夢,對高深莫測的哲學故作親近。于是,在詩找不到遠方的落寞中,我與那龍蝦杠上了。我也想知道它來自何方,最終將去何方。
列車轟鳴,夢境繽紛,杉葉飄盡,雪落一地。
轉眼畢業,回家鄉,那只老龍蝦是否還逍遙一隅,不得而知。
多年后,莫名刮起一股吃龍蝦風。大桶大桶的小龍蝦,擺放在店堂門口,灰蒙蒙,群螯亂舞,步足糾纏,哪還有一點披盔帶甲、特立獨行的霸王風范?湊近挑揀,盡眼睛細小,眼神猥瑣,看來只有對世界的迷惘與恐懼。
這些都是養殖的。水淺而濁,高密度,“腐殖”。對比之下,真懷疑當年與我展開“哲學對話”的那只龍蝦是不是來自外星球。有一點要說明,我遇見“老龍蝦”時,根本不知其品種,亦不識其名,只覺得屬于蝦一類,又有點像蟹,螯尤其像光溜溜的螃蜞,畸變。
后來,去了盱眙,吃了所謂的“十三香”,但無心再與快樂茍活的龍蝦對視。
后來,家鄉東太湖成功放養了羅氏沼蝦,蝦鉗格外長,色藍瑩瑩,殼體透明肉飽滿,但與小龍蝦顯然不是同類。倒是一種野生的大蝦,殼鐵青,腮部膨大,眼神有點野,人稱“小青龍”,你瞪它,它回瞪你幾眼,略有幾分神似。
老掉牙的文藝理論中,有一句經典說教,叫“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用在節肢動物身上,其實更顯“靈光”。蜘蛛的陰森,蜻蜓的呆萌,蟹的霸氣,蝦的靈動,其實都與眼睛的特異構造有關——復眼,暴凸,滴溜溜旋轉,本為好奇?
龍蝦的眼晴長在觸角根部,據說不靠折射而靠反射觀察事物——如此,審視人類,自然無所謂。忽然懷念起青春,一個民間俗語躍上心頭——彈眼落睛。
未來美好,曾經也出色。
鯉 魚
江南吳地,好像不太吃鯉魚,平日里。
吃鯉魚往往與儀式有關。比如娶親,禮盒里必盛一對大鯉魚,泛溢金紅色,極喜氣,當稱錦鯉,但那是活的,系聘禮。又比如過節,祭祖宗,得上魚,上鯉魚以示鄭重,但不必大,一斤左右即可,俗稱“菜鯉魚”,這是煮熟的,獻祭后自然落在子孫們口中。
鯉魚富貴相。須冉冉動,尾赤紅。“鯉魚跳龍門”,魚化龍,飛黃騰達。這樣的激勵極具沖擊力,當年農家子弟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即視作此。
鯉魚當是龍庭中的魚,是九曲黃河中的魚,孔圣人敬受之,水泊梁山好漢喜食之,上升則為神話,為文化,回歸還是活潑潑的一條魚。
作為水產品,鯉魚絕不名貴,哪怕神乎其神的黃河鯉魚,在一盞江南“莼鱸膾”前也黯然失色。桃花時節的鱖魚,菜花時節的甲魚,均為不可多得的河鮮,當然指“非人工養殖”,跟著時令食。
無論量還是質,我吃過的鯉魚均屬平庸。印入記憶的有兩條。一條是少年時躍入船艙的鯉魚,一條是鄉間親戚網得的抱籽鯉魚。

☉ 銀魚
少年時那條挺有意思。稻收季節,船在大蕩里搖行,蕩面寬廣,周邊的稻田一望無邊,夕照下金燦燦一片。我坐在船艙中張望,父親搖著船,不緊不慢。稻不多,堆放在前艙與船頭,偌大的中艙空著,仿佛預備著“請君入甕”。云淡風清,新鮮的稻谷香若有若無。將過竹籪,父親緊搖幾下,水流陡急,唰,唰啦啦,船底觸籪,水面嘩然,一條魚莫名其妙躍入了船艙。啪啪啪,直蹦到我腳邊。徒然掙扎后,魚躺平了,唇吻翕張,唇邊的魚須不服氣地抖動著。父親瞥了一眼,高興地說,這是一條大鯉魚。我用手按壓著它,感覺它像在做夢,是做了一個嘗新谷還是跳龍門的夢呢?鯉魚的眼睛大大的,神情酷似孩子驚醒過來不知身在何處的樣子。
就滋味而言,鄉間親戚網得的那條鯉魚更真切。那是不久前的事,油菜結籽,春意濃到歸結處。親戚家門前有一個塘,塘遠處連著蕩。有水就靈動,野風一吹,心曠神怡。可能是水質好,住戶也不多,親戚就在便利的水面上種了點水紅菱,菱葉間安插了幾張小漁網(俗稱“張吊籃”)。一日,漁網中大收獲,不是鰷、鳑鲏一類小魚,也不是鯽魚、昂刺一類常見魚,而是鯉魚,一條不多見的野生抱籽大鯉魚。正值農忙,親戚把魚宰了,略鹽漬,捎給我們。初,并不以為然。念人家心意實誠,權且紅燒,想不到,肉質竟如此緊致,絲毫沒有鯉魚常有的“泥土氣”。魚脊背足有寸許厚,肋肉肥而不膩,鮮而不腥。食有余,放入冰箱,結成皮凍,次日佐以白粥,吃得不亦樂乎。“小時候”的味道又回來了!
遺憾的是,魚籽經鹽漬,有些“蔫”。一則不飽滿了,二則不鮮亮了。淡水魚中,要數鯉魚籽最好吃,佐以少許腌菜(最佳為腌雪里蕻菜)炒食,魚籽如花菜球一樣緊實又金黃,入口一抿即散,一咬有彈性,那種飽滿的鮮爽勁令人陶醉。不幸鹽漬的魚籽,未能成“醬”,又喪失了生鮮彈性,實屬無奈。腌菜炒食,咸對咸,不吊鮮;蒸食,軟綿綿,無起色。金黃蛻變成灰青色,鯉魚籽好像異化成了鯰魚籽,撇撇嘴,不好吃。
忽憶典故“孔鯉過庭”,慚愧。
閃亮的魚
兩條魚,閃亮,一直在洄游,洄游于江海,也洄游在夢中。
一條是帶魚,一條是銀魚。
魚是水中機靈鬼,無鱗的魚仿佛更添一層神秘色彩,該稱水中精靈?
帶魚生活海中,海之于我的家鄉與童年遙不可及;而晝伏夜出的帶魚,就像一排排垂直的感嘆號,睜著圓鼓的大眼睛,沉穩又靈動地懸置海水深處。
帶魚如長刀,嘴尖尾細長,鋸齒令人懼。帶魚若飄帶,身姿曼妙,銀脂滑溜,閃現似寒星。一捕獲,“不自由毋寧死”。帶魚不屑于亮相,自然不甘心被活捉。
當年,冰鎮能力有限,運到內地的帶魚,多是腌過的,俗稱“咸帶魚”。腌得起硝,呈干柴黃,那是陳帶魚,特別下飯,還宜一小塊一小塊咀嚼著佐酒。農村普遍貧窮,人口多的人家,打牙祭就買帶魚,且專揀作堆賤賣的等外品,一買一小竹籃。因而,咸得發苦的腌帶魚,又多了個“窮帶魚”稱號。肉與鮮魚,品相高貴,除了節日與待客,孩子們是不敢奢望的,而吃“窮帶魚”,做父母的大多表現得大方,不怕你多吃——“咸死你”。好在一年也就幾回。
鮮帶魚的滋味,無與倫比。無論清蒸,還是紅燒,抑或油炸,都出色。特別是俊俏的國產“小帶魚”,清蒸后,銀色不減,鮮而不腥,肥而不膩,筷子一撥,潔白的“柱子肉”(類蒜瓣肉)立現。
帶魚直泊水中的形象,總讓我想到小海馬,想到小海馬睜著童話般眼睛呆萌;帶魚背鰭直立時,也讓人想起馬鬃,想起白練迎風齊刷刷。帶魚的身段骨,硬,疏密有度,儼然一柄雙排梳。
銀魚也洄游(對因地緣阻絕的內湖銀魚而言,至少儲存著洄游基因)。小巧玲瓏,冰清玉潔,有冰魚、玻璃魚等美稱。較帶魚的“長”,銀魚充其量“迷你”,即便所謂的“大銀魚”,也不過一拃長,難怪古人稱其為“一寸二寸之魚”。帶魚披一身銀膜潛伏深海,銀魚則通體透明,如萬千銀線穿梭粼粼波光,毫無城府織就繽紛魚陣。
小河通大河,大河通太湖。小時候,到得一定時節,總能在清澈的活水表層,湍急的清水渠中,目遇那些晶瑩的小精靈。那么無瑕的小身量,卻點綴著那么鮮明的小眼珠——那真是一粒烏黑锃亮的油菜籽啊。傳說,銀魚是投拋到水中的殘羹冷炙所化生,因而古稱“膾殘魚”;又傳說,萬千銀魚是孟姜女哭夫的萬千顆淚珠濺落而化變,顆顆傷心欲碎。前者“出淤泥而不染”,后者“質本潔來還潔去”,文化意義上的銀魚,如蓮藕,無可挑剔。
同帶魚一樣,小小的銀魚也是“氣性”特大,出水即“完結”。死后呈乳白色,如玉似雪。杜甫有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余……入肆銀花亂,傾筐雪片虛。”用“白小”借代銀魚,恰如其分;而“銀花亂,雪片虛”的描摹,亦栩栩如生。
銀魚羹,銀魚炒蛋,簡簡單單,輕輕松松。銀魚的烹調,不必多料理,天生鮮。小孩厭食,一小碗鮮銀魚燉草雞蛋羹,簡直就是藥膳,開胃又可口。“洞庭枇杷黃,銀魚肥又香”。跟著時令食,風味“最江南”。過時,只堪作干貨,曬成“繡花針”,中看不中吃——銀魚曬干就像帶魚腌制,屬無奈,聊勝于無。
魚兒閃亮,靈光閃現。嗅著兒時的味道,鄉愁,或長或短,不就是一尾尾洄游的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