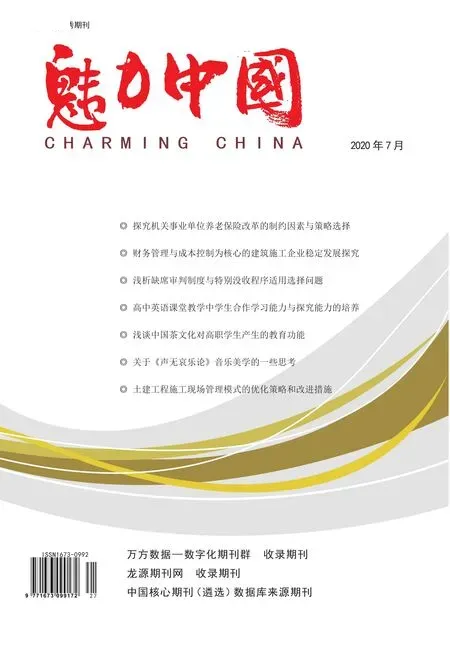“一帶一路”視域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認同
(魯迅美術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一帶一路”是為實現沿線各國經濟文化繁榮發展提出的戰略建議,它不是一條既定的路線,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生態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根植于這條生態鏈上的動態的文化遺產,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底蘊深厚。依托于非遺文化,可以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保持獨立性和特色、在文化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培養國民文化認同感。文化認同是建立在自我認同基礎上的內在認知,是對文化內涵意義的深刻追求。文化認同可以滿足民眾集體身份識別和認同的需求,具有可以產生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一、以“一帶一路”為機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古代,絲綢之路是外交的重要通道,文明史源遠流長,承載了很多優秀的歷史文化。“一帶一路”對于非遺的保護和發展是一個重要機遇。國家之間以合作和分享的態度,共同保護人類文明的傳承和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以文化相對化促成文化平等化,共生共榮[1]。借助“一帶一路”這個平臺,借助現代媒體和互聯網資源,讓本國非遺文化走向世界。通過“一帶一路”發展非遺文化,推動建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一帶一路”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性開發
(一)傳承人與企業、高校合作開發
推動“一帶一路”中非遺傳承人與設計師、設計公司、高校合作,擴大創作團隊,為非遺傳承人傳統的創作內容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文化載體。上海大學何然與寶山非遺項目羅涇十字桃花合作,創作了“繁花似錦”當代設計展(如2.1.1),讓布藝堆畫和非遺完美結合[2]。傳承人從設計師那里了解了多樣的表現形式,從而開拓了思路,設計師從傳承人身上了解非遺精神內涵、起源和技術手法,豐富了設計素材,實現傳統技藝再設計,通過合作程度的不斷深入,形成良性循環。二者合作提高了寶山非遺項目羅涇十字桃花的知名度,創作了優秀的藝術作品,擴大了知名度。
(二)針對非遺的“非物質性” 發展文化旅游業
在“一帶一路”中,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化內容,大力發展依托于人文資源的旅游業,尤其對于“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項目。如充滿魅力的民族節日,具有地域特色的表演等,與旅游業的結合會大力推動旅游經濟的發展,提升特色地域形象,拉動地區經濟發展,使傳承人更加積極地投身于非遺傳承中,使民眾更加參與非遺文化建設中,讓非遺文化重新煥發生機。“一帶一路”中的東興京族哈節和民族特色獨弦琴表演,在當地政府的文化保護和支持下,在哈節期間形成了文化旅游業的飆升,在保護京族人民文化傳承的同時,使游客了解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增強文化認同感[3]。
(三)創立“一帶一路”非物質文化遺產品牌
1.提煉重組文化符號,建立熱門IP。我們可以把非遺的圖案符號融入產品設計中,通過提煉重組文化符號,傳統文化再設計,推出熱門IP。借鑒故宮的轉型方式,即推出故宮IP,大力發展文創品牌。比如故宮口紅(如圖2.4.1),故宮與潤百顏公司合作生產六款顏色,郎窯紅、豆沙紅、玫瑰紫、碧璽色、楓葉紅、變色人魚姬,六款設計靈感分別來自故宮藏品郎窯紅釉觀音尊和洋紅色緞繡百花文夾氅衣、豇豆紅釉菊瓣瓶和月色緞平金銀繡水仙團壽字紋單氅衣、鈞窯玫瑰紫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和黑綢繡花蝶竹柄團桃紅碧璽瓜式佩和廣繡鶴鹿同春圖、礬紅底白花蝴蝶紋圓盒和明黃色工裝裙繡、胭脂水釉梅瓶和淺綠色工裝裙[4]。依托于故宮文物形象再設計,打散重組文化符號,使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通過打散重組創新文化符號,建立熱門IP,擴大產品受眾,將文化內涵轉化為生產力。故宮作為一個熱門IP,從一張歷史文化名片,變成人們心中的一抹情懷,真正鮮活起來,有助于培養人們的文化認同感。
2.“奢侈品”定位下的品牌發展方式。可以選擇開辟高端消費的“奢侈品”生產線,由于部分非遺手工工藝復雜,耗時較長,人力資源投入大,藝術價值高,非遺產品本身可以將宣傳推廣轉向高端消費群體。一方面,高級私人訂制是一種可行的方式,手工工藝可以滿足消費者定制圖案的需求,發展個性化多樣化的產品,尊重客戶內心體驗和時尚追求。另一方面,非遺應該打開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的渠道。南京絨花非遺傳承人趙樹憲和藝術家JUJU WANG 合作創作阿瑪尼旗下帕爾馬之水全球限量版絨花禮盒,以天然蠶絲為原料,銅花為骨架,使非遺絨花正式進入高端品牌。堅定做民族品牌,現在淘寶上的銷量每月可達百萬,借助品牌力量打開銷量,推動文化傳承。
三、“一帶一路”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性傳承
(一)設立專項資金,引入民間資本
設立“一帶一路”非遺專項資金,政府主持建設“一帶一路”非遺圖書館、博物館,宣傳文化內涵、采訪拍攝收集文化史料;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絡的數字博物館,對資料進行數字化分類整合管理;建設“一帶一路”國家手工藝全國、世界巡覽和各省市文化展館,提供非遺傳承人展示和交流的平臺,通過國家建設完成對非遺文化資料的整合和基礎宣傳。在此基礎上,引入民間資本,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提高非遺文化產品質量、提高科研和設計投入,提高市場競爭力,增加產品附加值。擴大“一帶一路”非遺文化的受眾人群,實現文化認同。
(二)擴大傳承范圍,數字化管理保護
與傳承人深入溝通交流,對傳承人進行表彰嘉獎,拓寬傳承渠道,單一的家族傳承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生活,需要擴大傳承人范圍,可采用基地性傳承方式、教育性傳承方式。藏羌族楊華珍成立了阿壩州藏族傳統編織、挑花刺繡協會和羌繡協會,帶領當地的婦女靠手藝生產自救,并且在傳統編織內容中,添加了手提包、鼠標墊、茶杯墊等現代載體。她的團隊已收集藏羌族服飾圖案600 種以上,并編寫教材《藏羌族織繡培訓教材》,與此同時,與星巴克合作設計信用卡圖案“萬靈載溢”山茶花(如圖3.2.1),線條向四周延伸,自由生長,表達了羌族人對自然淳樸的崇拜,有一種不斷向上生長的正能量。與植村秀合作設計明星產品瓶上的圖案,八種植物成分,象征青春和不朽[5]。藏羌織產品創造收益,擴大知名度,為其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同時通過消費者對非遺了解加深,提升文化認同感。
除了對傳承人的保護培養,還要培養專業人才,實現數字化管理保護非遺文化,科學地對非遺資料進行收集整理、分類記錄、開發整合。技術上開發多種資料檢索方式,比如民族、圖形紋樣、歷史文化、手工藝、實踐課程等,在良好的資源整合基礎上,還可以與多學科發展關聯。此外,可增加沉浸式、交互性強的文化展覽方式。通過數字化地演變、模擬發展趨勢,將數字化材料作為開發式保護的重要資源,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6]。
(三)加強非遺文化制度保護、法律建設,保護知識產權
針對《非遺法》頒布三年卻未增執行過一例的立法現狀,需要重新思考結合非遺發展具體情況和現行國家立法制度重新調整、試行、規范、普及。針對非遺文化設置特別保護機制,規范劃分抄襲標準,可組織成立對非遺文化了解程度高的專業小組,借鑒其關于抄襲界定標準的專業意見。對知識產權界定清晰,合理保護,規范市場行為,使非遺文化在市場競爭中健康發展。
四、總結
“一帶一路”非遺文化的保護工作,有助于“一帶一路”形成沿線友好互助國家關系。推動非遺文化的產業化發展也有助于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尋求企業和高校合作開發,實現傳統技藝再設計;創新非遺的文化內容和表現方式,滿足現代人信息接收方式;建立圍繞非遺的文化旅游業,拉動地方經濟發展;創立“一帶一路”非遺品牌,打散重組創新非遺文化符號。在開發性保護和繼承性保護的同時,兼顧保留非遺文化本真,實現文化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在發展過程中,通過非遺文化經濟的發展和非遺民族文化身份的獨特表達,提升國民文化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