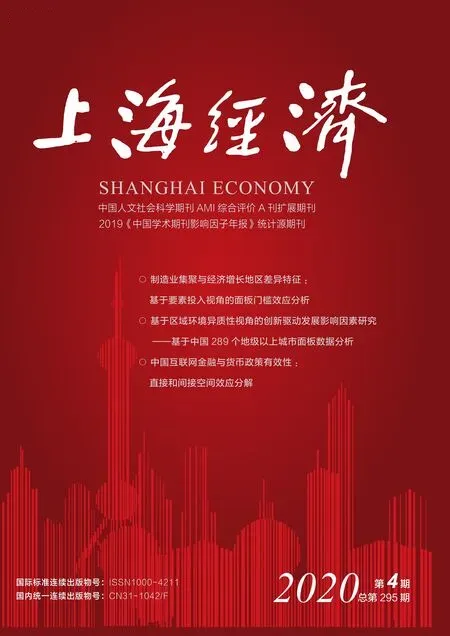基于區域環境異質性視角的創新驅動發展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中國289個地級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分析
尚勇敏 ,宓澤鋒 ,王振
(1.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上海 200020;2. 浙江工業大學經濟學院,杭州 310014;3.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 200020)
一、引言
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深化,科技創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受到重視(樊杰、劉漢初,2016)。國內外學界紛紛強調建立區域創新體系(Andrés R P & Riccardo C,2008)、進行知識創造(Iacovoiu V B,2016)、增強自主創新能力(Gu S & lundvall B ?,2016)等途徑推動區域經濟發展轉型,政策制定者也深信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和應對全球挑戰的先決條件(Kabia A B et al., 2016)。創新驅動發展的效果存在差異,不是每個地區都能依靠創新實現成功轉型(Diebolt C & Hippe R,2016),部分重視科技創新的地區卻被“引進技術—技術落后—引進技術”的發展路徑鎖定,如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雖然大力引進技術,但未掌握關鍵技術而導致對外部的“技術依賴”。由于創新要素未能與本地創新環境疊加,導致經濟增長沒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張月,2008)。中國將科技創新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然而不少地區卻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出現走偏或者陷入發展困境,如無錫過快追求新興產業,由于受外部環境和地方產業基礎影響,而陷入發展困境。好在近年來依靠發展集成電路產業,該地實現了經濟的再次復蘇,這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敲響了警鐘。隨著20世紀末強調創新地理空間集聚和根植性等內容的“新區域主義”理論形成(苗長虹、樊杰、張文忠,2002),以及金融危機以來強調區域如何在變化的自然、社會、經濟環境下恢復、適應和轉型的區域彈性概念的提出(周洲、王琛、郭一瓊,2016),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重視區域環境異質性在區域經濟發展轉型中的作用(孫久文,2016),這也被 Martin & Sunley(2011)稱作經濟地理學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但在創新驅動發展研究中,研究切入點和政策路徑的提出依然存在“一刀切”的情形(“one-solution” scenarios),一些學者呼吁應該關注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差異所造成的影響(Martinez G T,2014)。
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顯示,創新驅動發展其作用機制與效果具有復雜性,創新驅動發展并非總是奏效,需要高度關注創新要素與本地環境的有效結合。一個地區依賴創新實現轉型發展很大程度上由區域環境所決定,創新資源需要與本地資源稟賦特點相適應,并嵌入當地區域環境,才能提高創新效率(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馬雙,張翼歐,2019)。如果忽視了區域的地方性因素,科技創新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引導就會跑偏。區域環境異質性使得同樣的創新要素在不同的地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T?dtling F,1992),如中國各地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效率相差巨大,東部地區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王慧艷、李新運、徐銀良,2019;陳鵬,羅芳,2019);上海在長三角16市中的R&D投入最多,但其產出效率排名卻位居最末(曹賢忠、曾剛、鄒琳,2015)。這反映出創新驅動發展對區域環境具有依賴性,創新驅動發展需要重視區域環境異質性的影響,而當前各地鼓勵創新發展的產業政策往往忽視產業特征、區域環境特征,導致政策失效等問題明顯(林蘭、曾剛、呂國慶,2017)。中國區域差異巨大,在大國經濟背景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那么,創新驅動發展效果存在何種地理空間差異?區域環境異質性對創新驅動發展的影響機制與影響效果如何?何種區域環境的區域更適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本文基于區域環境異質性視角,分析其對創新驅動發展的影響機制與影響效果,探討創新驅動發展的區域環境條件,有助于推動區域環境異質性下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理論的發展,也有助于為我國因地制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二、區域環境影響創新驅動發展的作用機理
區域環境異質性是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區域環境因子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構成了區域環境的多樣性與復雜性。20世紀末以來,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強烈地引起了社會經濟要素的空間重組和地理集聚,全球經濟地圖發生深刻變化,并導致區域環境異質性的加強(陸大道,2011)。區域環境異質性主要有要素稟賦環境異質性、發展水平不平衡、社會文化與制度差異等三個區域環境異質性理解視角(彭薇、馮邦彥,2013)。對于區域環境異質性的解釋盡管存在分異,但賦予其自然的、社會的、經濟的屬性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區域環境異質性也導致創新以及創新所引發的經濟發展似乎也有空間選擇性(Capello R & Lenzi C,2012)。盡管信息、通信和運輸實際成本下降,但全球互聯的知識經濟距離關聯性卻持續增加,創新要素也傾向于集聚在特定的行業、區域等(De Groot H L F et al.,2007)。究其原因,創新依賴于協同,而協同創新需要維持在特定空間內,創新要素在少數區域集聚通常比在多數區域分散分布產生更多的創新行為和更大的經濟效益,要素在地理上的空間集聚或毗鄰更容易催生創新(Su Y S & Chen J,2015)。
創新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的研究,其內涵也在不斷拓展,不再限于發明與發現,更關鍵的是發明或發現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Uchechukwu U et al.,2016)。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對于經濟持續增長將形成乘數效應(Iacovoiu V B,2016),還將帶來更加多元化的經濟形式,為就業、生產力、出口、外匯等的增長提供支持(Uchechukwu U et al.,2016),進而推動了創新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一批學者對創新驅動發展內涵進行了解析,主要反映為科技創新推動發展方式從依靠資源要素驅動向依靠知識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轉變(徐國祥、陳燃萍,2019)。學術界對創新驅動發展內涵解析主要表現三方面特征:一是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二是創新驅動發展是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知識創新等的綜合協同;三是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鄭燁,2017)。由于創新驅動型經濟總是比資源驅動型經濟更具競爭性并將更少出現衰落的可能(Oluwatobi S O,2015),科技創新也被普遍認為是“解鎖”經濟繁榮之門的關鍵“鑰匙”和向更具競爭性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途徑,不管是在企業層面還是區域或國家層面亦是如此(Todericiu R & ?erban A,2016)。大量國內學者也提出區域創新能力決定了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方向,區域經濟發展必須將科技創新放在首要位置,實現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曾剛、尚勇敏、司月芳,2015)。
創新驅動發展是一個受多因素共同影響的復雜系統過程。依據Storper的“技術—組織—地域”三位一體(holy trinity)理論,技術、組織和區域相互關聯并進行著共同演化,區域環境的差異使得各地區技術、組織、區域共同演化過程和結果也存在差異,并導致創新驅動發展出現分離。區域環境在地理空間上具有不均勻性和復雜性,這就造成創新驅動經濟發展轉型效果在空間上的異質性。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在于有利于科技創新和組織變革的區域環境(尚勇敏、曾剛,2017)。區域環境對創新驅動發展的影響機制有兩種解釋觀點,一是創新要素論,即將區域環境視為創新要素,創新是要素投入的結果,區域環境通過提供創新驅動發展所需關鍵要素(如人才、資金等)促進創新更容易實現;二是創新效率論,即區域環境將影響創新驅動發展的效果,包括基礎設施環境、制度環境、開放環境、生態環境、經濟基礎環境等,區域環境將優化、整合區域內創新資源,提高創新要素效率,形成區域創新合力。基于上述觀點并結合相關研究,本文認為,區域環境系統包括強調資本、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創新資源環境、人力資本環境,以及強調創新所依賴環境的基礎設施環境、制度環境、開放環境、城市生態環境以及經濟基礎環境,共7類區域環境因子,這也是本文開展區域環境異質性對創新驅動發展影響研究的理論出發點。
三、研究設計
(一)區域環境指標體系構建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全要素生產率與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選擇長期受到學者的關注,多數研究表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是廣泛和多樣化的(劉建國、李國平、張軍濤等,2012)。上文將區域環境因子分為基礎設施環境、創新資源環境、人力資源環境、制度環境、對外開放環境、經濟基礎環境與城市生態環境等7大方面,本文基于這7方面來擇取相應的指標。為避免同類目指標間易產生的多重共線性,本文在各領域中選取1個代表性指標。① 基礎設施環境方面,城市道路交通是基礎設施的典型指標,本文用指標“人均鋪裝道路面積”來代表基礎設施環境。② 創新資源環境方面,良好的創新資源稟賦有利于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和城市經濟外部性的出現(林蘭,2016)。創新投入創新資源環境的重要體現,R&D投入與政府財政科技支出是學界常用的兩大指標(宓澤鋒、曾剛,2017;宓澤鋒,2019),由于本文需要采集地級市層面長時間段的面板數據,R&D投入數據較難獲得,因此選用“政府科技支出占GDP比重”來表征創新資源環境。③人力資源環境方面,在校大學生人數被認為是城市人力資源的典型代表(李震, 楊永春,2019),因此本文用“在校大學生數占總人口比重”來表征人力資本環境。④制度環境方面,良好的政府支持資源和制度支持有利于創新主體獲取創新資源和創新伙伴,增強區域創新能力。本文借鑒宮汝凱(宮汝凱,2015)等的研究,認為財政不平衡度(通過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的比值)極大的影響著政府挖掘地區創新潛力的能力:如果財政狀況較好,則地方政府有較大的自由度和精力去支持科技創新發展;如果財政狀況較差,則地方政府更需要在維持地方穩定發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進而本文選用“財政不平衡度”來表征制度環境。⑤ 對外開放環境方面,開放環境影響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空間結構和產業結構重組,對外貿易依存度和外商投資占GDP比重是反映開放環境的重要指標,由于缺乏289個城市長周期貿易依存度數據,本文采用“FDI占GDP比重”來表征對外開放環境。⑥ 經濟基礎環境方面,人均GDP一直是學界公認的表征經濟基礎的重要指標,因此選用“人均GDP”來表征經濟基礎環境。⑦ 城市生態環境方面,綠化是城市生態環境的基礎,也是表征這一方面的重要指標,因此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來表征城市生態環境。綜上,本文的指標選擇如下:

表1 區域環境指標體系
(二)研究對象及類型區劃分
本文研究樣本為全國289個地級以上城市(剔除三沙、儋州、拉薩等數據嚴重缺失城市)。區域環境因子是區域類型劃分的重要考量,區域環境的不同將對創新驅動發展作用效果產生影響。為聚焦本文主題,突出區域環境異質性,本文依據區域環境指標體系,在Stata軟件中運用K中位數聚類方法對中國289個城市進行聚類分析,共得到4種類別區域。類型Ⅰ主要由中西部地區的一般城市組成,該類型區域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各項區域環境因子總體呈現出相對較低水平的均衡,除政府科技投入占GDP比重外,各項指標均位居四類區域的第3位。類型Ⅱ主要為中西部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該類城市除政府科技投入、FDI占GDP比重外,區域環境因子總體較差,均位居各類城市的末位。類型Ⅲ主要為東部城市與中西部發展較好城市,該類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經濟水平、生態環境、財政不平衡度均較好,但開放環境、政府科技投入環境表現相對不足。類型Ⅳ主要由全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組成,除政府科技投入占比相對較低以外,區域環境各項指標均表現較優。由此,整理得到表2的四大類區域概況。

表2 四種類型區域特征
(三)指數測算
創新驅動發展的測度方法有指數法、增長核算法、數據包絡分析法與隨機前沿法等(海兵,楊蕙馨,2015)。指數法中的單指標難以準確合理刻畫創新驅動發展水平,而多指標則由于指標選取缺乏統一標準而過于主觀,以數據包絡分析法和隨機前沿法測算得到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成為刻畫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測度指標。測算TFP一般有索洛余值(SRA)方法和Malmquist指數兩類,前者更多為經濟學領域學者所采用,而后者得到更多地理學者所使用,盡管基本原理與測算方法有所差別,但所反映的內涵近似。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數作為測量方法,以各樣本不同時期的面板數據為基礎,衡量各城市創新驅動發展水平。Caves等定義的Malmquist指數測算公式為:


式(2)中右側第一項測算出技術效率面向產出指標在區間t和t+1的(逐漸趨近于生產前沿面)變化,根號中為技術變化指標,即前沿面在區間t和t+1變化的幾何平均值(劉建國、張文忠,2014)。
根據Malmquist指數模型要求,選取GDP作為產出變量,資本、勞動力作為投入變量。
(1)GDP。本文用中國的GDP平減指數(1990年為基期)進行調整。
(2)固定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各地區的資本存量,計算公式為:

其中,Kit?1為基期資本存量,本文借鑒Young(2000)的方法,以基期固定資產投資額乘以10作為初始資本存量;δ為折舊率,采用6%(Hall R E & Jones C I,1999);pi為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本文借鑒顏鵬飛等(2004)的做法,以GDP平減指數代替各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
(3)勞動力。即本市16周歲及以上,從事一定社會勞動并取得報酬或經營性收入的就業人員數。
根據上述方法,運用deap2.1軟件,測算得到2000—2017年全國289個城市全要素生產率。從圖1可見,2000—2017年,全國289個城市TFP總體上不斷提升,尤其是2011年以來全國各城市TFP平均值達到1.018,遠高于2000—2010年的0.941,創新驅動發展效果逐漸顯現。從各類型區域來看,類型Ⅳ區域的TFP相對較高,類型Ⅲ區域其次,類型Ⅱ和類型Ⅰ區域相對最低,創新驅動發展空間異質性顯現。

圖1 2000-2017年全國289個城市全要素生產率變化
(四)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00—2018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為消除數據間的異方差性,本文對解釋變量做取對數處理,公式如下:

式中,Lx表示數據x取對數后的值,x表示需要取對數的數據。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數據在1左右,故保留原值進行回歸,不做取對數處理。
四、回歸分析
區域環境因子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而易見,而全要素生產率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同樣會對區域環境因子產生全面的影響,從而普通面板OLS回歸會存在內生性問題。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發現Hausman檢驗的P值為0.0000,從檢驗上證明了模型中內生性問題的存在。而二步面板系統GMM方法能夠通過工具變量的設置,有效地解決模型中的內生性問題,從而本文采用二步面板GMM方法來進行回歸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指標數據不平穩易造成結果的虛假回歸,從而首先采用Fisher面板單位根檢驗對指標數據進行檢驗。Fisher單位根檢驗的原假設H0為指標存在單位根,由表3的結果可知,在P、Z、L*、Pm四種情景下,檢驗均拒絕原假設,說明各指標數據不存在單位根,數據整體上都是平穩的。

表3 Fisher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二)回歸結果
二步面板系統GMM模型需先設定工具變量以控制內生性問題。設定模型中被解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TFP)”的1階滯后變量為工具變量;設定內生變量“人均鋪裝道路面積(LnRoad)”、“政府科技支出占GDP比重(LnTec)”“在校大學生數占總人口比重(LnStu)”“財政不平衡度(LnFinancial)”“FDI 占 GDP 比重(LnFDI)”“人均 GDP(LnPCGDP)”“建成區綠化覆蓋率(LnGreen)”的0到4階變量為工具變量。
基于表4二步面板系統GMM的回歸結果,從全國層面28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整體來看,“被解釋變量TFP的一階滯后變量(L1.TFP)”顯著為負。這說明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度波動很大,各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未能實現持續增加。此外,“人均鋪裝道路面積(LnRoad)”“政府科技支出占GDP比重(LnTec)”“人均GDP(LnPCGDP)”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道路基礎設施的完善、財政科技投入以及經濟發展基礎良好能夠有效地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財政不平衡度(LnFinancial)”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財政狀況不良的地方政府難以較好地發揮科技的推動力量,從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建成區綠化覆蓋率(LnGreen)”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能帶來創新型企業、人才與要素的集聚,也反映出現階段我國的生態環境建設仍處于投入階段,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生積極影響尚未得到充分體現。“在校大學生數占總人口比重(LnStu)”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可能與人才具有流動性有關。受區域就業機會、收益多重可能性的粘附,人才地域選擇則呈現出“本地—躍遷”的特征(聶晶鑫、劉合林,2018),在校大學生人數比重難以充分轉化為本地創新驅動發展水平的提升。“FDI占GDP比重(LnFDI)”的回歸系數也不顯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所表征的對外開放環境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并不明顯,創新驅動發展對需要更加注重內生性創新而非依靠國外資本和技術引進的外生型創新。

表4 二步面板系統GMM模型的回歸結果
從4種類區域的回歸結果來看,表4中顯示各類型區域間既有一定的共性,又有一定的差異性。共性方面,區域環境因子中科技資源環境以及經濟基礎環境對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出極為顯著的積極影響,“政府科技支出占GDP比重(LnTec)”、“人均GDP(LnPCGDP)”在4類型區域中均顯著為正;制度環境的作用結果也相對統一,“財政不平衡度(LnFinancial)”在剩余的1類區域中不顯著,表明政府財政上的不充裕對全要素生產率整體上具有負面影響;而城市生態環境從總體上和對4類區域中的影響均不顯著。
而表4顯示基礎設施環境、人才資源環境、開放環境等對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出了較大差異:①對于基礎設施環境,類型Ⅰ、類型Ⅱ這兩類發展基礎相對較差的城市,“人均鋪裝道路面積(LnRoad)”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說明在這兩類區域中整體基礎設施水平并未換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步提升。這兩類地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區域,經濟發展仍然依賴要素、資本的大量投入,而非來自于技術進步推動,整體上尚未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在類型Ⅲ城市中,“人均鋪裝道路面積(LnRoad)”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該類型區域以發展基礎較好的東中西部城市為主,在政府創新投入水平和創新重視程度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也是影響該類區域基礎設施環境不能形成對全要素生產率正向作用的原因之一。在類型Ⅳ城市中,“人均鋪裝道路面積(LnRoad)”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類型Ⅳ多為各區域經濟發達城市,其創新投入水平、產出績效較強,創新基礎設施與創新驅動發展水平形成了協同效應和正向關聯。② 人才資源環境中,類型Ⅰ、類型Ⅱ、類型Ⅲ區域的“在校大學生數占總人口比重(LnStu)”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上述地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良好的人才資源環境能為當地帶來創新驅動發展亟需的人力資本,這支持了高素質人才作為重要的創新資源能夠有效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觀點;而在類型Ⅳ區域中,“在校大學生數占總人口比重(LnStu)”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該類城市多為區域內經濟發達城市或城市群,由于人才具有高度流動性,上述城市也形成了對人才較高的吸引力,為本地創新驅動發展貢獻的高素質人才往往多于本地高校在校生人數,從而類型Ⅳ區域中這一指標的回歸系數為負;這也間接說明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具有極強的不平衡性問題,欠發達地區創新驅動發展人才緊缺與大量高等教育資源集聚于經濟發達城市現象并存,人才存在空間配置上的錯位。③對外開放環境中,類型Ⅰ、類型Ⅲ、類型Ⅳ中“FDI占GDP比重(LnFDI)”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支持了FDI并難以為當地帶來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的觀點(張建偉、王艷華、趙建吉等,2016);而在類型Ⅱ區域中,“FDI占GDP比重(LnFDI)”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該區域發展基礎相對較差,FDI的進入往往帶來當地亟需的創新資源;以上也反映出通過市場換技術的創新驅動發展策略具有局限性,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階段FDI具有將有效推動當地創新驅動發展水平,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外資技術封鎖對FDI溢出效應發揮形成了阻礙作用。為此,在強調對外開放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同時,更應關注本地創新資源集聚、創新要素培育、創新環境優化,推動內生型創新。
通過上述分析,總結出下表5:

表5 區域環境因子對4類區域產生的異質性影響
(三)有效性檢驗
為保障二步面板系統GMM回歸結果的有效性,需進一步對模型進行檢驗。由于模型中存在工具變量的設定,從而需要用sargan檢驗來識別是否存在過度識別工具變量的問題。此檢驗的原假設為所有工具變量都有效,從表6各區域類型中的P值來看,所有模型的P值均接近1,不拒絕原假設,從而支持了二步系統GMM中的工具變量設定是可行的。

表6 各模型的sargan檢驗結果
擾動項的序列相關問題則需要通過eatat abond方法來進行檢驗,該檢驗的原假設為擾動項無序列相關,其通過的標準是1階時序列自相關,2階及以上無序列相關。從表7的結果中可以看出,所有區域類型均在1階時拒絕原假設,2階時不拒絕原假設,通過eatat abond檢驗。

表7 模型的eatat abond檢驗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系統分析區域環境異質性對創新驅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運用malmquist指數分析2000—2017年全國289個城市創新驅動發展水平,并構建區域環境指標體系,分析區域環境因子對創新驅動區域經濟發展效果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1)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效果顯現,2000—2017年,全國289個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總體不斷上升,尤其是2011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平均增長率達到1.8%,高于2000—2010年的-5.9%,反映科技創新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貢獻越來越明顯;但各地區創新驅動發展呈現出異質性,區域環境條件較好的區域的創新驅動發展效果優于其他地區。(2)基礎設施、創新投入、經濟基礎、制度環境等地方性區域環境因子是影響創新驅動發展效果的顯著積極因素,而生態環境和人力資本、開放環境等流動性較強和外部環境因子的影響相對較弱或者不顯著,反映出盡管流動空間影響越來越強,但創新驅動發展效果依然主要受地方性區域環境而非外部因素的影響。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嵌入地方性的區域環境中,這也是解釋不同地區創新驅動發展效果存在差異的重要基礎。(3)區域環境因子對不同類型區域的創新驅動發展影響存在異質性。從共性來看,科技投入、經濟基礎、制度環境等因子對不同地區創新驅動發展的影響相似,而基礎設施環境區域環境較好的地區具有積極影響。人才環境在區域環境相對較差的區域具有顯著正向作用,為當地提供了創新驅動發展亟須的人力資本,在區域環境較優的地區則通過吸引全國人才流入,本地人才環境影響不明顯;FDI在經濟發展較低階段具有積極影響,當發展到一定水平后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對創新驅動發展的影響也相對有限。(4)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在于營造有利于創新的區域環境,尤其是基礎設施、創新投入、制度環境、經濟基礎等地方性區域環境。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階段應積極加強外部技術和人力資源引進,在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應更加重視內生創新力量,將創新驅動發展嵌入地方環境中。
本文對于區域環境異質性下創新驅動發展理論機制分析與路徑探索具有重要價值,但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區域環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目前學術界缺乏對區域環境因子的科學界定;受數據可獲取性限制,本文難以窮盡區域環境的各方面,使得研究結論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區域類型劃分的限制,筆者通過深入分析不同區域環境的區域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路徑,以期為全國各地區因地制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