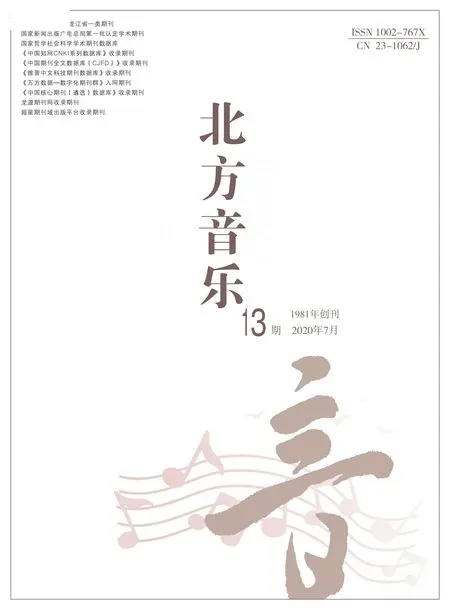論舒曼藝術歌曲《往昔痛苦的舊調》鋼琴聲部的藝術特征
紀 青
(浙江音樂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0)
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年)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德國偉大的作曲家、音樂評論家。他一生創作了多種音樂體裁,包括協奏曲、鋼琴曲、交響曲以及近三百首藝術歌曲,作為“歌曲之王”,他最廣為流傳的聲樂套曲是《詩人之戀》(Op.48)。
1835年,舒曼與教授約翰·弗里德里希·維克(Johann Friedrich Wieck,1785-1873年)的女兒克拉拉相愛,并迅速墜入愛河,但他們的愛情遭到了教授的強烈反對,因此這段感情曾讓兩人一度陷入低谷,直到1840年9月他們才終于收獲了愛情步入了婚姻殿堂。《詩人之戀》創作于1840年5月,由此得知,舒曼正是在對愛情的憧憬與煎熬的等待中完成了這部被稱為他與克拉拉“愛情日記”的作品。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年)是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他的深沉、憂郁氣質和他的詩詞一樣使舒曼獲得共鳴。1820-1823年,海涅創作了詩集《抒情的間奏》,其中的內容正是海涅自己與其堂妹愛情生活的寫照,海涅把在這段感情中遭受的痛苦和打擊融進了他的詩歌。舒曼對這部作品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與舒曼的情感生活也如此相似,使他想到和克拉拉坎坷的愛情經歷。于是,舒曼挑選了詩集中最具代表性的16首抒情詩歌組成了聲樂套曲《詩人之戀》。
《往昔痛苦的舊調》是該套曲的最后一首,描繪了一位青年男子經歷了愛情的甜蜜和痛苦的失戀后,對愛情的頓悟以及決定從悲痛中解脫出來的決心。歌詞中“Ich senkt’auch meine Liebe Und meinen Schmerz hinein!(我把所有的愛情與痛苦一起盛入!)”,體現了詩人最后因為失戀所達到的極度悲傷狀態,甚至近乎瘋狂。因此,整個聲樂套曲中,這首歌曲是有結尾式的藝術歌曲,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義。本文將從鋼琴聲部的旋律特點、力度變化、節奏律動、和聲色彩幾個方面來分析這首歌曲的藝術特征。
藝術歌曲的創作和鋼琴伴奏密不可分,在舒曼的創作中,鋼琴聲部不是僅僅作為歌曲的伴奏,而是和演唱者的歌聲相互交織、相互補充,甚至在有些作品中鋼琴部分獨自作為尾奏繼續表達音樂情緒,拓寬了鋼琴作為伴奏的表現,使其更加廣闊和具有深度。鋼琴聲部的藝術性在這首作品中如下:
一、旋律特點
《往昔痛苦的舊調》的整體旋律特點十分悲痛且深沉,歌曲一開始的三個小節引子由鋼琴演奏進入,旋律帶有復附點節奏音型,開門見山地暗示了主人公即將把愛情埋藏的痛心與堅定,也顯現出了歌曲整體的旋律動機。歌曲整個前半部分4-32小節的鋼琴伴奏聲部旋律,均采用連音與斷奏相結合的方式。在33-52小節出現了帶有柱式和弦的旋律音型,后又轉變為連續的切分音型。從53小節開始是鋼琴獨奏部分的分解和弦音型。
舒曼在這首歌曲中,對于鋼琴聲部旋律創作最大的魅力在于,在結束部加入了一個較長的鋼琴尾奏。在全曲共67個小節當中,最后15個小節的尾奏又好似鋼琴的發展樂段,體現出一種新的樂思。舒曼運用了行板的速度及抒情的曲調,最大限度地突出了鋼琴音域和音色,以鋼琴獨奏的形式來延伸歌唱者所未表達完的意境,對詩歌的內涵加以渲染和補充,情感抒發甚至較歌唱者更濃郁。有相似旋律和篇幅的還有《詩人之戀》的第十二首《一個明朗的夏天早晨》的鋼琴尾奏部分。《往昔痛苦的舊調》的整個尾奏部分像是在表現詩人心中愛情的死亡過程,極具深意,緩慢而沉靜的旋律線條與套曲的第一首《燦爛的五月鮮花》有著首尾呼應的效果,仿佛是對整首套曲講述的故事做了一個富有浪漫主義幻想式的總結。
在53-58小節中(譜例1),尾奏部分的旋律由模進的手法展開,延伸而下的分解和弦彌漫在整個旋律當中,表達了主人公憂郁的情緒以及愛情終將消散的現實。開始的右手旋律由弱拍進入,以帶延留音的高聲部匯制了一條連綿不斷向上蔓延的主旋律,具有隱形的推動力,流露出主人公對美好愛情的回憶與向往,表現出一種若隱若現的意境。再者,左、右手三個聲部相互交織、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種復調性旋律織體,右手高聲部旋律又與左手低聲部旋律的第一拍和第四拍上的旋律形成了一種交錯形式,表達了詩人恍惚、孤獨的感受。

譜例1
二、力度變化
力度是表現音樂情緒的重要因素,可以表達歌曲的憤怒、喜悅、激動等情感變化,也能表達主人公平靜、憂傷、愛慕的內心活動。舒曼在這首作品中通過力度變化塑造了深刻的音樂形象以及詩人細膩的心理變化。
在《往昔痛苦的舊調》中,鋼琴伴奏在力度上共出現了1個強后突弱(fp)、2個突強(sf/sfz)、2個很強(ff)、4個弱(p)、4個強(f)以及出現了19個重音記號(>)。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人語氣的堅定以及內心復雜的變化過程,并通過比喻式的歌詞來突出了棺材之大,可以看出詩人借物來抒發他對這段愛情的投入之深。
全曲伴奏聲部的力度從第1小節就出現了一個突強(sf)和很強(ff),第2-5小節還出現了多個重音(>),并結合連奏與斷奏音型,與左手第一拍和第三拍上的重音強力度相結合,體現出詩人內心高漲的情緒和沉痛的心情。
從19小節-35小節,出現了連續4小節一句的弱(p)與強(f)力度交替變化(譜例2),這一對比生動地描繪出十二個巨人搬運厚重的棺材時氣喘吁吁、走走停停的形象,也表現出主人公內心的掙扎與矛盾。當進入強(f)力度時,轉而以一種直線向上且伴隨逆行的音型直至旋律高點,形象地刻畫出又長又重的大棺材,同時也表現了詩人埋葬愛的決心。

譜例2
三、節奏律動
全曲鋼琴聲部運用了多種節奏型,包括復附點節奏型、連續的八分音符節奏型與切分節奏型等。
第1-3小節的復附點節奏型,以鋼琴獨奏很強(ff)的力度闖入,并結合長拍時值上的重音記號,強調了主人公對愛情帶來傷痛之后的頓悟和內心的絕望,奠定了整首歌曲悲痛的基調(譜例3)。
第4-32小節是連續的八分音符節奏型,以鋼琴連斷奏結合的演奏方式,呈現出一種平穩而有力的頓挫節奏,連音與跳動的音符猶如火焰般在燃燒,配合左手四分音符時值如同鐘聲般神圣,表現了一種莊重的氣氛。

譜例3
第43-47小節的切分節奏型,打破了此前規整的4/4拍重音規律,使原本平穩的節奏產生了搖擺的感覺,描繪出萊茵河起伏的波影。第43小節,伴隨在漸弱的力度之下,歌曲的情緒才開始真正緩和下來,仿佛詩人陷入了一種無盡的悲傷。在第44-47小節,結合弱(p)的力度表達出在平靜的氣氛下詩人充滿憂傷且沉痛的內心(譜例4)。

譜例4
四、和聲色彩
舒曼在創作中大膽突破傳統和聲的運用,在全曲鋼琴聲部大量運用減七和弦、增和弦、半音化和聲等不協和和聲構建了和聲結構的復雜化,加強了和聲色彩的多樣性,通過這些不協和和聲語言深化了詩詞對情感的表現,描繪出歌曲中失戀后的詩人對愛情的絕望和悲痛。
減七和弦(包括在主調、離調中)用于全曲的7個小節中。在整首歌曲的前部分僅在第11的小節最后一拍和第12小節的第一拍上出現,配合歌詞“Hinein leg(盛進)”,通過不協和和聲表達出詩人的極度不舍,把主人公內心對戀人這份深沉的愛放入棺材的時候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在39-40小節(譜例5)以延長音和強有力的重音標記出現,伴隨著歌詞唱出的“denn solchem gro?en Sarge(對如此巨大的棺材來說)”,一方面刻畫出棺材之大,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主人公眼看裝滿所有甜蜜愛情的棺材已經被深深沉入萊茵河下的痛心。最后,減七和弦在鋼琴尾奏部分的第55小節和60小節當中也有出現。

譜例5
此外,樂曲在53-58小節出現了大量半音化和聲的運用。此處半音化和聲的進行增強了歌曲的抒情性,在音響上使聽眾感受到柔和與平滑,也更細膩地抒發了詩人對埋葬愛情后的游離不定以及悲傷、憂郁的情緒。
五、結語
《詩人之戀》堪稱是舒曼藝術歌曲中的一部扛鼎佳作,他與海涅一樣都借助詩歌來表現了自己內心的憂傷,歌詞結局雖然是悲劇的,但舒曼最終是幸福的,因此他借由悲劇來突出自身經歷的愛情來之不易。同時,舒曼還將自己與克拉拉在愛情生活中的情感體驗細致入微地滲透進音樂創作中,完美地展現出音樂與詩歌的相互碰撞。
《往昔痛苦的舊調》在套曲《詩人之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創作上也有其獨特的風格。作為套曲的最后一首,表達了一定的結局式特點,不僅有鋼琴聲部本身的風格所在,更體現了伴奏與人聲聲部之間的密切聯系,體現出藝術歌曲的創作與詩詞相結合的魅力。
本人對該曲的旋律特點、力度變化、節奏律動、和聲色彩等進行分析,以期演奏者能充分發揮鋼琴聲部的藝術魅力,在對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更好地使鋼琴伴奏者與歌唱者共同抒發詩歌的內涵與情感,從而達到更完美的演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