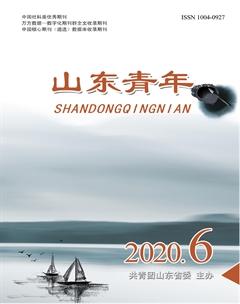試論商鞅緣法治國的有力保障
張文婷
摘 要:為保證法令作為治國準則與衡量尺度的順利實施,舉國上下形成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保障政策。“以法為教”,首先需要法令的制定應(yīng)適時、因俗,其次法令本身需淺顯易懂方才利于普及于眾。為方便順利地普及法令,君主需要為百姓設(shè)置能將法令銘記于心且融會貫通的法官與法吏,作為百姓的老師使千萬黎民百姓皆能知法避害,最終使緣法治國獲得“定分止爭”的功效。
關(guān)鍵詞:商鞅;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定分止爭
商鞅,戰(zhàn)國時期秦國變法家。此時他所處的時代正立于禮崩樂壞、兵戎相見、兼并戰(zhàn)爭不斷的社會劇變之下。《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及:“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
[1]這兩段描述可見往世推崇的仁義禮樂,名分秩序早已被無盡追求利己主義的強國政策所吞沒,諸侯與天子陰陽易位,邦分崩離析,父子與兄弟葉散冰離,家四分五裂。然而此時也是文化思想盛極一時的時代,傳統(tǒng)的天命鬼神思想開始在人文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覺醒下沉淪,實用主義哲學(xué)占據(jù)一席高地。各諸侯國在紛爭下亟需可以富國強兵的人才,百家爭鳴應(yīng)運而生,具有戰(zhàn)略智識的士人階層穿梭于各諸侯國之間通過宣講自己的學(xué)說來緣遇人生伯樂。此時,商鞅從無法施展鴻鵠志向的魏國來到偏居西陲的秦國,利用自己工于權(quán)變的能力以及雄厚的各家思想儲備來四說秦孝公,最終以“強國之術(shù)”使得孝公大悅,幸遇人生伯樂,被任用后獻身于變法圖強的興邦之業(yè)。在他勵精圖治的二次變法后,從“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道行”[2]到“夫商君為孝公平權(quán)衡,正度量,調(diào)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zhàn),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3]從當初被諸侯國卑秦的寡廉鮮恥若禽獸,到諸侯畢賀的富強兵勝若龍鳳,這得益于商鞅的興邦良策。在此,筆者不揣谫陋,在先賢真知灼見的理論基礎(chǔ)之上,以歷史與辯證的眼光,就保障緣法治國順利進行的這一關(guān)鍵思想發(fā)表一下自己的拙見。
一、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奸臣鬻權(quán)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眾而木析,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于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商君書·修權(quán)》),如果廢除公正嚴明的法度而任由既無法權(quán)衡利弊又無法獲取威信的私議虜獲君主的心,君主愛好私議與讒言,那么身邊多是以讒言奉君的毀譽之臣而非以法度明辨是非的正直之士。無法度的約束,私門大開,奸邪之臣會通過千金一擲的方式求取高官俸祿,而已獲得官職的臣子為獲取更大的私利,向上對君主隱瞞事實民情、向下對百姓敲骨吸髓。這些貪婪投巧的官吏如同蛀蟲一樣,不斷地啃噬著支撐一代偉業(yè)的高樓大廈。不僅如此,上至官員、下至百姓,皆不行實用之事,爭相誦讀空虛的言論,推崇博學(xué)多聞、能言善辯之士,最終形成官惰職、民惰農(nóng)的局面。官員只顧以權(quán)謀私而無法真誠公正地顧忌黎民百姓,百姓無法知法度趨害避利且散思于淫逸虛言,長期以往,百姓停止務(wù)農(nóng)、官吏以權(quán)謀私、君主失去威信、一國大廈將傾。“秉權(quán)而立,垂法而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保證法度作為治國準則與衡量尺度的順利實施,舉國上下形成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保障政策。
(一)以法為教
“故圣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君書·定分》),賢明的君主掌握政權(quán),按照緣法治國的政策興國,黎民百姓鮮有犯上作亂、作奸犯科、惰農(nóng)“近言”之人,因此觸犯刑罰之人屈指可數(shù),此類現(xiàn)象的原因并非是君主無法做到賞信罰必,而是圣明的君主推行的法令淺顯易懂從而婦孺皆知。百姓知道何事該規(guī)避、何事該趨赴,皆能依法自治,利于君主定國安邦。以上可見百姓依法自治具有切中肯綮的作用,而百姓依法自治的前提是使法令普及于眾。
其一,君主依靠法官普及于眾的法令需因時、順情、因俗。“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于時而行之,則不干”(《商君書
·壹言》),賢明的君主治國立法的標準是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具體情況以及社會風俗的具體表現(xiàn)來制定,做到不囿于古、不拘于今,順應(yīng)民情、時勢而變。如果法令的制定不符合民眾的實際情況,例如在路有餓殍、饑荒遍野的情況下要求百姓在外征戰(zhàn),而不是開倉放糧、獎勵務(wù)農(nóng)。如果法令的制定不符合社會的風俗習(xí)慣,例如堅持認為民性本樸并采取中古時期大行仁政于天下的政令,企圖用仁義道德感化民眾使之忠心為國。這些偏離民性民情民風民俗的法令,最終走向只能是“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
其二,法令需明確易懂,家喻戶曉。“故圣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后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書·定分》),法令文字需具體簡易,勿抽象深奧,在普通愚笨的百姓與敏而好學(xué)的圣人之間,圣人是來向千萬百姓傳道授法的,不是每一個普通人都具有超凡入圣的資質(zhì),他用以教育民眾的法令必須是明白易知的。以法為教使百姓知法,除了法令需合民情、適民智之外,普及法令的過程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以吏為師
“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于險危”(《商君書·定分》),為方便順利地普及法令,君主需要為百姓設(shè)置能將法令銘記于心且融會貫通的法官與“主法之吏”,作為百姓的老師從而為百姓普及法令,目的是使千萬黎民百姓皆能知法避害,遠離危險的境地。
其一,法官與法吏的委任需要遍及由中央至地區(qū)的行政機關(guān),“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商君書·定分》),中央設(shè)3個法官,天子宮殿、御史衙門以及丞相衙門各設(shè)一個法官,給各個諸侯國、郡、縣設(shè)置一名法官與法吏,地區(qū)法官的設(shè)置都按照秦都法官的標準。主管法令的法官和法吏受命上任后,他們的任務(wù)是在自己通曉從禁室傳來的法令內(nèi)容后公告此法令、解答官吏與百姓的疑惑。
其二,作為連接思想上層建筑與勞動力的中間樞紐,法令對法官與法吏本身也有著朝督暮責的要求。例如:禁止遺忘掌管法令的條目、禁止增減更改法令內(nèi)容、禁止對百姓或官吏詢問的法令內(nèi)容答非所問、禁止解答問題時不設(shè)備案等,如若違反要求,要么罪死不赦,要么以相關(guān)法令嚴懲不貸。法官與法吏也屬于整個吏治系統(tǒng)的一部分,整治吏治才能更好的保證法令暢行、官民相擁、政治清明。
二、 成效圖景
(一) 定分止爭
緣法治國的最大成效就是“定分止爭”。“故圣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shè)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君書·開塞》),圣賢之人順應(yīng)時代發(fā)展,分析百姓性情變化,吸收前車之鑒,從來制定了關(guān)于土地、財貨、男女的歸屬權(quán),也就是在土地私有制為基礎(chǔ)上的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與家庭關(guān)系的所有權(quán)。為確定這個所有權(quán),需要設(shè)定法令、設(shè)立官職、設(shè)置君主,將三者整合起來形成由君主頒布、由官吏執(zhí)行的緣法治國政策。通過這個的政策,使百姓用知曉的法令來確定自己的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與家庭關(guān)系,明確自己應(yīng)該追求什么、抵制什么,才能在各自利益互不侵犯的情況下達到止爭的目的。
(二)當代影響
對商鞅緣法治國政策的評價自古分為迥然不同的兩個派別,推崇法家以及目標是威震宇內(nèi)的人對此贊賞有加,弘揚民生與君民共治的人對此橫加指責。我們對商鞅的評價應(yīng)站在歷史與現(xiàn)代的角度上辯證的進行批判,在批判他過度壓抑人性以及限制文化的多元性、不能充分地制約君主權(quán)力的同時,不容置否的應(yīng)站在此時戰(zhàn)國的時代切面上考慮政策是否符合時代的訴求,如今,刑罰應(yīng)分時執(zhí)行且不能孤立存在,需與德治雙向作用。變法中進步的歷史觀、靈活利用人性的方法、提倡刑無等級的平等措施、嚴密的官吏管理制度與信息儲備方式等值得后世取精并見于實踐。例如:其“為公去私”以及“無宿治”的思想,在當今保證官員隊伍反腐倡廉行動上以及官民同心的和諧關(guān)系上具有劃時代的借鑒意義。其“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之所以為端也”的思想,推動了如今司法機關(guān)、權(quán)力機關(guān)、行政機關(guān)相互監(jiān)督、彼此制衡的場景形成。當今社會,應(yīng)繼續(xù)堅持歷史發(fā)展觀,為法治賦予時代背景與新興風俗下的新內(nèi)涵,因俗而變、因勢而成、發(fā)展法治的新內(nèi)容,完善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法治觀。
[參考文獻]
[1](漢)劉向.《戰(zhàn)國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96.
[2]張清常,王延棟.《戰(zhàn)國策箋注》[M].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93.625.
[3](漢)劉向.《戰(zhàn)國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01.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xué),安徽 合肥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