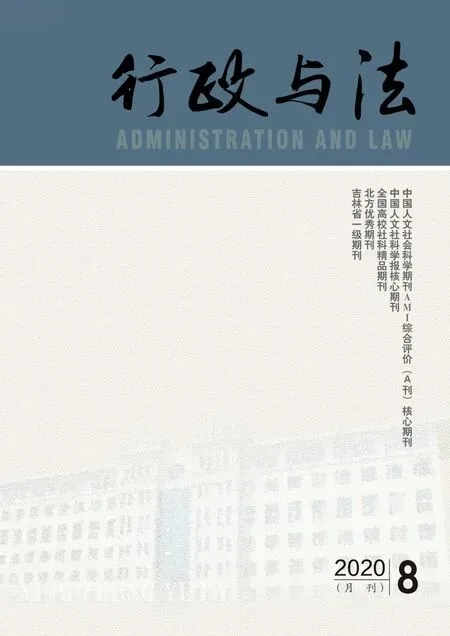基于內容分析法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研究
□ 王洪濤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遼寧 阜新 123000)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公共安全問題。食品安全無小事,一粒米一桌餐,牽動著千家萬戶,關乎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注重食品安全、倡導健康生活早已成為社會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食品安全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來抓,堅持黨政同責,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人民群眾“舌尖安全”。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讓問題產品無處藏身、不法制售者難逃法網,讓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安全。近年來,我國針對食品安全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然而,從轟動一時的三聚氰胺事件到“餓了么”黑作坊曝光,食品安全問題仍時有發生,觸痛著敏感的大眾神經。目前國內學界有關食品安全研究的文獻主要側重于治理方式和安全檢測兩個方面,對于治理源頭——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研究較少。鑒于此,本文對現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進行考量,力圖找出其中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議,以期為未來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體系的建構提供參考。
一、研究設計
本文以國家發布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為研究對象,借助北大法寶數據庫,以“食品安全”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搜索到2002—2019年間3部食品安全法、3項行政法規、28項國務院規范性文件、600多項部門規章。經過篩選,去除具體針對某一企業的行業規定,保留406項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見表1,因篇幅所限僅列舉部分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

表1 研究對象
本文基于內容分析法對我國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進行考量。內容分析法是指以文本內容為研究對象,將文本內容定性分類后轉變為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的綜合研究方法,其優點在于可按照一定標準將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文字內容轉變為統計數據,能夠更為客觀地反映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本質特征。
本文的研究步驟為:第一步,通過對頒布時間和數量進行統計分析,探究我國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發展趨勢;第二步,通過對政策發文主體的統計分析,了解不同主體的參與程度,明確食品安全管理的主導機關,描繪主體間的聯系網絡及聯合程度。第三步,通過內容分析法從政策工具和社會需求兩個維度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文本進行編碼,以解讀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政策工具使用、社會需求滿足狀況,從中發現不足并加以改進。
二、分析框架
(一)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基礎性分析
1.發文時間分析。依據406項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發文時間、數量、累計數量(見圖1),以2006年蘇丹紅事件、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2010年地溝油事件、2011年瘦肉精事件及2011年56部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峰值為節點,將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分為2002-2006年(起步)、2007-2009年(發展)、2010-2014年(沖擊)、2015-2019年(完善)四個階段進行分析后發現,大量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往往是在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次年或舉辦大型活動的當年出臺的。

圖1 發文時間與數量
2.發文主體分析。依據層級發文主體可分為三類,即最高層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層級——國務院;第三層級——國務院各部委,這一層級占絕大多數。依據數量發文主體可分為兩類,即單獨發文機關和聯合發文機關。單獨發文機關有30個(見表2)。其中,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文151次,占比37.2%;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文97次,占比23.9%。發文主體多元化雖然體現出國家對于食品安全的重視程度,但也容易產生權責不清、形式主義等問題。聯合發文的政策性文件共計31篇(見表3),聯合發文的部門最多為4個。對比數據發現,聯合的部門越多,發文數量越少。

表2 單獨發文機關及發文數量

表3 聯合發文
為直觀了解部門聯合發文的情況,本文運用UCINET軟件構建了聯合發文網絡圖(見圖2)。在圖中,一個節點代表一個政策主體,主體間連接線值代表主體間聯合發文次數,節點越大則政策主體的活躍性越強。可以看出,在眾多聯合發文中,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和農業部起引導作用。

圖2 聯合發文主體網絡圖
(二)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內容分析
1.分析框架構建。
⑴X維度分析框架構建。政策工具以政策結構性為立論基礎,通過一系列基本單元工具有機結合,反映公共政策價值和理念。[1]借鑒Rothwell和Zegveldz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2]本文將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分為三類:一是供給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過擴大供給力度彌補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缺少的要素;二是環境型政策工具,表現為間接影響;三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在對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對社會組織的需求(見表4)。

表4 政策工具
⑵Y維度分析框架構建。作為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直接對象,社會需求可分為三種:一是資源需求,是指從社會需求出發,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確保食品安全;二是參與需求,是指政府需要滿足社會群體共同治理食品安全的意愿;三是市場需求,是指社會群體對食品市場穩定的需求。綜上,本文構建了二維分析框架(見圖3)。

圖3 分析維度
2.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文本編碼。內容分析法的核心步驟在于分析單位選擇,對分析單位進行編碼,編碼的合理性決定量化分析的結果是否客觀合理。[3]本文采用“政策編號——條目編號”形式對406項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文本的每一項內容進行了編碼(見表5,因數量龐大僅節選部分編碼)。

表5 政策內容編碼
在編碼基礎上,本文對分析單位進行了政策工具歸類,即判斷每一個分析單位具體屬于哪一種政策工具(見表6)。

表6 編碼歸類
從已經編碼的政策工具中選取符合社會需求的編碼項歸類到二維分析框架中(見圖4)。

圖4 分析維度統計
3.頻數統計與維度分析。
從X維度來看,經過統計,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共涉及1490個政策工具,其中,環境型政策工具使用率為49%,供給型政策工具使用率為42%,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率僅為9%(見圖5)。實際上,需求型政策工具在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發揮著與社會充分交流、引入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應當予以重視。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務類使用率為41%,基礎設施建設類使用率為25%,信息支持類使用率為19%,人才培養類使用率為12%,而資金投入類使用率僅為3%,難以形成有效支持(見圖6)。在環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規管制類使用率為87%,已經逐漸形成一套嚴格且標準的管理體系,但策略性措施類使用率僅為9%,容易出現“一時一令”的現象;財務金融類使用率只有4%(見圖7)。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服務外包類使用率為70%,貿易管制類使用率為20%,而政府采購類使用率只有10%(見圖8)。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政策工具處于失衡狀態。
從Y維度來看,對社會需求三個層面的政策工具使用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在涉及社會需求的449項政策工具中,參與需求占48.33%,市場需求占40.09%,而資源需求僅占11.58%(見表7)。另外,在涉及市場需求的180項政策工具中,法規管制就有156項,占比86.7%。以上數據充分說明,政策工具的使用嚴重失調。

圖5 政策工具統計

圖6 供給型政策工具

圖7 環境型政策工具

圖8 需求型政策工具

表7 社會需求&政策工具
三、分析結果
(一)政策出臺連續性不足
從發文時間和發文數量來看,2002—2019年間食品安全相關政策的出臺與食品安全事件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呈波動趨勢,相關政策銜接不足。如2006年蘇丹紅事件后,2007年出臺的政策多達20項,2008年則降到6項。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2009年出臺的政策激增到21項。而且,食品安全政策的核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如某一食品出現安全問題后,相關政策的核心就針對這一食品領域制定更嚴格的標準并加大監管力度,發文數量迅速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的食品安全在宏觀管理上略顯不足,存在“亡羊補牢”現象。
(二)政策發文主體聯合行動不力
食品安全的發文主體涉及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商務部、農業部、科學技術部等30個部門。在406項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中只有31項為聯合發文,這說明相關部門之間聯合程度不夠,極易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即便是僅有的31項聯合發文也存在政出多門的問題,如針對中小學和幼兒園的食品安全問題,既有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和教育部的聯合發文,也有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和教育部的聯合發文,條款多有重復。從圖2可以看出,政策發文主體之間結構較為松散,部門間的信息溝通網絡不暢、權責劃分不清,使得政策雖然數量眾多但執行效果不夠明顯。
(三)政策工具結構失衡
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涵蓋了供給型、環境型、需求型三種政策工具,但環境型和供給型政策工具過多,需求型政策工具較少,不利于激發市場自我監管。而且,三種政策工具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同樣問題,如在環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規管制類政策工具使用較為頻繁,容易出現矯枉過正現象,給食品市場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資金投入類和人才培養類政策工具過少,基礎設施類政策工具使用效率不高,整體失衡;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服務外包類政策工具較多,政府采購類和貿易管制類政策工具較少,不利于形成較好的政府示范效應。
(四)社會需求滿足度不夠
從圖4和表7可以看出,雖然政府十分重視食品安全管理中的社會參與度,針對資源需求、參與需求和市場需求皆有政策工具來支撐,但在使用上存在失衡問題,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如在資源需求方面,食品安全投訴機構等基礎設施建設跟進不夠;在參與需求方面,政策工具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務類和服務外包類,過于單一;在市場需求方面,為鼓勵食品市場自發提高食品安全標準,理應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但政府只是使用156項法規管制類政策工具進行監管,財務金融類政策工具僅有9項,財政支持類、稅收優惠類政策工具則是空白。
四、相關建議
(一)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保證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協調性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導,國務院各部委及直屬機構組建聯合辦事機構,對涉及食品安全的不同部門的職權范圍和相互合作方式進行梳理,設置權責清單。構建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執行反饋機制,根據社會上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回應或建議出臺相關的配套政策。構建長效預警機制,發布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應以“防患未然”為原則。發文特別是聯合發文時相關部門應加強信息溝通,時刻把握食品安全問題和政策運行效果,最大限度地把食品安全政策數量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保證政策順暢執行。
(二)強化政策工具在使用過程中的協同性
在實現滿足社會需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環境型、供給型、需求型政策工具被拆分、融合,因此政策工具的內部協調就顯得尤為重要。就環境型和供給型政策工具而言,目前,政府對于食品安全管理的環境型和供給型政策工具投入已呈飽和狀態,應在鞏固的基礎上進行篩選和整合,剔除重復性、矛盾性、無效性政策工具,精簡合并相近類政策工具。如精簡法規管制類政策工具的使用頻率,加大財務金融、稅收優惠等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逐步形成多元治理的局面;合理配置資源,增加人才培養、基礎設施建設、財政支持類政策工具的使用頻率,力求與需求型政策工具配套使用。就需求型政策工具而言,進一步提高政府采購類、服務外包類、貿易管制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效能,以需求拉動食品市場發展。如與高校合作研發新型食品安全檢測儀器、采用政企聯合的方式將服務外包、通過公務微信公眾號及時發布食品安全政策動態等。相關部門應指派專門人員與食品行業代表共同成立食品安全監督小組,定期與群眾溝通,實時關注食品市場動態,了解政策供給是否能真正滿足群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