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程安全建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李利平,成 帥,張延歡,屠文鋒
(1.山東大學 巖土與結構工程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061;2.山東大學 齊魯交通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3.成都理工大學 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四川 成都 610059)
21世紀是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新紀元,以隧道為代表的地下工程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在長達數十年的建設歷程中,我國已成為世界上隧道建設規模、難度和數量最大的國家,涉及公路、鐵路、水利和市政等諸多工程領域[1]。近十幾年,在“十一五”至“十三五”規劃指導下,我國地下工程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隨著川藏鐵路、渤海灣跨海隧道為代表的一批世紀工程的修建或推進,我國隧道與地下工程建設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面臨新的歷史性機遇。同時,工程建設面臨極端復雜的地質條件與建設環境等挑戰,以川藏鐵路雅安至林芝段為例,全線橋隧比極高,隧道65座、線路總長802 km,其中最長的易貢隧道長達42.2 km,沿線地形高差顯著、地質環境復雜、板塊運動強烈、山地災害頻發。此外,為了進一步加強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城市地下空間”建設規劃的銜接,隧道工程不斷向“深、長、大”方向發展,面臨的地質問題日趨突出,意味著地下工程建設災害風險更高,防災代價更大,安全建設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在我國地下工程世紀性的騰飛面前,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的,如何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是地下工程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1 中國地下工程建設現狀分析
1.1 中國地下工程建設規模
據有關統計數據,截止2018年底,我國運營的交通隧道總數達30 776座,總長30 611.1 km,正在或即將修建的交通隧道總數達6 644座,總長13 125 km,典型隧道工程詳見表1[2]。特別是錦屏二級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等超大規模的地下洞室群建設規模不斷刷新世界地下工程記錄,如白鶴灘水電站地下洞室總長度達217 km,廠房頂拱跨度34 m,高88.7 m,為世界已建跨度最大的地下廠房。

表1 我國典型深長隧道工程[2]
1.2 中國地下工程發展趨勢
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先后把交通水利隧道、城市軌道交通、地下綜合管廊、地下綜合開發和海綿城市等作為重要戰略,進一步推動了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地下工程作為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的咽喉,大力開發地下空間、拓展地下縱深空間已經成為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迫切需求。
我國幅員遼闊,地下空間體量龐大,可開發規模達200億m3,可計算價值超過15萬億元,特別是國家《“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的實施,要求重點推進地下空間分層開發,拓展地下縱深空間,進一步統籌城市軌道交通、地下道路等交通設施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的規劃布局,打造城市立體交通系統,促進地下空間與城市整體同步發展,以地鐵、地下綜合管廊為代表的城市地下空間建設進入黃金發展階段,為我國地下工程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3-4]。
1.3 中國地下工程建設面臨難題
我國山區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70%,且巖溶地區、沉積巖分布廣泛,地形、地貌及地質條件復雜,地下工程建設面臨巨大的地質難題,修建過程中突涌水、圍巖垮塌等重大地質災害頻發。據相關資料統計,本世紀前十年,我國交通和水電等地下工程建設中發生突涌水災害294起、圍巖垮塌災害300余起[5],造成極大的設備損失、人員傷亡和工期延誤。
地下工程災害監測、預警及控制是實現地下工程災害有效防治的重要手段[6]。然而,地下工程地質災害演化過程極其復雜,災變機理尚不明晰,現有理論難以準確描述災害演化模式、災變機制及前兆信息,已成為制約我國地下工程災害監測預警技術發展的瓶頸。特別是,現有監測設備適用性差、監測數據差異性大、監測理論尚不完善,傳統監測理論、預警技術與風險控制方法難以滿足主動防控需求,進一步導致地下工程重大地質災害長期處于被動防治局面。因此,系統開展地下工程地質災害演化機理、監測預警方法、主動防控技術研究,實現重大地質災害由被動治理到主動防控的轉化已成燃眉之需。
2 地下工程安全建設面臨的機遇
交通運輸是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如今我國站在世界交通大國的新起點上,應該始終朝著建設交通強國的目標奮進。在推動交通發展方面,要由追求速度和規模轉變為注重高質量、高效益,要由各類交通方式單一獨立發展轉變為一體化融合式發展,不能再僅依靠傳統要素驅動,而是要注意依靠創新驅動,依照這些改變,構建一個安全、高效、便捷、綠色、經濟的綜合性現代化交通體系,打造一個擁有一流設施、一流技術、一流管理、一流服務的交通強國,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的支持。在如今這個建設交通強國的關鍵時期,地下工程隧道建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也蘊藏著巨大的機遇。
隨著地上空間資源的消耗,開發地下空間資源變得刻不容緩。21世紀是一個全球性的地下工程空間大開發的世紀,大直徑、長距離以及隧道結構功能多樣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國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刺激著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城市軌道交通工程、高鐵、長大隧道和越江跨海隧道的發展。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公路鐵路建設走向世界。至2020年底,我國公路、鐵路隧道總長度將突破4萬km。雖然中國的隧道建設數量以及規模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是在許多關鍵技術方面還存在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國家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地下工程的研究者們應該抓住機遇,努力攻克關鍵技術難題。
2.1 川藏鐵路
川藏鐵路被稱為世界上最難修建的鐵路工程,將是進出西藏最快速、最便捷的主通道,也是鞏固國家邊防安全的重要戰略通道。長大鐵路隧道的建設、運營、維護都面臨著嚴峻挑戰,巖爆、大地形、高地熱以及全新世活動斷裂等問題突出,長大隧道防災、救援經驗不足,隧道棄渣及利用難度大。
川藏鐵路從成都到西藏,經過雅安、林芝,建設方案如圖1所示[7]。川藏鐵路經過五個地貌單元,工程地質復雜和強烈的板塊活動威脅施工安全,跨七江、穿八山,“七上八下”,大大增加了施工難度[8]。因為強烈的板塊活動,導致其內動力地質作用之強烈是世界鐵路少有的。川藏鐵路還穿越十余條深大活動斷裂帶,包括龍門山、鮮水河、理塘、甘孜-理塘、巴塘、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八宿、嘉黎、雅魯藏布江等活動斷裂。這些深大活動斷裂帶存在斷裂粘滑位錯(地震)、活動斷裂緩慢活動(蠕滑)等,會產生較嚴重的山地災害,包括潛在不穩定巖土體滑坡、泥石流、冰川型泥石流和冰湖潰堤型泥石流等。例如,2000年4月9日,波密縣易貢扎木弄巴發生巨型滑坡,堵塞易貢藏布,壩高100 m,潰決水位即達55 m,流量達12.4萬m3/s。

圖1 川藏鐵路沿線地形地勢圖[7]
2.2 渤海灣跨海通道
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協同發展,超長跨海隧道已成為連接海峽和海灣的重要交通工程,也是區域互通、海陸互聯和海洋開發的重要紐帶。我國已建設廈門翔安隧道、青島膠州灣隧道、廣東獅子洋隧道、港珠澳大橋等十余條海域段不超十公里的隧道,未來將建設以渤海海灣通道(預計123 km)為代表的超過百公里長的世界級超長跨海隧道。超長跨海隧道建造運營的難度遠超山嶺隧道和短距離海底隧道,無限海水覆蓋、海底強震以及復雜的海洋地質和惡劣的服役環境,導致很多超長跨海隧道在施工和運營期發生突涌水、坍塌等一系列重大災害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這也向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挑戰。
首先,超長跨海隧道賦存環境是“海水-海床-構造-隧道”復合體系,海底致災構造賦存環境極其復雜,缺乏災害源精細探測的有效方法。一方面,海床松散沉積地層飽含海水,嚴重衰減地球物理場甚至誘發其畸變或“淹沒”,準確查明海床地質構造難度極高;另一方面,上覆巖層中的亞米級導水通道等不良地質體由于探測難度大,以往在施工期沒有得到處置,使其成為突涌水、失穩災變的主控誘因。由于對海下構造探測不明,導致對工程賦存地質環境、演變過程和發育規律等認知不清,使得海底隧道施工重要環節缺乏科學依據,這是超長跨海隧道安全建造面臨的應用基礎科學難題。
其次,超長跨海隧道由于洞線長,不可避免穿越斷裂帶等地質單元,地震風險極高,地震動力災變機理極其復雜,國內外尚無成熟的隧道結構高效隔振抗斷控制技術和韌性設計方法,導致隧道襯砌錯段和“蛇形變形”,誘發大規模坍塌、大型突涌水災害。發展海底隧道韌性結構體系,引領超長跨海隧道抗震韌性設計水平發展,揭示抗震原理與規律,是今后超長跨海隧道安全建造及運營面臨的前瞻性設計理論難題。
除此之外,超長跨海隧道無限海水侵蝕、荷載復雜多變、服役環境惡劣,隧道圍巖和結構在復雜環境作用下,圍巖和加固體呈現漸進性破壞,襯砌逐步裂損演化,亟需發展有效的計算模型和分析方法,填補海底隧道圍巖-支護結構耐久性評價和壽命預測理論空白。如何突破海底環境下隧道圍巖-結構性能演化分析方法,為隧道信息智能感知和災變控制提供理論支撐,達到海底隧道結構防災減災技術水平制高點,領跑國際水平,是今后超長跨海隧道安全建造運營面臨的基礎性理論科學難題。
3 典型突發性重大地質災害主動防控的共性難題
3.1 力學機理
大批深長隧道修建在地質條件極端復雜的地區,如西部高原山區、西南巖溶發育地區等。隧道修建過程中常遭遇突涌水、圍巖垮塌、大變形、巖爆等典型突發性地質災害。突涌水災害呈現顯著的超高水壓、超大流量、高隱蔽性、強突發性和強破壞性特點,其防控為世界級工程技術難題。巖爆呈現出滯后性、延續性、衰減性、突發性、猛烈性的特點,造成支護系統損毀、設備癱瘓,誘發大規模巖體坍塌,嚴重影響施工人員安全。大變形災害因其變形量大、變形速率高和變形持續時間長的特點,常造成襯砌壓裂、結構錯位,最終誘發大型塌方事故,延誤工期。此外,隧道修建以及運營過程中還會面臨瓦斯、毒氣、粉塵以及高溫熱害等不良施工環境,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施工與運營安全。
縱觀各類典型深長隧道突發性地質災害,難以實現主動防控的根本理論難題在于深部巖體本構關系與動力災變機理不清楚,災變演化過程的高效模擬分析方法未建立,現有的數值計算方法難以實現工程尺度的災變模擬。有效多元信息的監測方法缺失,致使災害前兆信息測不到、測不準。單一、有限的信息間存在“孤島”現象,亟需建立信息一體化融合方法,規避災害誤警和虛警現象,突破災害發生時間、位置和危害等級的預測難題。本研究分別以施工期隧道突涌水災害及圍巖垮塌災害兩類典型地質災害為例,論述突發性地質災害主動防控的力學機理。
3.1.1 隧道突涌水災害
基于防突結構破壞模式的不同,突涌水災害可劃分為隔水巖體漸進性破壞突涌水和充填結構滲透失穩突涌水[9]兩種類型。隔水巖體漸進性破壞可劃分為拉剪破壞和壓剪破壞。層狀巖體隧道突水模型又可分為巖體漸進性破壞的尖點突變和雙尖點突變模型[9]。研究巖體破壞時既要考慮巖體內裂紋尖端的應力場和位移場特性,也要研究節理、斷層等巖體不連續面的破壞特性。現階段的防突結構破壞突水判據多適用于巖體突然斷裂的脆性破壞情況,對于巖體彈性變形后發生較大塑性變形以致破壞的情況適用性較差。同時,巖石變形破壞的過程是和外界產生能量交換的過程。巖石的失穩破壞就是巖石中能量突然釋放的結果,這種釋放是能量耗散在一定條件下的突變[10-11]。此外,對于巖體破壞突水機理也需研究爆破開挖等外載擾動造成的漸進性破壞過程。鉆爆施工條件下產生的爆炸應力波會造成裂紋內部水壓力大小發生變化。隧道掌子面裂隙巖體突水發生源于含水裂紋巖體的壓剪擴展破壞[12]。充填型不良地質構造中突水通道的形成是由于其內部充填介質的滲流災變導致。基于充填物的滲透特性可將充填滲透突水模式分為充填介質的滲透失穩與充填體的滑移失穩突水[13]。
1)最小防突安全厚度計算方法
防突結構的破壞模式與演化過程是防治突涌水災害的關鍵,防突結構的最小安全厚度是突涌水發生的臨界厚度。巖溶隧道掌子面突水是由雙重作用引起的:一方面是隧道爆破開挖擾動導致巖體固有裂紋激活,發生擴展;另一方面是在高巖溶水壓持續作用下,巖體裂紋產生軟化溶蝕,改變了巖體裂紋間有效應力,致使裂紋發生擴展-貫通直至破裂突水。研究人員針對不同的工程地質情況提出了一些防突安全厚度計算模型。例如,梁板模型[14]、基于臨界水壓力的掌子面巖墻安全厚度計算模型[15]、基于系統勢能突變控制參數災變演化路徑的最小安全厚度計算公式[11]、“一區一帶”計算模型的中間巖柱失穩力學模型[4]等。對于隧道洞頂、掌子面前方突水情況,有“三區”理論[9]、“一區一帶”計算模型[12]。以上模型極大地豐富了隧道突涌水最小防突安全厚度的理論研究,為工程實踐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但各有其限定的適用條件,如,梁板模型對于隧道底板處存在溶洞情況,將爆破擾動簡化為振動附加力作用在巖體上,暫考慮的是靜水壓力;掌子面巖墻安全厚度計算模型計算了抗裂保護區厚度,但裂隙帶的取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物探結果的精準性;“一區一帶”計算模型,暫未考慮隧道開挖與側部高壓富水溶腔對中間巖柱穩定性的耦合影響等。
2)災變演化過程的數學模型
深部巖體中,隧道施工的開挖卸荷與爆破擾動對巖體的開裂、裂隙擴展、滲流乃至突涌水發生的影響不容忽視。同時,深長隧道工程中,面臨高地應力、高地溫、高滲透壓力的影響,長洞線致使施工及運營期間遭遇更為復雜的區域性滲流場,突涌水的災變機理與演化過程愈加復雜。循環動力擾動、強卸荷與高滲透壓環境下,表征深部巖體的破裂機理、滲流特性、水與巖土體互饋關系的數學模型將成為突涌水動力演化機理研究的關鍵。
3.1.2 隧道圍巖垮塌災害
針對隧道圍巖垮塌災害,許多學者對塊體的幾何封閉性和幾何可動性原理進行了本質的擴展研究,豐富了危石平動、轉動、斷裂的失穩模式,先后提出了直接墜落、單面滑移、雙面滑移、角點傾覆、角點旋滑、楞線傾覆、平移斷裂七類運動模式,系統建立了隧道危石失穩運動模式的幾何識別方法及危石穩定性分析模型[2,4]。此外隧道危石識別軟件及隧道危石識別系統也相繼發展成熟,逐步解決了隧道危石幾何識別的理論及技術問題。但隧道工程環境復雜,信息化要求日益增加,針對巖體結構探測、三維模型重構等問題,仍需深入研究。
1)物-鉆-表三位一體的巖體結構探測方法
隧道結構狹長,開挖臨空面少,巖體結構面跡線難以完全展開。施工中經常遭遇結構面產狀變化劇烈地段,簡單的巖體表面掃描已難以滿足巖體結構把控的要求。基于真彩激光掃描和雙目立體攝像技術[17],以巖體表面掃描為重點,采用陸地聲納、激發極化、瞬變電磁等物探手段與鉆孔攝像等鉆探方法內外結合,將是完善巖體結構三維探查技術體系,實現巖體結構精細化探查的必由之路。
2)巖體結構模型跨尺度聯合重構方法
巖體結構信息數據量龐大,探測數據繁雜,數據的解譯成果多樣,傳統方法如圖解法僅針對幾條或幾組結構面進行集成分析,難以全方位覆蓋巖體結構信息[18-19]。針對隧道巖體結構模型、巖體局部模型、隧道區域地質模型三個層次,基于計算機可視化建模技術,建立層次間模型耦合建模方法。著重解決地質模型局部動態更新算法,集成隧道巖體結構信息、局部信息、區域地質信息,構建隧道跨尺度可視化重構方法,將是隧道模型重構的主要發展方向,也是隧道危石識別、分析及后期查詢的必要工作。同時,巖體探測數據類型多樣,眾多類型間的數據配準與融合標準化處理將成為巖體結構信息技術革新的關鍵。日益成熟的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也為智能化的巖體結構信息數據融合帶來了新的契機。
3.2 計算方法
隨著計算機硬件水平的不斷提高,數值計算已經成為地下工程建設中必不可少的輔助研究手段。其中涉及的計算理論可以分為連續變形分析方法和非連續變形分析方法兩大類,主要包括有限單元法、有限差分法、無網格方法、數值流形元法等。縱觀當前地下工程領域,即使在計算理論和計算平臺方面百家爭鳴,但所使用的計算方法卻普遍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局限性:
1)在前期建模方面,主流數值計算方法不能實現地質體模型的實時更新。目前的地質體模型構建方式依賴于初期勘察設計報告,主要表現為通過獲得工程區域等高線信息、鉆孔地層信息以及巖土體的物理力學信息等關鍵參數,將模型邊界簡化處理,從而利用軟件前處理模塊建立地質體模型。但是,使用上述方法可能會因為地質勘探誤差或者隱伏地質缺陷造成地質體模型與實際工程存在較大偏差,因而應當基于多源地質信息融合技術,研發多尺度精細化地質體模型與工程構筑物耦合建模系統,提出地質體結構剝離識別及模型動態更新算法。
2)在計算理論方面,基于連續介質力學的方法難以模擬巖石破碎問題,基于非連續介質力學的方法難以模擬工程尺度問題,同時重大地質災害的模擬難以還原其動態演化過程。究其原因,基于連續介質力學的方法(如有限元方法)受限于其介質連續假設,而基于非連續介質力學的方法(如顆粒/塊體離散元)受限于其在計算工程尺度問題時計算單元數量龐大,難以實現可接受時間尺度內的模擬計算。同時,針對具體的重大工程地質災害,例如隧道突水突泥、圍巖垮塌以及巖爆等災害,內在機理復雜,理想簡化的本構模型難以準確描述災害演化過程中復雜的非線性過程。因此,應當重點突破多種計算理論耦合計算(例如有限單元法和離散單元法耦合計算),發展非連續介質力學計算理論中的高效計算方法,并結合物理試驗與工程經驗建立表征典型地下工程災害演化過程的本構模型。
3)在后處理展示方面,目前主流的計算平臺在數據立體化方面略顯不足。主要表現在,數值計算結果多以點、線、面(云圖)、動圖的數據形式呈現,參觀者無法真實感知重大地質災害的動態演化過程。其主要原因是VR(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AR(augmented reality,增強現實)技術與數值計算的結合不夠緊密,尚未有比較普遍的結合應用。因此應重點突破后處理可視分析系統,建立并行可視化方法,利用數據幾何和行為建模技術,構建人機交互的可視化環境,使參觀者可以身臨其境,感知工程地質災害動態演化全過程。
3.3 監測預警
目前在地下工程監測領域中應用最廣泛的技術為監控量測技術,監測內容集中于圍巖或支護結構應力、位移等信息,信息源和監測方案較為單一。傳統的“點式”監測方法可能遺漏隧道危險區域,雖然增設監測密度可提高監測效果,但工作量及設備成本將大為增加。此外不同監測設備自成體系,監測信息之間存在差異、共享性差,不利于同時空域內隧道結構穩定性分析。隨著光電傳感、無線傳輸、數字攝影技術的發展,有望解決大范圍區域信息實時高精度感知問題。在預警機制方面,現有的預警指標體系不夠完善,考慮工程地質、水文地質、設計參數、施工工藝等綜合信息不夠,單一或有限的信息無法充分反映致災因子間的關聯關系,無法量化災害所處狀態及預測時間傾向。
監測以機理為基礎,以機理的差異性來區別災害發生的類型,通過多物理場信息的不同響應來判斷災害的時間空間以及強度大小,現有的監測設計方法以及傳感器缺乏針對性,不能對具體災害類別做出精準監測,亟需開展專項設計和定向研發。預警是以過程為基礎,通過獲取、分析和判斷變量的變化情況,通過分析多源信息邏輯共生關系與關聯準則,昭示存在的風險,預測危害等級并進行時空預警,對后期主動調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4 主動調控
目前針對地質災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災害發生后,通過注漿技術、架設鋼拱架等方式進行被動治理。這既造成地質災害頻發,又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以災害發生前期和中期進行“對癥下藥”的主動調控來代替被動治理將成為應對突發性地質災害的有效手段和未來的研究熱點。
通過業界共同努力和協同攻關,建立災變演化全過程的實時預測理論和預警方法,基于大數據云平臺對地質前兆信息、預報前兆信息和施工監測信息三部分預判斷得出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與規模、致災構造的空間位置與大小,建立重大地質災害不同演化階段全過程綜合控制與智慧決策系統,最終通過智慧云端分析治理方案,提出綜合治理決策,有效地將地質災害消滅在萌芽中。
4 突涌水與圍巖垮塌重大災害主動防控技術
4.1 突涌水主動防控技術
作為世界上地下工程建設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和難度最高的國家,我國在礦山、鐵路、公路、水電以及跨流域調水等諸多領域的建設過程中經常面臨的挑戰是突涌水災害頻發。據不完全統計,在21世紀的前十年間,突涌水及其誘發的地質災害占我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中重大安全事故總數的77.3%[23],不僅耽誤工期、廢棄或改線易址,而且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并極大威脅了生態環境。隨著國家科技戰略發展規劃的逐步實施,施工期間遇到的“高水壓、大流量、強突發、多類型”突涌水災害堪稱世界級工程難題,對突涌水災害的主動防控逐漸成為制約地下工程建設發展的關鍵科學技術問題。
4.1.1 突涌水災變演化狀態判識與過程式控災模式
不同孕災模式下的突涌水災變演化過程關鍵控制因素及其相應的控制方法尚不確定,難以建立相應的決策模型,鮮有學者開展突涌水等災變過程的“控制理論”研究。采用模擬分析方法與計算程序,可以揭示不同孕災模式下深長隧道突涌水災害的災變演化全過程;基于突涌水全過程中應力場、滲流場以及位移場等信息的演變特征,劃分其災變過程的演化階段。利用不同演化階段中巖體結構狀態特征、地下水運動規律和多場特征信息,并結合多源預報結果和前兆多元信息的實時監測與識別,可以實現突涌水災變過程和演化階段的狀態判識。通過研究不同災變演化階段的關鍵因素與控制參數,實現突涌水發生位置、時間及量級的有效預測,得出隧道突涌水的最佳控制時機,最終實現隧道不同類型突涌水災變過程及與其狀態相適應的最佳控制模式決策。
4.1.2 基于隧址生態環境保護的突涌水協同控災方法
突涌水控制與治理很少從環保方面考慮對水資源的保護,大量工程案例證明,由于未實現突水演化過程的有效控制,突涌水往往造成地下水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把隧道突發地質災害控制與保護水資源和生態環境結合起來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新的理論問題。
通過研究隧址區地下水賦存和徑流規律,建立地下水負效應評價體系,并得到不同開挖狀態、注漿參數、襯砌條件下隧道涌水量計算模型;基于不同災變演化階段的關鍵因素及控制參數,可以研究隧道不同類型突涌水的控制方法及處理時機,為隧道安全施工提供決策方法。通過隧址降雨、地表水、地下水以及隧道排水的動態監測,進行基于動態監測的隧道涌水量和來源信息識別,研究隧道開挖對地下水的影響規律和影響范圍,建立“防、排、堵、截”綜合決策模型,為隧址區水資源保護提供最優方法。綜合地下水環境保護和隧體穩定性協同控制雙重準則,研究地下水限排標準,構建隧址區域地下水保護技術體系,進行集疏水泄壓、注漿堵水和水資源保護的協同控災,實現隧道施工到運營的地下水全過程控制,為保護隧址區的生態環境提供科學依據。
4.2 圍巖垮塌主動防控技術
圍巖垮塌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原始結構面及開挖擾動形成的次生結構面與開挖臨空面組合切割下形成的孤立或半孤立巖塊發生墜落、滑移、傾覆的局部失穩現象[2,4],其具有“強結構性、強隱蔽性、強突發性,分布范圍極廣、探識難度極大,防控手段盲目”的主要特點。據不完全統計,自2005年至今,見報的圍巖垮塌案例多達300余起,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重大經濟損失。隧道圍巖垮塌防控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技術難題。目前,國內外學者圍繞巖體結構信息采集、模型構建、穩定性分析、監測預警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下分別從巖體結構信息采集及解譯技術、隧道圍巖垮塌失穩機理及穩定性判識和隧道圍巖垮塌監測預警與防控三方面進行概述。
4.2.1 巖體結構信息采集及解譯技術
巖體結構信息獲取與解譯是隧道圍巖垮塌預測的基石。然而,以人工接觸測量為主的傳統結構面信息獲取手段耗時長、精度低、效率低下。因此,國內外學者嘗試將數字攝影測量技術和激光掃描技術引入巖體結構探查中,并取得了一定的實際應用效果。在數字攝影測量技術方面,日本、澳大利亞等多國開始研究利用數碼圖像技術為隧道掌子面圖像提取有效地質信息[26-28]。李浩等[29-32]結合工程實際研發了基于數碼相機的硐室編錄系統,提出了地質信息圖像處理及產狀提取算法。冷彪等[33-34]著重圖像處理算法研究,通過增強圖像質量完成結構面信息統計。在激光掃描方面,Slob等[35-36]研究了基于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巖體結構面信息獲取方法。何秉順等[37-38]應用三維激光掃描技術測量巖體結構面產狀,并通過對點云數據進行三角網格劃分,利用三角面的法向矢量來計算巖體結構面產狀。
然而,無論是數字攝影量測還是三維激光掃描,仍無法完全克服隧道、采礦等地下工程中由昏暗、多塵、潮濕等復雜施工環境帶來的數據采集難題。筆者在這方面也開展了一定的研究,通過開展隧道施工全過程照度、粉塵、濕度等環境參數跟蹤測試,提出了不同環境下圖像采集參數設定區間與最優采集模式,建立了隧道環境下激光衰減系數的計算方法,初步實現了巖體結構信息的有效獲取,如圖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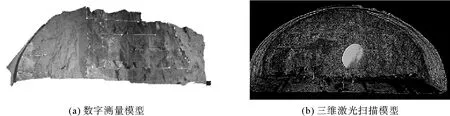
圖2 基于數字測量與三維激光掃描的隧道掌子面結構模型
4.2.2 隧道圍巖垮塌失穩機理及穩定性判識方法
隧道圍巖垮塌失穩模式的復雜性體現在其賦存環境的不確定性、受力狀態的演化性及結構的可變性。因此,圍巖垮塌失穩是一個動態問題,采取靜態理念難以有效解決。1982年,Goodman等[39]提出了塊體理論,后在塊體理論的基礎上,考慮結構面與巖塊的變形,提出并發展了非連續變形分析(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DDA)[40]。Yeung[41-42]利用楔形模型、塊體理論、三維DDA三種方法研究楔形體穩定問題,驗證了三維DDA方法的有效性。此外,針對隧道圍巖垮塌失穩動態過程,部分學者采用數值方法開展了一定的研究,如采用FLAC3D、3DEC等數值手段研究隧道不同開挖過程塊體的變形規律及穩定性影響因素問題[43-45],研究地震、爆破、地下水、地應力等因素作用下塊體的穩定狀態轉化問題[46-49],研究不同支護或加固措施下塊體及支護結構的作用關系問題[50-51]。
筆者認為,對隧道圍巖塊體結構面的受力模式進行分類,研究不同受力模式下結構面的強度演化機制,結合數值模擬手段,分析隧道塊體結構及應力轉化機制,分階段揭示不同結構面組合條件下塊體穩定性演化規律,是研究隧道圍巖垮塌演化機理的必要工作。
4.2.3 隧道圍巖垮塌監測預警與防控
相較其他隧道災害,圍巖垮塌具有顯著的局部性及突發性,其災變發生時間短促且位移前兆不明顯,傳統監測手段難以捕捉有效臨災前兆信息。巖體在災變演化過程中會產生多種物理信息響應,常常伴隨應力、溫度、形變、能量、電磁輻射(包括紅外輻射)等物理量的異常變化,可被用作災害預測的判識依據。國內外學者通過室內試驗、現場試驗等多種手段對邊坡危巖失穩、隧道突水突泥、地下硐室巖爆等災害過程巖體破壞前兆開展了大量研究,涌現了一大批新的巖體災變監測手段,主要包括聲發射技術、紅外熱成像技術、電磁輻射監測技術以及巖體固有振動頻率監測技術等[52-58]。針對隧道圍巖垮塌災害,研究其災變過程多元信息響應規律,篩選有效前兆信息,建立多元信息融合分析方法及臨災預測模型,是對隧道圍巖垮塌機理的有效補充,也是隧道圍巖垮塌監測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
5 結論
我國交通隧道建設規模和難度居世界首位,重大地質災害防控為地下工程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1)地下工程地質災害的防治長期處于被動局面,亟待建立深部巖體本構關系、動力災變機理及災變演化過程的高效模擬分析方法,研究適用于不同災害類型、災變階段的安全施工決策方法將是地下工程災害防控的重點突破方向。
2)立足國家發展戰略,作為兩大世紀工程,川藏鐵路和規劃中的渤海灣跨海通道將為我國地下工程領域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也必將推動我國在高海拔山嶺隧道修建技術和超長海底隧道設計方法突破技術瓶頸,領跑世界相關技術發展。
3)針對典型突發性重大地質災害,重點歸納了災害主動防控亟待突破的關鍵領域:深部巖體本構與破壞機制、工程尺度模擬與分析模型、災變演化機理與過程調控,地質災害監測預警與主動調控方法。以學科交叉融合創新為基礎,建立融合動態修正多尺度耦合建模技術、巖土工程災害演化過程模擬方法及基于虛擬現實的后處理技術的地質災害模擬演化系統是實現突水突泥、圍巖垮塌、大變形、巖爆等重大災害主動防控的重要途徑。
4)聚焦隧道突涌水與圍巖垮塌重大災害,論述隧道工程不同災害發生時間、位置和危害等級的領域研究熱點,探討了地質災害主動防控的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建立典型災害的多元信息融合分析方法及臨災預測模型,可有效充實地下工程災害災變機理與災害監測體系,為地下工程安全建設保駕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