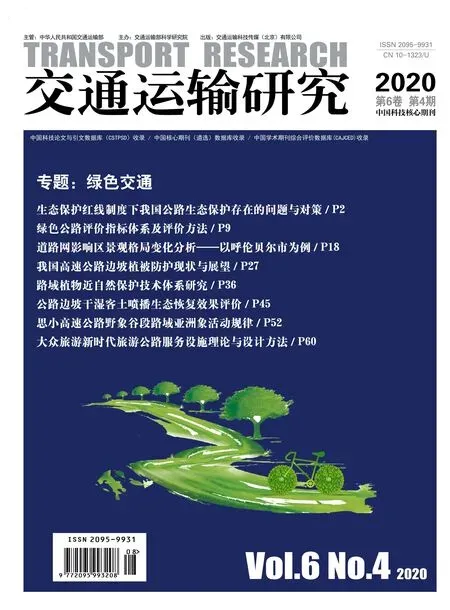思小高速公路野象谷段路域亞洲象活動規律
關 磊,王 云,陳 兵,王 冀,徐景江,鄭宏民,趙 琨
(1.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29;2.交科院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3.云南交通投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650228)
0 引言
我國公路建設發展迅速,截至2018 年底我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已超過14 萬公里,成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1]。公路的建設和運營不可避免地對周邊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造成影響,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尤為突出[2]。在我國,有兩條公路對野生動物活動造成的影響最引人關注:青藏公路對藏羚羊遷徙的影響和思小高速對亞洲象活動的影響。其中,思小高速是全封閉型的高速公路,完全限制了亞洲象從高速公路穿越。
亞洲象屬哺乳綱長鼻目象科亞洲象屬,是我國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將其列為瀕危物種,《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將其列入附錄Ⅰ物種[3]。亞洲象曾廣泛分布于我國南方地區,但是由于人為干擾和過度捕殺,亞洲象分布區域不斷縮小,目前僅分布在云南省西雙版納、普洱和臨滄3 個地區[4-5]。作為我國現存體型最大的陸生野生動物,亞洲象目前面臨著棲息地喪失、棲息地破碎化、種群隔離、偷獵/盜獵等諸多威脅,估計我國境內種群數量為228~279頭[6]。
思小高速公路自2006年起通車運營,橫穿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勐養子保護區。作為亞洲象分布的主要區域之一,活動在該地區的亞洲象種群是否對公路及通行車輛產生了適應性,值得開展持續的跟蹤調研工作。由于亞洲象的區域性分布特征,國外有關交通對亞洲象的影響研究集中在印度地區,火車與亞洲象相撞致死統計研究是其關注的主要方面。統計顯示,過去25年中印度有超過200 頭亞洲象被火車撞死[7-8]。而關于交通對非洲象的影響研究則更多聚焦于道路修建帶來的偷獵/盜獵等方面,因為道路修建為偷獵/盜獵者提供了更為便捷的入口。剛果盆地由于道路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偷獵/盜獵活動,給當地大型野生動物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過去10年約有2/3 的非洲象死于偷獵/盜獵[9-10]。國內有關交通對亞洲象的影響研究相對較少,以動物通道、道路致死、路網阻隔等宏觀層面的研究為主,Pan等[11]在思小高速建成初期,于2006 年3 月到2006年10 月對思小高速為亞洲象預留的23 條野生動物通道和2 個上跨式隧道進行了研究,發現只有44%的人工通道被亞洲象所利用,認為思小高速阻礙了亞洲象的活動;思小高速公路上共記錄亞洲象活動44 次,約40 次發生在晚間至凌晨,其中1次造成車象相撞事故。Huang等[12]使用最大熵算法預測未來的交通網絡擴張方案,預測結果顯示交通網絡擴張可能會減少亞洲象棲息地,亞洲象各種群間的隔離程度將進一步加深。
本研究采用紅外相機技術對思小高速公路野象谷段的亞洲象活動現狀開展監測。紅外相機技術作為一種非損傷性調查方法,為野生動物本地資源調查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證,目前已廣泛應用于陸生脊椎動物多樣性監測[13]。本研究從亞洲象種群活動規律的微觀層面開展研究,跟蹤監測思小高速公路運營多年后對亞洲象的影響范圍及對其活動節律的影響,從動物本身的生態習性方面為相關保護和管理工作提供數據支持,旨在更為科學有效地保護該區域的亞洲象種群以及保障公路運輸安全。
1 研究地區概況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東經99°56′~101°50′,北緯21°08′~22°36′。西雙版納野象谷地處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勐養子保護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保護區)之內,地處北回歸線以南,氣候類型屬于南亞熱帶山地季風氣候,年均氣溫18℃,年降雨量1000~2000mm。5 月至9 月為雨季,炎熱多雨;10 月至次年4月為旱季,溫暖干燥[14]。
思小高速K78+450—K91+710 段穿越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勐養子保護區,限速80km/h,路寬22.5m,橋隧長占線路總長的26.4%。在高速公路設計階段,為穿越保護區段的亞洲象活動區設置了2個隧道以及23條動物通道[11]。
2 研究方法
2.1 相機布設與數據采集
從2018 年4 月10 日到2019 年10 月18 日,通過前期調查,在野象谷北立交、觀象臺、野象谷南收費站附近、野象谷隧道等4 個亞洲象經常活動的區域共布設紅外相機20 臺(型號為Ltl-Acorn 6210MC),每臺相機至少相隔100m。具體布設位置如圖1所示。

圖1 紅外相機布設示意圖
相機主要布設在橋梁、隧道等可能會被亞洲象利用的公路基礎設施周邊,有亞洲象活動痕跡或獸道附近的區域。由于拍攝對象亞洲象體型巨大,相機固定位置較高,在喬木樹干離地2m 處。相機朝向通常與獸道呈銳角,盡量避開陽光直射,前方無遮擋,并采用GPS 記錄紅外相機布設點。
2.2 相機參數設置
紅外相機參數設置如下:(1)拍攝照片模式;(2)照片像素大小為9MP(900 萬像素);(3)傳感器靈敏度中等;(4)觸發間隔10min;(5)每次觸發連拍3 張照片;(6)監測期內通常每3~6 個月即對相機進行檢查,更換記憶卡和電池。
2.3 數據處理
對拍攝的照片以人工目視的方式進行判別。由于亞洲象體型巨大,大多數情況下以照片拍攝到亞洲象的清晰實體作為判別依據。但部分夜間情況下,由于亞洲象距離較遠而無法拍攝到大象實體,則以確定的陰影作為依據來判別亞洲象。
以1臺相機在野外工作24h作為1個相機工作日(Camera Day,CD),對于同一個地點且時間相近(時間間隔小于30min)連續拍攝的同一種動物的照片算作1 張,定義為1 張獨立照片(Inde?pendent Photograph,IP),以此計算亞洲象的相對數量(Relative Number,RN)[15]。
全天時間段劃分如下:06:00—08:00 清晨,08:00—18:00晝間(8:00—12:00上午,12:00—14:00中午,14:00—18:00下午),18:00—20:00黃昏,20:00—06:00夜間[15]。
3 研究結果
3.1 路域亞洲象相對豐富度
調查期間20 臺相機從2018 年4 月10 日到2019 年10 月18 日共拍攝了556 天,累計11 120 CD,獲得可判別的獨立照片68 組,共拍攝到亞洲象113 只次。其中,拍到亞洲象數量最多的一組是2019年3月23日在野象谷南觀象臺附近拍到的10只亞洲象家族。
設置相機的4 個位點所拍到亞洲象的有效照片數量差別極大,其中最多的是在野象谷南觀象臺位點,共拍攝到亞洲象有效照片33組,共拍攝到亞洲象63 只次,最少的是在野象谷北立交位點,共拍攝到亞洲象有效照片1 組,共拍攝到亞洲象1 只次。各位點拍攝到的亞洲象情況如表1所示,部分照片如圖2所示。

表1 4個相機位點拍攝情況


圖2 拍攝的部分亞洲象照片
3.2 路域亞洲象日活動節律
根據照片上記錄的拍攝時間,對全天24h 拍攝到的亞洲象有效照片數量和拍攝到的亞洲象個體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見圖3。從圖3中可以看到,在監測區內亞洲象的活動頻率在16:00—23:00 處于高峰,23:00—次日8:00 活動頻率相對較低。其中,18:00—19:00 拍攝到亞洲象有效照片7 組,亞洲象22 只次,19:00—20:00 拍攝到亞洲象有效照片9 組,亞洲象12 只次。這兩個時段分別為有效照片數量和個體數量最多的兩個時段。

圖3 紅外相機拍攝數據隨時間的變化
按照前文對全天時間段的劃分,統計各個時間段累積拍攝的有效照片數量和亞洲象個體數量,結果如表2 所示。可以看到,在監測區域內亞洲象活動最頻繁的時間段是夜間,其次是黃昏,再次是上午和下午;活動最不頻繁的時間段是清晨和中午。

表2 不同時間段有效照片及亞洲象個體情況
3.3 路域亞洲象季節活動節律
根據照片上記錄的月份,對不同月份拍攝到的亞洲象有效照片數量和亞洲象個體數量進行統計。2018 年和2019 年均有4 月—10 月的數據,2018年4月和2019年10月兩個月的拍攝時間不足一整月,故4 月數據取2019 年4 月的數據,10 月數據取2018 年10 月的數據,5 月—9 月數據取兩年數據的均值,統計結果如圖4 所示。可以明顯看到,亞洲象在監測區域內的活動高峰時期是1 月—7 月,其中3 月份的活動程度最高,拍攝到有效照片13組,亞洲象個體數量28只次。

圖4 紅外相機拍攝數據隨月份的變化
4 討論
4.1 亞洲象對公路的適應現狀
本次監測結果顯示,亞洲象在公路沿線區域活動時對構造物橋梁和隧道均有選擇,這與潘文婧[11]對思小高速沿線23 個亞洲象通道和2 個隧道上方亞洲象活動情況的研究結論一致。亞洲象對公路構造物周邊生境的選擇沒有明顯差異性,但傾向于使用與其原有活動路徑一致的人工通道。
亞洲象對道路已經沒有明顯的回避行為,多次拍攝到亞洲象在國道邊及思小高速橋下活動的行為。Gubbi 等[16]和Granandos 等[17]的研究也發現亞洲象可能會造訪路邊,取食演替早期的植被,且該研究沒有發現亞洲象亞種群與道路的距離與亞洲象肇事風險之間存在關系。根據相關統計,在中國亞洲象與車輛相關的事故比較少,推測原因是亞洲象種群規模較小、特定區域有限速要求、高速公路柵欄阻隔以及野生物動保護部門和交通部門的協作等。
4.2 人為干擾對亞洲象日活動節律的影響
本研究監測區內的亞洲象日活動節律主要集中在夜間與黃昏。張立等[18]對思茅區亞洲象種群的研究也發現,象群主要在黃昏到次日黎明之間活動,白天隱藏在密林中休息,一般17:00 以后象群才開始活動,且象群的遷移也在夜間進行。而Sukunmar[19]對印度南部的亞洲象種群進行了研究,發現受人為干擾較為嚴重的地區,亞洲象有類似日落而出、日出而息的日活動節律。綜合以上研究結論以及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推測本研究監測區內人為干擾對亞洲象的日活動節律活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與2003年該地區的亞洲象日活動節律相比沒有明顯的變化。后續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人為干擾因素的量化。
4.3 亞洲象季節活動節律分析
亞洲象除了具有日活動節律外,還具有顯著的季節活動節律。本研究觀測到路側亞洲象活動高峰時期是1 月—7 月,其中3 月份的活動程度最高。亞洲象所在地區有明顯的雨季和旱季氣候特征,通常將5 月—9 月劃分為雨季,10 月—次年4月劃分為旱季,不同季節亞洲象的活動區域和活動范圍有所差異。由于亞洲象喜食的植物在雨季來臨后需1~2 個月才能生長成熟,因此其活動時間與季節更替時間相比有一定的時滯。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張立課題組對亞洲象多年的觀測[20],亞洲象在旱季來臨時,其位于熱帶雨林深處山地上的棲息地缺水,食物來源會受到影響,通常會遷徙到溝谷等水源較為充沛的地區進行取食等日常活動。公路通常沿溝谷修建,本研究的監測區域也位于溝谷地區,監測到的亞洲象季節活動頻率與當地的旱季與雨季交替氣候條件基本一致。根據林柳等[21]和王巧燕等[22]的研究,食物來源是引起亞洲象家域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到歷史數據的旱季末期才出現路域亞洲象活動的高峰,因此推測出現該現象與2018—2019 年的降雨、植被狀況等亞洲象食物相關因子有關。
4.4 公路路域亞洲象活動區的管理
結合從思小高速公路普洱管理處收集到的2017 年思小高速野象谷南收費站車流量統計數據(見圖5),可以明顯發現車流量的兩個高峰:寒假(2 月)和暑假(8 月)。其中寒假假期為亞洲象在野象谷區域活動的高峰時期,應該在這個時期加強對該區域亞洲象的監控,最大程度地避免人象沖突,保證游客的人身及財產安全。

圖5 2017年思小高速野象谷南收費站車流量統計
雖然在中國境內發生的車輛與亞洲象直接相撞事故較少,但是關于印度的相關研究顯示,時速60km/h 的火車在1987—2015 年間撞死了超過200 頭亞洲象,而更高等級的道路減少了80%的大象移動空間[23]。因此,需要更加關注交通建設和人為干擾對亞洲象造成的間接影響。Huang等[12]對中國西南地區亞洲象肇事的空間分布模型進行了研究,并使用最大熵算法預測未來的交通網絡擴張方案,預測結果顯示交通網絡擴張可能會減少亞洲象棲息地,亞洲象各種群間的隔離程度將進一步加深,人象沖突將進一步加劇。因此,建議在該地區開展交通基礎設施規劃時,將亞洲象及其生境作為專項內容進行評價,評價結果納入規劃的參考因素。同時,在紅外相機監測期間,亞洲象的活動區域中多次拍攝到當地村民、游客采野菜、野生菌等干擾行為,其人身安全存在一定的隱患,建議加強對亞洲象活動區域公路周邊人類活動的管理。
5 結語
對思小高速公路運營14年后路域亞洲象活動規律的監測表明,亞洲象對思小高速已沒有明顯的回避,但人為干擾對其活動節律具有一定影響。為了減小由于道路修建和人類活動對亞洲象種群的影響,建議持續對路域亞洲象活動范圍、頻次、種群動態等進行監測,擴大監測區域,延長監測時間,為將來思小高速改擴建工程和周邊其他交通工程建設合理避繞亞洲象活動重點區域,修建更符合亞洲象原有活動路線的通道提供充分的數據和理論支撐,為今后其他生物多樣性較高地區高速公路的規劃、設計、建設和運營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