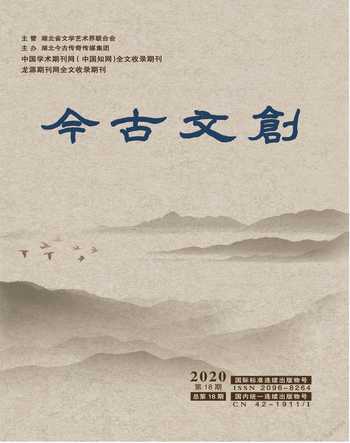心靈的避難所
【摘要】 《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以其溫暖人心的治愈功能聞名。奧斯特在該書中以大城市中的孤獨者為聚焦點,敘述他們在布魯克林這樣的小社區中重建生活圈,將文學作為心靈避難所尋求慰藉的故事。本文則以創傷理論和想象共同體為理論指導,分別從作者、作品和時代三方面解讀《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的治愈功能。
【關鍵詞】 保羅·奧斯特;《布魯克林的荒唐事》;避難所;治愈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8-0004-02
一、引言
從古至今,書寫災難的作品不勝枚舉且大多揭露其殘酷本質,反思人性。保羅·奧斯特的《布魯克林的荒唐事》是該類作品的一個代表。本文以創傷理論和想象共同體為理論指導,分別從作者、作品和時代三方面解讀《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的治愈功能。
二、訴諸文學的作家
保羅·奧斯特,一個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創新小說家。《布魯克林的荒唐事》是其眾多作品中最具熱情、最具生氣的一部,是一支為普通人吟唱的贊歌,感人而難忘。
書中,保羅·奧斯特將自己的個人元素緊密地嵌入人物和故事。他不僅為書中人物編織暖心治愈的人生故事,還為整個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之痛的美國提供了精神層面的解救之道。可以說,這本書也是作者個人的心靈的避難所,毫不遮掩地強調文學不可小覷的治愈功能。本小節著重討論作者將文學作為自己心靈的避難所,體現在《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個人元素。
(一)寫作風格轉向。紐約一直是當保羅·奧斯特熱衷書寫的對象。在經歷了恐怖襲擊和次貸金融危機之后,奧斯特對城市景觀書寫有明顯的轉向,即從抽象的幻象之都轉向具體化的文化地理景觀——布魯克林。奧斯特本人是極具創新力的作家,他不拘泥于某一題材或者話題,并將文學作為自己精神歸屬地不斷耕耘。時代的、個人的都在文學作品直觀呈現。雖然《布魯克林的荒唐事》描寫的是襲擊發生前的故事,但是它帶給人的治愈力量卻非比尋常。實際上,奧斯特正是用這樣的故事告訴人們,只要“當你發現一個有精神的人時,這世界就還有一些希望”(奧斯特 51),奧斯特從自己原有的后現代主義轉向現實主義,表現出對時代的關懷,試圖用文學為自己和時代提供一個心理的避難所。
(二)個人元素嵌入。作者個人元素在《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的體現主要集中在書中人物經歷,人物個性的方面。
首先是故事地點——布魯克林。“布魯克林既是紐約,又不是紐約”(奧斯特,46),它沒有大城市極度繁華后的孤獨感,相反,有的是一種充實感,是書中三個受傷的孤獨者的療傷地。其次,各位人物的特點。奧斯特借湯姆之口講述了卡夫卡用信件中治愈丟失布娃娃的小女孩的故事,借納森之口直言“永遠不要低估書本的力量”(300)。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細節再現作者個人元素,比如納森的猶太身份設定是作者猶太血統的再現;書中對宗教狂熱者邁納和他所在的圣道門教會的批判反映作者對恐怖分子的批判等等。
奧斯特將個人經歷轉移到作品人物中,不僅是個人元素的再現也是作者本人從文學中汲取力量的渠道。綜上,奧斯特將文學作為自己的心靈的避難所,也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斷深化這樣的信念。
三、集體取暖的孤獨者
(一)文學避難所。作為將文學作為避難所的實踐者,作者書中三個主要人物皆與文學結緣:納森自己成了別人眼中的作家,湯姆攻讀文學博士并一直深愛文學,哈利則經營一家二手書店并提出了最具文學理想性的“存在飯店”。但是,這里最典型的還是納森。
“我在尋找一個清凈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議布魯克林。”(奧斯特 1)這是《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的開篇首句,也是主人翁納森的心里獨白。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自我,既包括自己認為所屬的關系,也取決于認識他的其他個體及其所在團體所做的相應評價。納森·格拉斯,一個正獨自走向生命盡頭的癌癥患者。婚姻破裂,年老退休,無親無友,唯一的血脈——女兒蕾切爾也與自己關系緊張,納森是個徹頭徹尾的孤獨者。
剛來到布魯克林的納森,用厭世和否定的態度看待人和事,對關心自己病情的女兒敷衍了事,對打趣他的服務員心生厭煩。但是,為了打發時間,他開始種花、散步、理發,然而“總是獨自一人”(4)。但是,這些雜事并不能驅趕他的孤獨,直到機緣巧合下重拾寫作的愛好才有所好轉。但是,他選擇用一種認真的態度寫戲謔的話題,他稱之為《人類愚行大全》。
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獨者,在失去了所有的外界認可和個人價值后,尋求的最終擺脫內心空虛和消磨時間的方法竟是寫作。納森自己說“我不愿我的精神變得空空洞洞,也不愿沉溺于沮喪的內心自省”(5),正是表明自己將文學作為自己心靈的避難所,想象中的共同體。“內森的記憶書寫,體現文學建構想象共同體的作用”(樸玉 2018:45)。納森個人的記憶書寫,是源于對文學治愈功能的秉信,同時也是想象共同體的體現。
(二)聚集取暖地。除了訴諸文學避難所,社交取暖也是必需。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其社會性,必要且重要的社交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無法和不愿拒絕的。隨著故事的發展,納森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自然而然,《人類愚行大全》中慢慢增加了除了自己圈內其他人的愚行傻事。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重要故事在飯店展開。所以,本文認為飯店也是文中孤獨者們聚集取暖的避難所之一。
宇宙小店,是納森嘗試了好幾家餐廳之后固定下來的午餐地點。后來,宇宙小館也成為納森和朋友湯姆默契中形成的每日午餐地點。這個毫無特色的宇宙小館承載了書中前期情節的展開和故事的發展,好的壞的、秘密的公開的、快樂的羞恥的都在這里鋪展開來。
在這里,湯姆對納森一吐心中積郁,坦白了自己在中斷博士論文之后努力開啟新生活卻屢屢失敗最終做了出租車司機的煉獄般苦楚,也講述了自己老板哈里·布賴特曼的鮮為人知、陰郁晦暗的人生經歷。納森則在這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盡管后來納森因為不快不再光顧宇宙小館,但是這里仍是納森展開新生活重要的取暖地之一。原先的他孤獨厭世,離開宇宙小館后的他漸漸地開始向社會伸出了試探的觸角。
除了宇宙小館,書中很多重要情節也與飯店有關。最具代表性是“食飲之夜”。納森,湯姆,哈里三人已經坦誠過往,互相了解。三人選擇在豪華的餐廳里享用價格不菲的酒飯,為的是痛痛快快地暢聊心事。這是第一點,三個原先喪失生活希望的孤獨者聚集在此談天說地,天馬行空,沒有任何物質利益牽掛,這是孤獨者們抱團取暖,相互慰藉的行為,飯店則是他們的暫時的取暖地和避難所。
更有趣的是,這次談話中促成了一個“生存飯店”,一個三人的想象共同體。“生存飯店”原是哈里小時候的幻想地點,一方面是救助二戰兒童的庇護所,另一方面是純理想主義的彼岸世界。不論從那個方面看,這都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歡樂的烏托邦式的避難所。湯姆對于“生存飯店”的想法則不如哈里和納森那樣熱衷,他只是消極地表達著自己對這烏煙瘴氣的世界的厭惡,想要找一處安靜祥和的社區躲避。但實際上他對“生存飯店”這樣一個精神庇護所心向往之。特別是當湯姆和納森偶然住到了“生存飯店”的現實版本的“蛤蜊湯酒店”時,兩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悅感,甚至積極地謀劃如何將“蛤蜊湯酒店”買下作為“生存酒店”的方案。
看似消極的孤獨者實際上是積極地找尋生命的意義所在(Pramanik & Modak 2017;樸玉 2018)。孤獨者就像飛蛾一樣,沖著代表溫暖的亮光處飛去,當他們接踵而至后,這溫暖他們的就不只有亮光了,還有他們彼此間的聚攏的體溫。《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的人物們,就如同一只只孤獨的飛蛾,不斷找尋著理想中的亮光處,而飯店這樣的聚集地就是他們取暖的庇護所。
四、大起大落的新世紀
“9·11”恐怖襲擊事件給美國帶來的是恐慌和迷茫、傳統價值觀的質疑和幻滅。精神危機和意識形態的淪陷讓人們陷入恐慌。文學在此時扛起了救贖的大旗,眾多傷痕文學作品涌現。就像奧斯特在書中寫到的卡夫卡與小女孩的故事一樣,文學扮演的就是卡夫卡這樣一個用文字和關懷撫慰人心的角色,而這個時代就是丟失了布娃娃的女孩。呼嘯而來的四架飛機,撞倒了世貿雙子塔和五角大樓,就如同奪取了這個時代的象征繁榮和權力,時代創傷無法用物質和武力來解決,文學便是適時的解藥。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文學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它從現實汲取素材卻回饋出更多。
五、結語
保羅·奧斯特在大起大落的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時代背景下,面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結合個人經歷為創傷后的美國人民寫下了《布魯克林的荒唐事》這樣一本治愈小說。它不僅僅是作者自己的精神寄托,還為整個時代展現了一種精神并提供了一條治愈之路。自我價值的尋找、生活意義的重建、心理創傷的修復,這是正本小說中每個孤獨者都在努力做的事,奧斯特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訴說著文學的治愈力量,是他對自己,對作品乃至對整個時代的關懷。
參考文獻:
[1]Pramanik1,A.,and Modak, A. Trouncing Noogenic Neuroses through Logos: a Logotherapeutic Reading of Paul Auster’s The Brooklyn Follies, Rupkatha Journal 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umanities (2)2017:213-219.
[2]保羅·奧斯特.布魯克林的荒唐事[M].陳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3]樸玉.奧斯特《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的自我與共同體思想[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42-47.
作者簡介:
田捧,女,漢族,河南永城人,碩士研究生,單位: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研究方向:話語分析。